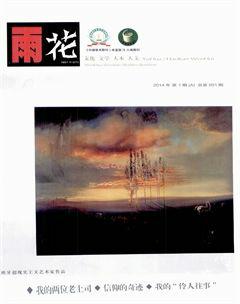體驗自由
薛爾康
雖無自由之身,卻有自由之心,意識既已感悟自由,肉體的禁錮還能算是禁錮嗎?當精神擺脫客觀現實的制約,營造出一份自在的心情,人便進入“監獄本無房,鐵門亦無鎖”的境界。
在一個沒有自由的地方說自由,頗有諷刺意味,恰如面孔餓得發青奢談美味佳肴。轉念一想,相比腸胃撐得難受的人來說,那個臉皮發青的家伙才真的懂得何為美昧。
號子分里外兩間,里間是真正坐的,外間同樣大小,頂上封著扁鋼與鋼管焊成的網,遛腿用,叫風場。
每當早晨傳來空谷足音,“咔嗒”一聲如同上帝咳嗽:風門開了。在六平米的里間足足憋了二十三小時的囚犯迫不及待到外間走動透氣。風場是人性的表示,證實關在里間的不是兩足哺乳類動物,一小時的放風大大降低精神性疾病發生的可能。
透過鋼鐵的網,仰望藍色的天,內心總是悸動起來:在與自然的唯一聯系中,遠古的記憶在體內蘇醒,發覺靈魂與天空存在著血緣的聯系,我就是從那深邃的蔚藍中誕生。憑著這樣的感覺,我信了天人合一那句話,有理由拒絕人從猴子變來的學說。人類祖先該是遨游藍天的會飛的動物吧?
沒料到我的妄想竟然得到佐證。手頭的一本佛教書籍告訴我,地球人類來自光音天第七重天,本來出于好奇,觀光而已,結果貪吃地球上的食物,身體變重,再也飛不回去。可見地球上的美食領先宇宙。要想推定這種結論,目前可以找到的根據有二,一地球人個個是天生的饞嘴,二是人都愛仰望天空,帶著幾許惆悵。
幾百萬年來,所有的脊椎類爬行動物迫于生存的壓力都在進化,唯獨人直立,尚且頸椎骨特別靈活,做昂首向天的動作毫不費力。人類對于自由的追求從仰望天空開始,誰不想掙脫地球的引力,獲得飛翔的愉悅呢?遠古中國人的崇拜物一式是騰云駕霧的,就連太陽也被想象為鳥,稱作金烏、赤烏、曙雀;古埃及的法老們不敢落伍,崇拜鷹神荷魯斯,鷹至今刻在一些西方國家的貨幣或者旗幟上。
人一出生便意味著與自由簽訂了生命之約。自由精神出于人類的本性,也是根本的追求,當是當今世界最無爭議的事。
但是,人老是抬頭望天也不是件好事,容易想入非非,像我現在凝望頭頂上的天被割成36塊大小相等的矩形,就犯糊涂:我與天空究竟誰被囚禁了?看來,鳥籠一定要用黑布蒙起來,開在牢房高處的小窗戶雖然要跳起來才能望見外面,仍需用擋板擋住出于同理。
在號子里呆久了,我終于能平靜地接受沒有自由的日子,原來置身的那個世界淡出記憶。你是一只打開鳥籠也不想飛出去的鳥了吧?我沒事找事問自己,直把自己問得心驚肉跳,驚悟自身處境的危險。
自由的意識竟能從人性中清除掉?
其實,在牢里不能說沒自由,嘴巴就享有充分的自由,罵什么都可以,而且沒人管,以至于我想誰想罵個痛快無妨坐一回牢。同倉難友哪天不罵就沒法過夜,罵政府罵官員罵公安,罵得痛快惡毒、狗血噴頭,販毒犯盜竊犯搶劫犯都夠判政治犯。他們是用言論的自由聊補人身的不自由吧?對于我而言無補于事,我的自由在哪里呢?
有一陣,牢里安排做工,插塑料花或做燈珠,盡是簡單重復的活兒。干活是歡天喜地的事,因為風門就整天開著了。出于所方照顧,沒讓我干,其余五人到外面做活,我獨占六平米不說,還能隨時到風場溜達,活動空間一下子擴大到十二平米。這個便宜撿得大了去了,就因為那擴大了一倍的空間,我讀書、思考竟然格外專注深入,寫點兒筆記之類思路敏捷。早先寫作,有一種不是我在寫的感覺,我不過是某種力量借來捏筆的一支胳臂,夜以繼日不覺得累。事后,常常覺得那些文字不是我寫的,文章發表后讀著會吃驚:這是我寫的嗎?
現在,腦血管的淤塞忽然被清除干凈,這是擴大的那六平米做出的貢獻,我重新變做那支捏筆的胳臂。自由實在用不著太多,甚至只需要是一種許諾或者象征,因為我整天窩在里間做我的事,懶得到風場去,有人往返進出的時候,還要叮囑一聲:“請關上風門。”
空間雖只擴大一倍,帶來的卻是十倍的自由,還有一百倍的感嘆。空間如此可愛,空間原來等于自由,此種判斷似乎觸及到生存的本原,于是理解人為什么舍命追求空間。就拿人類歷史來說,除了一群人與另一群人為爭奪空間打打殺殺之外,也實在看不到別的故事。
兩個月后,沒工做了,長吁短嘆在四壁間來回擊撞。我的奢華生活戛然而止,內心已無法接受回歸的正常,整日惶惶不安,靠來回踱步壓制浮躁的情緒。自由原來是不能得而復失的,哪怕只給你那么一點點,這該是中外專制制度不愿意觸碰自由,歷代獨夫民賊聞自由而喪膽的緣故吧?
我不時走過去捶風門出氣,忘記這是一種違反監規的放肆行為。飯窗突然啪地打開,巴掌大的長方形中出現老管教的面孔,沒等我說一聲對不起,他就把飯窗啪地關上了。老管教一向對我頗為關照,但這一次的關照完全不同,是理解我的行為之后給予的格外開恩。他連一句警告的話也沒說,讓我感動了一整天。顯然,鎖住的風門是令我感到窒息的原因。平心而論,兩個月來風門雖未上鎖,也是關住的,與現在形式相似。形式的確具有欺騙性,但自由不能是欺騙,自由的涵義決定它不可能只是一種形式。以前,只是我不想出去罷了,隨著一聲清脆的“咔嗒”,除非白癡,誰要想象風門開著是不可能的。
時間又過去一年,說起來請別不信,我竟然喜歡上這個六平米空間了。幾年來,馬不停蹄,忙于商務,抱怨沒有讀書思考的自由,休息的自由,寫作的自由,抱怨多了,命運便以荒誕的形式讓我擁有這些自由。都說牢里時間如山,壓得死人,眼下,我已將山挖空,還挖出坑來,對歲月生出白駒過隙的埋怨,沖破了“把牢底坐穿”的記錄。
時間,正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消逝,沒做多少事呢,一晃眼一天沒有了;一不留神,一周一個月又過去了。雖未坐禪,已進入“坐禪一日一彈指”的境界。
此種情狀,促使我逼問自由的真義。
以前,我之所以坐牢坐得辛苦,是精神跟著肉體坐了牢,精神的牢是自設的,也就真的坐了牢。自由是生命活性和活力的體現吧,往更高的層面說,是生命力轉化為創造力的重要環節吧,當我的生命重新煥發活力,進入創造的過程,不就處在自由的境界中了嗎?endprint
坐牢并不是我的選擇,但將牢房變為書房卻可以是我的選擇。這種選擇對我來說很自然,就像橋牌迷沃倫·巴菲特說下面的話很自然:“如果一個監獄的房間里有三個會打橋牌的人的話,我不介意去坐牢。”
意想不到,監獄這種鬼地方竟是修身養性的好所在。如同蝸居深山的苦行僧,忍受環境的壓迫,磨煉受難的心志,冥想修行,超然自得,獲得精神的自由和靈魂的解脫。我覺得自己站著比從前更像一個男人。
風門,還有那扇每次關閉必會發出震悚心靈的金屬撞擊聲的牢門,我已經不介意它們的存在。空間繼續延伸,而且豐富,再聯想那些打開籠子也不想飛出去的鳥,覺得可悲的不是鳥,倒是籠子。鳥不以為籠子是籠子了。
自由原來可以用意識來體驗,環境壓力在體驗中分崩離析,并且獲得生理快感和審美感受。當生命意識進人由被動進入主動自覺的追求,我感到意識世界的新鮮、美麗、遼闊、深邃,宇宙從來沒有如此和諧過。
我對自由的感悟,可以從中國文化淵源中尋找到存在的理由。自古以來,中國人認為自由來自自然之理,來自心與物、內與外、人與自然的和諧合一。自由既由人的內心世界來體驗,如果沒有心靈的自由,也便感悟不到生命世界的自由。這種哲學,與西方人認為自由來自神性的賦予完全不同,兩者來路不同勢必造成詮釋的不同。
基督教世界認為人既是上帝創造,必享有天賦人權。這種觀念源自《圣經》,已有三千多年歷史,正值商代末期,其時華夏確認的是天賦王權的觀念,老百姓的自由拿捏在一個人的手中,不當順民便沒有生路。《圣經》既由猶太人寫出來,自然要表達在埃及當過四百五十年奴隸的民族的訴求,他們渴望人的解放、平等、博愛,對法老的統治發動孤注一擲的反抗。到獨立戰爭時期,美國人喊出的口號也是“不自由,毋寧死”。故而,西方世界的自由注重人身的不被奴役和束縛,至于對喜歡胡說八道的嘴巴和胡思亂想的大腦,沒有專門予以強調,直至上世紀中葉發現疏漏,由此,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除了規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外,宣稱“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布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首先從西方將“自由”概念引進中國的是嚴復,他老人家斷言:“西方之所以強,中國之所以弱,其原因全在國民之自由不自由異耳。”此話銳利得在中華民族身上割出血來,指明自由是開創性和創造力的源泉,可見自由不止是人性的基本需求,對人類的發展至關重要。這個世界上真理太多太多,能陪伴人類走到最后的少之又少,嚴復老人家對于民族強弱的發現是其中之一。
有人說,整個哲學的起點和終點是自由。哲學是哲學家腦子里擺弄出來的似是而非的玄虛,哪里擔得起這個綱呀,將哲學兩字拿掉,寫人人性兩字才能顛撲不破!中國自建立大一統的封建專制的秦王朝起,歷代興文字獄和言罪,士大夫們只得放棄外在的生命世界的自由,轉而尋求內心世界的自由,以避免肢體的不自由或者遭消滅。幸而在百家爭鳴的年代里,老莊已經創建好一套完備的理論擺在了那兒,以供不時之需。中國的知識階層大受其惠,以抽象為特點的中國文化便以更多的努力轉入精神世界,于是,一種超越人身的自由觀奇妙地出現。且不管這是中國人的幸與不幸,憑賴心性的熔煉、精神的升華而獲得的自由,不須他人恩賜,即使類似寓言或者童話,卻是實惠得很。在長達數千年的封建專制王朝,文人不僅未被折憋死,還竟然創造出那么燦爛的文化奇觀。反之,中國歷史和文明勢必是另一碼事了。
莊子是追求精神自由的始祖,他對老子的道做出精微美好的延伸,首創中華民族特有的審美的自然主義的境界。他早年辭去蒙城小官,寧愿糝湯野菜,自囚陋屋著書,楚威王派使者攜千金請他出山,莊子嘻嘻哈哈地“喻牛辭相”,要不然,世上便無《逍遙游》,后人也便無法體驗那種擺脫物質世界、無極之外又是無極的精神自由。
比照中國的理論,西方對自由的詮釋,及不及格是個問題。超逸脫俗,無為自化,西方人摸得著頭腦嗎?“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不是上帝才有的自由嗎?禪宗提出“平常心是道”,取自老莊又普及老莊,讓中國式的自由觀在世俗社會遍地的生根開花。
我是深得上述自由觀的實惠的。譬如,頭頂上日夜亮著的200瓦大燈泡不存在了,不再為之失眠,且具催眠之功效,我每天獲得深度的一夜不醒的睡眠。又譬如,風門的“咔嗒”聲不再是上帝的咳嗽,在風場呆不滿半小時,我要緊告別上帝回來做自己的事了。再譬如說,讀一本書讀至入神,我從心里對自己說,可別在這兩天放我出去,容我將書讀完吧!
雖無自由之身,卻有自由之心,意識既已感悟自由,肉體的禁錮還能算是禁錮嗎?當精神擺脫客觀現實的制約,營造出一份自在的心情,人便進入“監獄本無房,鐵門亦無鎖”的境界,以至將牢房認作再生之地,這是我不愿意惡咒這個該死的六平米的理由。
自由的實質不過是一種心理感受,所以,我要說精神的自由是人類自由的落腳點,是更深刻的自由。看來,對前文“自由即空間”的詮釋必須加以修正,這個空間應當包括精神空間的超越在內。人啊,如果你將自己的精神推進某一間囚室,也便只擁有爬蟲走獸的快樂,離自由的真義遠了去了。
精神的不可囚禁正如天空的不可囚禁,是人類不會退化為動物的保證。在最不自由的環境里,我活得充實,苦難僅限于肉體。有人說這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還有人說是人I生的墮落。我明確告訴他們,我不墮落你們見到的將是一個傻子,精神病患者,眼睛斜著嘴巴歪著那種,這個人將會在你的臉上抓出十道血痕來。
盡管我頭發變白,臼齒松動,臉色難看,有明顯的營養不良癥狀,人反而變得睿智了,畢竟在沒有自由的空間里找到了自由。
多謝老祖宗!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