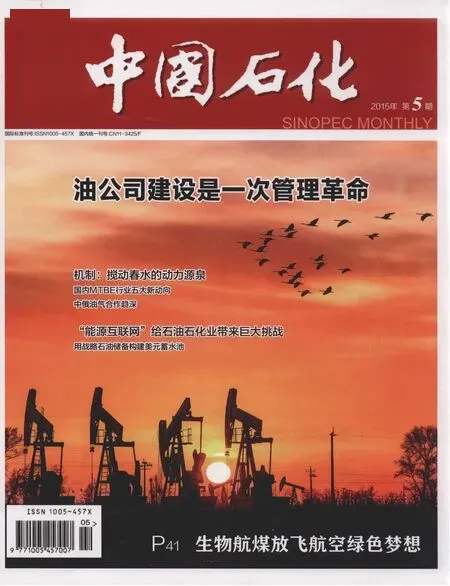用戰略石油儲備構建美元蓄水池
□ 馮躍威
只要美國能夠保證中東等產油地區動蕩且可控,世界各國就需要建立更多的戰略和商業石油儲備,就需要更多的美元沉淀在石油儲備上,也就會有更多的美元成為“死當”。
隨著油價暴跌,不斷有外媒報道中國戰略石油儲備相關狀況。國家戰略石油儲備這一概念也成為此輪油價下跌期的關鍵詞之一。而國家發改委在1月28日發布《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加強原油加工企業商業原油庫存運行管理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建立最低商業原油庫存制度,確保國內石油市場穩定供應。
構建全球性戰略石油儲備
在國際石油市場上,石油供給中斷并不是什么罕見的事情,在二戰后的60年中,全球至少發生過14起。從這些事件的基本特征看,中斷時間持續最長、中斷量最大、中斷量占該時期產量比最大和中斷強度最大的事件都不是發生在人們所稱的1973年和1979年的兩次石油被危機中,只有價格波動最大的那次供給中斷事件是發生在第一次石油被危機中。因此,從石油供給中斷事件綜合影響力看,若沒有美國人在背后運作和支持油價上漲的話,油價幾乎不會有大的變化,進而使供給中斷的國際影響力趨近于零。即使有個別供給中斷事件會出現油價巨幅波動的問題,但若剔除美元超發導致實際購買力下降因素,其中斷效力對國際的影響力也會大打對折。

□ 全球至少有5000億美元沉淀在石油儲備上。李曉東 供圖
進入19世紀60年代后,產油國陸續在歐佩克的支持下,通過國有化運動使西方的國際石油公司失去了對產油國資源資產的控制權和定價權,再加上石油供給中斷的威脅,使國際石油公司特別期待能由政府牽頭組建一個能與歐佩克組織抗衡的消費國的國際組織。在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后,阿拉伯產油國再次使用石油禁運的手段,使部分西方國家的確受到沖擊。恰在此時,為了避免如脫韁野馬般的超發并成為歐洲美元進一步沖擊美國的金融資本市場和對美元霸權地位進行的挑戰,美國政府努力地為這些歐洲美元尋找穩定的棲身之所。而石油禁運、被禁運國的痛苦,以及西方國際石油公司“復仇”的期待交織在一起,讓美國在這一系列事件外發現了可以沉淀超發美元的極佳的“蓄水池”,那就是構建全球性的戰略石油儲備。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在美國等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倡導下,1974年11月,在法國巴黎成立了政府間合作組織——國際能源署(IEA),它隸屬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是一個自治的機構。IEA由28個成員國組成,擁有來自其成員國的190位能源專家和統計學家。其主要職能是協調成員國的石油儲備行動等。它要求成員國持有的石油儲備至少應相當于上年度90天的石油凈進口量,并在出現石油短缺時,該機構在成員間實行“緊急石油分享計劃”,即當某個或某些成員國的石油供應短缺7%或以上時,該機構理事會可作出決定,是否執行石油分享計劃。該機構各成員國根據相互協議采取分享石油庫存、限制原油消耗、向市場拋售庫存等措施。
為此,不少政客甚至是學者對這一機制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將其作用無限夸大,認為一是可以通過向市場釋放儲備油來減輕市場心理壓力,從而降低石油價格不斷上漲的可能,減輕石油供應對整體經濟的沖擊程度。二是可以給調整經濟增長方式,特別是為調整能源消費方式爭取時間。三是可以起到一種威懾作用,使人為的供應沖擊不至于發生或頻繁發生。特別是在歐佩克交替實行“減產保價”和“增產保市場”的政策時,戰略儲備能夠使進口國的經濟和政治穩定,不會受到人為石油供應沖擊的影響。四是為石油進口國對付石油供應短缺設置了一道防線,甚至還有觀點認為戰略儲備真正的作用是抑制油價的上漲。然而,美國人卻在西方主流媒體上這一片贊美的輿論聲中,再次巧妙地以集體石油安全利益為由,完成了對超發美元在石油上的進一步沉淀,并且是猶如“死當”般地沉淀。
戰略石油儲備變成美國治理全球的工具
1975 年12 月,美 國 國 會 通過《能源政策和儲備法》(簡稱EPCA),授權能源部建設和管理戰略石油儲備系統,并明確戰略石油儲備的目標、管理和運作機制。至1980年美國僅建有1億桶的儲備規模,但第二次石油被危機后,到1981年卻猛增到2億桶。盡管這一年的年均原油價格還在每桶37美元的高位運行,可美國購進的戰略石油儲備仍高達每天33.6萬桶。市場越是擔憂伊朗伊斯蘭革命和兩伊戰爭將會造成供給減少,對原油供給缺口擴大的預期就會越大,搶購原油增加戰略石油儲備的欲望也就會越強烈,實際需要的美元現鈔就會越多。進而,可以順利地消化與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并急需擴建戰略石油儲備的OECD國家手中的部分美元現鈔,減少其貨幣與美元之間的匯率戰。歐佩克產油國也因此會受益,造成原油銷售收入增多,回流美國的石油美元增加。最終,協助美聯儲并促進上世紀80年代美元步入強勢軌道,并實現美聯儲將通貨膨脹擠出的貨幣政策目標。
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OECE國家集體幫助美國在上世紀70、80年代“無成本”地建立起戰略石油儲備。到1982年,美國戰略石油儲備增加到3億桶,到1990年接近5.9億桶。筆者曾經對美國戰略石油儲備績效進行過研究,其中,到2011年11月,美國的戰略石油儲備平均購置成本約為每桶28.86美元,而且,美國通過對各種國際事件的運作,使其戰略石油儲備油的采購成本不僅沒有上升,而且還在下降。
從全球石油儲備規模看,美國仍是現今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儲備國。到2011年10月,IEA戰略石油儲備規模達到15.26億桶,商業儲備40.92億桶,總計儲備量為56.18億桶,而美國戰略石油儲備和商業儲備分別是6.96億桶和17.7億桶,分別占IEA儲備量的45.6%和41.79%。因此,僅IEA除去美國后就有2000億以上的美元被沉淀在石油儲備上,若再加上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儲備量,全球將至少有5000億美元被沉淀,像守株待兔的農夫,死守在美聯儲身邊,用血汗掙得的長期處于貶值狀態的美元換得石油儲備,耐心等候著石油供給中斷或油價暴漲的再次來臨。
從對產油國的影響看,自建立了全球性的戰略石油儲備機制后,產油國石油禁運的武功就已“全廢”。即使隨后由美國策動的幾場圍繞著產油國展開的局部戰爭,所造成的每日區區100萬至200萬桶的供給中斷也猶如泥牛入海,在不出半個月或在戰前就可完全被龐大的供給市場填補。即使動用戰略石油儲備也僅是一種象征性的政治宣誓,并順便實現庫存原油的輪換,減少輕質烴逃逸造成的原油品質下降。
石油戰略儲備待商榷
美國用“供給中斷”這等美好的、童話般的預言將全球忽悠并催眠。于是,只要美國能夠保證中東等產油地區動蕩且可控,世界各國就需要建立更多的戰略和商業石油儲備,就需要更多的美元沉淀在石油儲備上,也就會有更多的美元成為“死當”,美國即使再繼續超發美元那也不是個事兒!正因如此,二戰后美國就不斷在中東地區找盟友,扶支柱,滅盟友,建平衡。結果是推翻摩薩臺、逼走巴列維、絞死薩達姆、消滅卡扎菲、攪亂巴沙爾,近期又借IS(為其提供軍火)搞垮了馬利基,美國人很忙!忙的就是要讓更多超發的美元沉淀在包括原油在內的大宗商品等資源資產上,解決企圖對美元霸權構成沖擊或挑戰的貨幣及其國家的威脅。
回望中國,在國人普遍認為中國應該大力構建國家級戰略石油儲備時,美國人還真就躲在壁爐前偷著樂呢。中國若建戰略石油儲備,面對如此巨大的經濟體量,別說90天,就是建立60天的儲備也需要6億桶,即使按每桶50美元計算也最少需要300億美元采購原油。在幫助美國消化了超發的美元,占用了政府可支配資金后,也未必就能換來供給安全。在美國亞太再平衡中,已將60%海空軍力抵近中國部署,一旦發生沖突,首選的打擊目標必有戰略石油儲備。所以,戰略石油儲備安全嗎?有必要做石油戰略儲備嗎?這些問題都值得商榷。
慶幸的是,2015年1月28日,國家發改委發布《意見》,要求建立最低商業原油庫存制度,確保國內石油市場穩定供應。應該說,這是政府在能源安全管理方面向市場化邁進的重要一步。盡管該《意見》還有可完善的空間,但正朝著正確的方向買進,而且是向風險最小的一種儲備方式買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