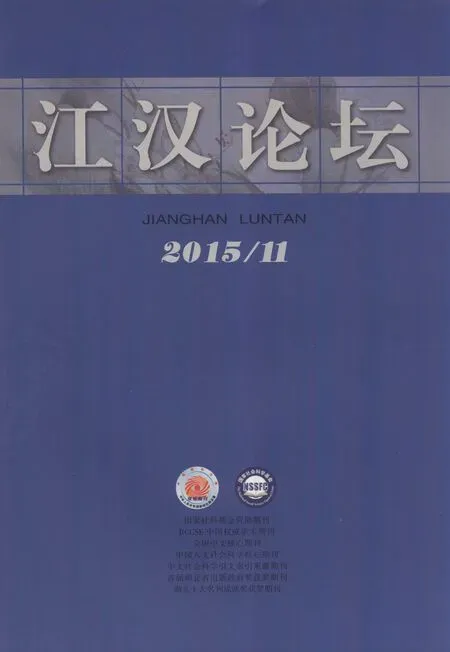論公共決策領域中政府回應網絡民意的法治化*
許玉鎮 肖成俊
我國社會發展轉型期恰逢互聯網普及和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時期,一般作為社交媒體平臺的網絡在中國卻承載著越來越多的政治表達功能。網絡以其低門檻、圈群化、即時互動和裂變傳播的核心特性,打破了公共話語權的壟斷狀態,極大地推進了我國公眾參政的速度、深度和廣度,越來越多的公民力圖通過網絡參政議政、網絡民主監督、網絡群體性意見表達等形式來影響政府的公共決策。那么面對公共決策中洶涌的網絡民意,政府是否應該進行回應?又如何進行回應呢?
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背景下政府回應網絡民意的時代價值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以下簡稱《決定》)將公眾參與列入重大行政決策的必經程序。有參與就應該有回應,政府回應不僅直接反映政府對公眾參與的態度,更反映政府對民眾訴求的態度。美國學者格羅弗·斯塔林認為:“政府回應意味著政府對公眾接納政策和公眾提出訴求要做出及時的反應,并采取積極措施來解決問題。”①我國學者俞可平教授在 《治理與善治》一書中指出,“政府的回應性與政府的責任性關聯密切,是指公共管理人員和管理機構必須對公民提出的要求做出積極和負責的反應。”②我們認為,政府對公民網絡參與公共決策的回應是指:政府在公共決策過程中,對于網民群體所關注的社會問題、表達的利益訴求給予的回答及響應。政府的回應意味著政府對公民參與權的充分尊重和保障,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背景下更彰顯出其具有的時代價值:
第一,政府的回應有利于公民民主政治權利的實現。公民的政治參與權是公民重要的民主政治權利,但在實踐中我國的公民參與有時流于形式。這部分是因為在我國的政治體制下,行政權力主體并沒有接受公民參與的意見和建議的制度性壓力。但我國的公民參與權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黨中央在政治上高度認可的。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引導人民群眾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有序參與國家政治;黨的十八大報告也從協商民主的高度充分肯定了公民政治參與權。因此,政府積極回應民眾網絡意見是對黨的政治決策的落實,對推動公民民主政治權利的實現具有重要價值。
第二,政府的回應有利于激發網絡 “正能量”,促進政府決策汲取民智民慧,實現決策法治化、科學化。網絡參與作為由公民發起的接觸式參與方式,多是針對涉及人民最根本、最直接的切身利益或是特定的公共問題,通過網絡發聲 “不斷增強與各種負責公共項目和政策問題的公共機構的聯系和溝通”③,為決策主體提供民意參考,進而推動相關問題的合理解決。網絡參與順應了政府決策向開放性與參與性轉變的時代要求,為政府在公共決策過程中的價值取舍、利弊權衡等提供了重要依據。
第三,政府回應有利于提高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隨著公民參與政府公共決策活動需求的不斷增加,由政府主導的傳統社會管理運作模式逐漸被打破,更多的公民以及其他社會組織、團體將借助網絡更直接、更有效地參與社會治理。奧斯特羅姆所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論認為:社會治理的主體具有多元化特征,公共部門、非政府組織、企業、社區、權威機構以及公民個人等都可以成為治理主體,各主體之間權力的密切合作有利于共同完成公共管理職能。新公共服務理論也提出,公民不僅僅是選民,也是政府的擁有者和社會治理活動的參與者,政府必須對公民的社會需求無條件回應,向公民提供滿意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網絡的即時性、互動性特點為公眾表達利益訴求、參與經濟和政治生活提供了一個方便快捷的平臺,從而形成了“政府主導,網絡參與,社會監督”的決策模式,是國家管理向國家治理轉型的重要內容。因此,提升政府對社會需求的回應力,實現政府與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是實現善治的最基本要求。
二、公共決策領域中政府回應網絡民意的現狀及問題
1.公共決策領域中政府回應網絡民意的現狀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政府對民意回應經歷六十余載的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信訪制度、聽證決策制度、公示制度等一些政府回應制度規范相繼出臺。尤其是1999年 “政府上網工程”正式啟動以后,公眾網絡參與熱情被極大調動,對網絡民意的回應也作為最具信息時代特征的政府回應方式得到迅猛發展。我們以政府在網絡回應中所持有的態度以及公民網絡參與模式的法治化狀況為依據,將政府網絡回應現狀以四種政府回應方式來體現:
(1)政府主動吸納型回應。指的是政府為緩解社會矛盾,提高立法活動和決策活動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主動創造參與條件,引導公眾借助網絡參與到相關政策制定過程中,并將公眾意志體現在所制定的政策和法律當中。這種政府引導社會公眾“自上而下”有序的參政議政模式,有利于拉近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距離,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正如查爾斯·泰勒指出的那樣: “‘距離’所表示的是政府機關已經與普通公民脫節了”④,縮短 “距離”的最有效途徑就是尊重和保護公民的參與權,提升政治民主化程度。據CNNIC(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統計,截止到2015年7月,我國各級政府門戶網站數量達到82674個,其中絕大部分都在網站首頁設立了專門的意見征集或者政策討論互動專欄。政府借助網絡來征求民眾的意見、建議,引導社會公眾有序參與到公共決策當中已成為普遍作法。自2005年7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網絡征求意見開始,至2014年7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航道法 (草案)》網絡征求意見止,10年間,共有61部通過網絡征求意見的法律草案 (其中有4部為二次審稿);在每年召開的全國 “兩會”期間,中央政府都會借助互聯網設置專欄征求公眾意見、建議,比如 “我有問題問總理”、 “我對兩會有話說”、 “e兩會”等網絡互動品牌欄目。同時,各級領導干部重視網絡、利用網絡的意識也越來越強,通過開博客、微博、微信等形式積極主動與網民進行更為直接的溝通。
(2)政府事后吸納型回應。指的是政府事先并沒有設定議程,而是社會公眾主動借助網絡 “自下而上”表達意愿訴求,并形成公共話語,政府基于此通過制定政策、法律法規或其他方式來滿足公眾的訴求。2003年引起轟動的 “孫志剛事件”發生后,包括網絡媒體在內的許多媒體詳細報道了此事件,并曝光了許多同一性質的案件,一時間在網絡上對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討論甚囂塵上,并很快形成網絡公共話語,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很快廢止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并出臺了 《城市生活無著落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我國當前處在各種社會矛盾的多發時期,公民 “那些受壓抑的情緒是不會輕易自生自滅的,不讓其通過集體、帶點非理性的方式表達出來,它就有可能變成其他形式的破壞社會穩定的行為”⑤。面對洶涌的網絡民意,政府一方面要強化對網絡言論的管理和引導,防止出現網絡 “群體極化”⑥現象;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公民網絡言論權、重視網絡民意,強化對網絡輿情的搜集和應對能力。
(3)政府回避型回應。指的是政府出于壟斷相關信息或逃避責任的目的,通過主動回避或者借助一定的技術手段屏蔽、刪除網絡言論的消極回應方式。有些地方政府在面對公眾合法的網絡參與要求時采取回避的方式,對于公眾關注的信息不予公布或者延遲公布,從而引起不良的社會后果。例如,2013年6月網絡媒體曝光了陜西某縣政府在發布一條處理當地房地產開發商高額利息非法集資一事的微博時,專門在批辦單中強調注明 “積極做好刪帖工作”,消息一出,引起了廣大網民的強烈不滿。“積極刪帖”行為不僅說明政府對網絡輿論影響力的回避和懼怕,也是對公民參與權和知情權的踐踏。這種消極不作為的回應方式,往往會造成相關事件的輿論熱度不降反升,各種謠言、猜測也會隨之傳播,導致政府的社會公信力下降。
(4)政府追責型回應。這是一種特殊的回應方式,是指政府相關部門依據公眾借助網絡所曝光或舉報⑦的違法、違紀等信息,經查證屬實后,依法對相關人員進行責任追究和查處的回應方式。網絡信息傳播的快捷性、公開性等特征,將政府置于公民視野之下,為公民監督權的行使提供了良好的渠道。一項抽樣調查顯示,網民當中非常關注網絡監督功能的比例占到87.9%。網絡渠道作為監督政府及其工作人員活動的 “放大鏡和顯微鏡”,相對于傳統信訪舉報監督渠道更能吸引眼球,引起關注,有些事件能在很短時間內形成社會輿論壓力, “迫使”相關部門快速作出回應。網絡可以將公民的視野觸及到政府工作的各個角落,這不僅提升了社會監督的廣度和深度,也推動了新時期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另一項關于舉報貪污腐敗渠道的調查顯示,74.6%的人會選擇通過網絡途徑舉報,而只有1.27%的人會選擇信訪舉報。同時根據紀檢機關統計,僅2013年我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受理網絡舉報案件就高達386913件。隨著政府反腐力度的加大和對網絡舉報的重視,一些長期得不到處理的腐敗問題一經網絡曝光,相關人員便很快受到了法律的嚴懲,網絡也因此成為 “秒殺貪腐官員”的利器。
2.公共決策領域中政府回應網絡民意存在的問題
網絡參與政府決策的實質是公民群體借助互聯網信息平臺表達利益訴求,進而影響政府決策進程和決策結果,這不但是公民依法行使參與權的表現,也是公民監督政府公權力運行的有效途徑。政府回應則是政府公權力對這種 “影響”作出的回答和響應。網絡參與的興起,對政府的信息公開和政府對民意的回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國務院2013年下發的 《關于進一步加強政府信息公開回應社會關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見》 (以下簡稱 《意見》)強調,依法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是人民政府密切聯系群眾、轉變政風的內在要求,是建設現代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穩定市場預期,保障公民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的重要舉措。但是當前政府信息公開程度以及對網絡民意的回應與公眾期望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具體存在的問題是:
第一,政治動力不足,政府回應缺乏主動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55條規定: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和上一級國家行政機關負責并報告工作。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并報告工作。全國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都是國務院統一領導下的國家行政機關,都服從國務院。”在這種制度下,我國地方政府進行的公共決策活動直接對本級人大和上級國家行政機關負責,而對地方民眾卻沒有直接的政治和法律責任。但在有些國家,如美國,由于各州州長、議員、重要行政官員的當選都跟地方民眾的選票密切相關,所以政府對于公民請愿和訴求的回應是否及時、有效,關系到行政官員的支持率和連任等實際利益,因此,認真做好對公民網絡參與的訴求和利益表達的回應工作是政治體制帶來的壓力,官員們都動力十足。而我國有些地方政府官員面對傳播速度極快的網絡民意時,很難快速作出及時有效的回應,甚至害怕網絡參與會影響上級領導對自己工作的 “好印象”,對網絡意見持抵制態度;對洶涌的網絡“拍磚”、 “吐槽”風聲鶴唳,網民的言論稍一涉及自身利益,就冠之以 “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大帽子, “勤奮刪帖”甚至 “跨省追捕”。這種 “泛政治化思維所導致的運動式治理模式折射著行政執法過程中程序正義和法治精神的嚴重缺失,似乎只要行政行為符合政治需要便可以不受法律和道德約束對行政相對人采取任何手段。相應地,支撐現代文明社會規范行政行為的法律準則被棄之一邊,社會主體可依憑的法律保護徹底失效。”⑧
第二,相關制度體系不完善,政府回應缺少法律、法規依據。法律是治國之重器,完善的法律制度體系是實現善治的基本前提。然而目前我國仍缺少相應的法律、法規等制度體系來為政府回應提供依據和規范:一方面,現有關于政府回應的法律法規、行政規章等的規定較為抽象籠統,執行難度較大。比如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第15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向行政強制的設定機關和實施機關就行政強制的設定和實施提出意見和建議。有關機關應當認真研究論證,并以適當方式予以反饋。那么,適當方式究竟包括哪些方式?什么樣的方式是不適當的方式?沒有研究論證、沒有反饋的應承擔什么法律責任?這些內容都很模糊。再比如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 《意見》,其內容更加偏重于回應平臺和回應機制建設,在責任追究方面只是籠統地強調加強考核力度,加大問責力度,對于回應時效、回應方式、回應責任、回應監督等具體環節和相關責任人應受到的處罰等卻沒有具體規定。缺少明確具體的可操作性規范,政府就可以憑借其在職權范圍內所擁有的自由裁量權,按照自己的意愿來選擇性的作出回應。另一方面,缺少全國統一的、效力較強的政府回應依據和規范。國務院的 《意見》更多的是起到內部指導作用,法律效力弱,很難作為統一的強制性依據。政府回應作為構建服務型政府和責任型政府的關鍵環節,缺少了法律的強制力保障和法律責任的追究,政府回應就很難有效落實。在實踐中,政府回應法律制度不完善,直接會導致政府網站信息發布的“程式化”和回應的 “符號化”,公民在政府門戶網站官民互動專欄中所表達的利益訴求很難得到有效回應,與公民對政府的回應期望嚴重不符。
第三,部分政府官員缺乏法治思維和法治觀念,回應態度偏頗、效率偏低。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 《決定》明確提出要提高黨員干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但在政府回應中,由于部分政府官員法治意識淡薄、法治思維能力較低,在處理一些網絡輿論熱點事件時多采取 “回應有風險,說話需謹慎”的消極態度,雖然政府能很快掌握關鍵信息,但在信息發布過程中多是消極回應、草草應付了事,壟斷相關輿論熱點信息。比如,2013年7月發生在某市的水污染事件,在事件發生近一周后的新聞發布會上,市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一再強調污染源所處位置 “山高路遠”是導致環保部門監管不力的根本原因,然而這與新聞記者的實地調查結果相背離。這種敷衍塞責的回應,往往達不到降低社會事件輿論熱度的回應初衷,反而會使事件輿論熱度再次升高,甚至引起 “民憤”,導致網民所關注的不再只是事件本身,更多的是在討論政府面對和處理相關問題的態度和職責。2014年4月某市發生了群眾游行示威抗議政府修建殯儀館事件,根源在于市政府沒有充分利用門戶網站事先征集公眾意見,等到問題出現后,政府才以官方回應的形式開始網上民意征集工作。可見,即使設置了政府網絡參與平臺,但某些政府門戶網站的 “民意征集專欄”沒能真正成為政府對一些項目、決策的意見征集和回應渠道,卻成為政府表現政績的擺設和應付電子政務評估檢查的形象工程,使較為健全的網絡參政議政平臺被決策部門有意無意地排斥在決策體制之外。究其原因還是相關決策部門領導缺乏對網絡民意的正確認知,決策過程仍是 “閉門造車”,排斥與民眾的互動和意見交流,缺乏法治思維,不善于運用法治方式開展工作。
三、政府回應網絡民意的法治化建設
在我國目前政治體制下,完善政府回應網絡民意制度建設首先應推進政府回應的法治化建設,建立規范化、程序化及公開、透明、公正的政府回應法律機制。具體應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第一,加強立法,保證政府網絡回應工作有法可依。我國現階段關于網絡參與政府決策回應的相關核心法律缺失,這直接導致政府對公民網絡參與的回應活動的具體操作規范沒有明確的依據可循。互聯網的迅速崛起將人類帶入一個全新的信息時代,同時也為政府提出了諸多亟待解決的新課題,其中就包括如何建立健全有關政府網絡回應的法律法規體系,以適應新時代公民網絡政治參與的要求。黨的十八大強調,要加強網絡社會管理,推進網絡依法規范、有序運行,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更是將網絡列為重點立法領域,強調加強網絡立法,完善網絡社會管理,規范網絡行為,習近平同志在接受美國 《華爾街時報》書面采訪時亦強調互聯網不是 “法外之地”,同樣要講法治。這些都凸顯出政府回應立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截止到2014年底,雖然我國已相繼出臺關于網絡和網絡空間管理的規范性文件約190個,但對于政府網絡回應的立法還存在諸如法律層級較低、約束力不強、核心法律缺失等問題。因此,政府回應的立法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要提高立法層次,盡快出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網絡管理法律和相配套的行政法規,細化回應時效、回應程序、回應方式、回應內容、回應結果、回應監督的具體行為規范,強化對政府網絡回應失職的法律責任追究;另一方面,要嚴格遵循網絡回應的立法原則,一是堅持回應時效原則,即政府應在合理時間內回應。二是堅持回應內容針對性原則,即政府的回應不能顧左右而言他,回避主要矛盾,而應實事求是,切中要害。三是堅持回應方式公開透明原則,政府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如網站、報紙、電視、新聞發言人等方式公開透明回應網絡民意。四是堅持回應效力權威性原則,政府回應是政府公信力的體現,不能朝令夕改。
第二,加強政府網絡回應的執法保障。網絡的勃興以及網絡不當行為的存在促使政府網絡管理權限的產生。我國公民的參與權和知情權均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護,法律在尊重公民正當參與權、知情權等權利的同時,也應對公民的參與渠道、參與形式和言論表達的方式內容等方面給予規范,政府網絡回應質量的提升,是以公民網絡參與的高質量為前提的。對于一些網民惡意散布謠言、混淆視聽、侵害他人權益、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行為應依法追責,為公民參與政府決策創造良好的網絡環境。但正如孟德斯鳩所言, “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一條經驗。”⑨網絡的發展對傳統的政府管理行為模式提出了挑戰,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員濫用職權,限制網絡民意表達的情況時有發生,政府網絡回應的執法保障要從政府行使網絡管理行政權的法律依據、程序和方法、內容、對象、效力等方面對政府網絡管理行為進行規制,既要保障政府的網絡管理職能,又要約束政府違法行政壓制網絡民意的行為。
第三,建立政府網絡回應的司法保障機制。“無救濟即無權利”,公民權益受到侵害有獲得司法救濟的權利是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基本特征。應建立完善的政府網絡回應司法保障機制,通過立法明確規定政府回應法律責任追究的主體、客體和范圍以及相對應的執行細則,確保權責對應、有責必究。一方面,應建立政府回應法律責任追究機制。政府作為回應主體必須依法將公民參與引入到公共治理的活動過程中,保障公民合法的網絡政治參與行為不受公共權力的任意干預,并積極主動對社會公眾的利益訴求和意愿給予及時、有效地回應,對于被社會大眾關注的重大輿論事件或公民自愿表達的合理訴求,政府沒有給予回應的,應當承擔相應責任,在法律框架內追究相關責任;另一方面,從司法訴訟制度上完善相應政府責任追究機制。2014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修改行政訴訟法的決定,修改后的行政訴訟法擴大了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明確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當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文件規定了政府回應義務時,如信息公開,公民可以就政府不回應、不公開等行為提起訴訟,法院應該受理。
注釋:
① [美]格羅弗·斯塔林: 《公共部門管理》,陳憲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頁。
② 俞可平: 《治理與善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版,第12頁。
③ [美]約翰·克萊頓·托馬斯: 《公共決策中的公民參與: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與新策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頁。
④ [美]查爾斯·泰勒: 《公民與國家之間的距離》,載汪暉、陳燕谷主編: 《文化與公共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99頁
⑤ 王四新: 《表達自由——原理與應用》,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頁。
⑥ “群體極化”這一概念是由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和政治系KarIN·Llewellyn法哲學講座教授凱斯·桑斯坦在其著作 《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中提出的,他指出: “群體極化的定義極其簡單,團隊成員一開始即有某種偏向,在商議之后,人們朝著偏向的方向繼續移動,最后形成極端的觀點。”
⑦ 2013年9月2日,中紀委監察部網站正式開通,英文域名為www.ccdi.gov.cn,網站接受網絡信訪舉報,首頁顯著位置設置12388網絡舉報板塊,方便群眾順暢、安全地舉報監督。
⑧ 蔡立東: 《閑置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收回制度的司法實證研究》, 《法商研究》,2014年第3期。
⑨ [法]孟德斯鳩: 《論法的精神》上冊,張雁深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