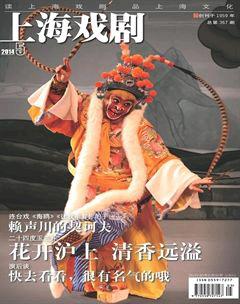尋找桃花源
岳上鏵

戲劇的本性在于溝通,溝通編劇、導演、演員和觀眾,溝通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人與社會,在心靈的交互中,溝通讓情感得到釋放、心緒得到宣泄。從這個意義上說,戲劇對調節和引導人自身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本文試圖以臺灣導演賴聲川的話劇《暗戀桃花源》為例,從戲劇的本性出發,來探討戲劇在教導人的全面發展方面存在的可能性。
一.戲劇:溝通的藝術
對戲劇本質的界定,是評論界關于戲劇本體論孜孜以求的一個問題,這也是難以一錘定音能達成一個既定標準的根本難題。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美學》中指出:“戲劇的動作在本質上須是引起沖突的,……這種沖突既要以符合人物性格和目的的方式產生出來,又要使它的矛盾得到解決。”他把戲劇要素之一的“沖突”的地位和價值得到提升,將戲劇看作是一種描述人和人之間意志對立的藝術形式。而阿契爾在《劇作法》中闡述:“我們可以稱戲劇是一種激變的藝術,就像小說是一種漸變的藝術一樣。”他認為戲劇矛盾不是一味地對立沖突的,而是在相互融合、相互轉化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激變效果。德國的尤里烏斯·巴布的“三位一體說”則認為劇作家、演員和觀眾是產生戲劇缺一不可的三個要素。綜上所述,對戲劇本質的闡釋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在時代的輾轉流變中,不同的審美選擇和創作需求賦予戲劇極其豐富的思想內涵和價值尺度,推動戲劇不斷地向前發展。
戲劇是一種觀演結合的綜合藝術,是一種精神溝通的藝術。弗洛伊德在對人格結構進行分析時指出本我、自我和超我這三個概念,取其字面概念,我們可以暫且把屬于精神的人的“靈”叫做“本我”,而把現實世界中的人叫做“自我”,人性最具和諧的狀態是人的“本我”和“自我”二合為一的交融狀態。反觀現實,人的“本我”和“自我”存在著較嚴重的背離。現實的重負讓人越來越偏離自身的“本我”,而為現實的“自我”忙碌奔波,在重復單調的工作和生存競爭面前,“自我”慢慢膨脹,“本我”慢慢縮小,乃至于“本我”被壓制到最小,獨存“自我”。正如魯迅的《傷逝》所描繪的,涓生和子君因彼此的“本我”而結合,但日常生活的瑣碎和繁雜卻把他們原來的“本我”消磨殆盡,只剩下困頓、迷茫、無奈的現實“自我”,無休止的爭吵抽空了曾經彼此愛的信念,空虛無聊的現實處境剝離了他們愛的理想光芒,在相互的責怪和質疑中,愛慢慢凋零。現代的我們,似乎是 “涓生”和“子君”,心靈已被現實生活擠壓得無法承載更多,勇氣也漸漸失去。
戲劇提供情感釋放的空間,搭建心靈溝通平臺。劇作者和導演對劇作精神的闡釋和構思、演員對角色的揣摩演繹、演員間的相互配合和體驗、演員的表演對觀眾的感染,觀眾對演員及其角色的接受等等,這一系列的情感交流的完成,是基于導演、角色、演員和觀眾之間的“本我”的一種無等級、無差別的共鳴和契合。從導演到角色到演員到觀眾,再從觀眾反饋到演員,“本我”在相互傳遞、感染、轉換中釋放、蔓延、擴大,于是,彼此“本我”與“本我”之間的互動和交融,心靈碰觸和叩響在劇院悄然發生。享受戲劇的我們,不自覺地重拾心靈的“本我”,召喚和回歸自身“本我”。戲劇的魅力帶來精神體驗,觸及心靈原始的感動和震撼,在美善的洗禮中尋找到曾經失落的遙遠之夢,在歡笑和哭泣中,構建起屬于心靈的神圣殿堂和精神的美好家園。
二.戲劇:人的舞臺
人的本質在于其社會性,人的本能存在于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之間相互交往、相互溝通的錯綜關系中。在這種關系中,人自身得以確立,而溝通交往則成為關鍵。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之間也需要相互溝通、相互交流、相互寬容。戲劇所特有的溝通功能對人自身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此,謹以臺灣導演賴聲川的話劇《暗戀桃花源》為例,從戲劇的本性出發,來探討戲劇在教導人的全面發展方面存在的可能性。
《暗戀桃花源》講述的是《暗戀》和《桃花源》兩個故事,演繹兩個看似不同而又相似的人生的故事。《暗戀》中重病的江濱柳刊登尋人啟事,想在臨終前見到四十多年前失去聯系的昔日戀人云之凡,但見到了戀人時卻“相顧無言,卻唯有淚千行”。人世滄桑留給人的終究是無奈。《桃花源》中的老陶因為遭妻子春花嫌棄,得知春花出軌后,傷心出走,卻意外進入世外桃花源。當他想接妻子同來桃花源時,卻發現她和袁老板陷入日常爭吵中,老陶再次無奈離開。風格迥異的兩個故事整合滲透后,達到全劇在情感實質上的統一,形成異質間的同構。此劇的成功因在戲劇內蘊的豐富性和戲劇技法上的巧妙性,淋漓盡致發揮溝通特質。溝通把戲劇的導演、演員、舞臺、觀眾整合在一起,溝通把我們與自己、他人和社會扭結在一處。
1.人與自我的情感溝通
人最不能認識自己,最不了解真實的自我。所以,尋找自我是漫漫長途,是艱難的精神苦旅,始終帶著對自我本體的拷問。人的一生是自我的求索史,社會歷史也是一部人追究自身本真的探索史。人對自己的尋找,周而復始,循環往復。
貫穿《暗戀桃花源》始終的主題是“尋找”。《暗戀》的導演尋找曾經遺失的記憶;江濱柳尋找云之凡;老陶尋找桃花源;無名的少女尋找劉子冀。所有的人都在尋找,但是都失落:愛情失落于時代,理想失落于現實生活。江濱柳保存著對昔日戀人的夢,夢讓他對生活充滿期待和希望。在《暗戀》的第二場中舞臺場景:四十年前的上海外灘公園和四十年后的臺北醫院病房,一個現實中的江太太,一個心中的戀人云之凡。劇作安排江濱柳站在現實和內心的邊界處,煎熬掙扎……結果江濱柳走向了他心中的那個夢。《桃花源》,老陶想帶春花一起過桃花源的幸福生活,看出老陶身上存在桃花源孕育而成的美好、和諧的一種人性狀態,正是人自我實現的一種理想狀態。
現實讓我們愛情、理想、人性失去了憧憬。當我們用鄙夷的目光來褻瀆美好的情感時,也封閉著心靈、扼殺著靈魂。正如《暗戀》里的那個小護士始終無法理解江濱柳和云之凡的愛情一樣,我們漸漸地在成為愛情的旁觀者。類似《暗戀桃花源》的戲劇開啟了封閉的心靈,我們開始與自己的“本我”對話,與自我的心靈交談,慰藉心靈深處最本真的存在,宣泄我們一再被抑制、被忽視的情感內在。endprint
從戲劇中,人能正視心靈,面對情感需求,憧憬因為現實而不得不放棄的某些理想。在心靈和情感的釋放中,戲劇能平衡我們的身心發展,減少對現實物欲的依賴,避免我們淪喪為純粹的物的追逐者。
2.人與他人互助的交流
人和人的關系就像一張蜘蛛網,每個人都是這個網上的一個小支點,支點與支點之間的相互連接,依賴的就是一種互助合作的精神。合作讓人和人之間的距離拉近,而溝通則讓合作成為可能。
《暗戀桃花源》展示了人與他人之間的這種交往關系。導演會因表演沒有達到他的要求而多次打斷表演并解釋角色所處的時代背景及其性格特征;《桃花源》中,老陶一再地強調自己排戲不能受到別人的干擾;兩個劇團之間關于排戲場地無法達成一致協議而產生矛盾等等。在戲劇過程中出現的導演和演員之間、導演和幕后工作人員之間、演員之間、演員和觀眾之間的溝通錯位,可能難以達成預期目標的事實。這種戲中戲的方式,展露原生態的戲劇技巧,可見戲劇的溝通特性不斷融合的實踐過程。溝通障礙的出現,是劇中人自身對戲劇所尋找的愛和理想的精神實質的消化不良,是劇中人各個小“本我”在向戲劇總精神這個大“本我”靠攏的過程中所遭遇的不協調。尋找理想和美,既是小“本我”相互合作對大“本我”的集體尋找,也是小“本我”各自對大“本我”的尋找,只有在不斷的磨合、溝通和合作中,大小“本我”才能集體走向歸一。兩個劇團從互相爭場到同舞臺排戲,接著兩劇團達成諒解,輪流使用舞臺,最后兩劇都順利完成。由人和人之間的溝通諒解,到人和人的合作互助,再到戲劇和戲劇的共通交融,兩個劇團逐步完成了對人、戲和“本我”的和諧構建,使悲劇《暗戀》和喜劇《桃花源》超越時空、超越既定的戲劇形式而完美結合,共同傳達人心靈中同樣的期盼和希望。
話劇與現實生活中人際溝通是相契合的。交流和合作中消除誤會、達成共識。每個人或悲或喜,或哭或笑,各自演繹不同的故事,卻又都四處尋找曾經遺失的同樣的心靈空間。溝通中了解別人,認識自己;合作中承擔得失,編織理想。在反復的溝通和合作中,釋放心靈,宣泄情感,人際關系蜘蛛網得以不斷壯大。現實中的我們卻更多冷漠,缺少溝通,吝嗇付出信任和真誠。劇場讓我們打破各自的心靈禁區,走出彼此的封閉空間。參與戲劇,讓我們懂得溝通的魅力和合作的力量,使我們成其為一個完整的人。
3.人對社會的現實把握
江濱柳說:“在那個大時代中,人變得好小、好小;到今天這個小時代,人變得更小了。”面對現實,人是脆弱不堪的,歷史的進程不會因生命的消失而停止,現實生活不會為人的自由意志而牽絆,在現實時代面前,人注定是悲劇的主角。
江濱柳說的:“這么大一個上海,我們能在一起,一個小小的臺北卻把我們給難住了。”替代抱頭痛哭只有簡單的問候,云之凡一句“我大哥說,不能再等了,再等就要老了”涵蓋了所有的心酸和無奈。江濱柳喚回了曾經的深情,卻無法喚回現實的人生。現實總是讓人生充滿無奈。現實的一切已經把昔日的激情消磨了,日常瑣碎的事務嘲弄著愛情。春花和袁老板就如同是古代版的《傷逝》的涓生和子君。他們在憧憬理想時,充滿無限的力量,卻在現實的考驗下不堪一擊。從桃花源返家的老陶,對春花抱有同情還是慶幸。現實像一把刀,赤裸裸地,剝離了人所有的希望。
現實不是理想,所以暗戀以遺憾告終,愛情以無奈結束。桃花源失落了,暗戀失落了,劉子冀失落了。無法改變現實的殘酷,卻可以堅守自己內心的一片晴天。江濱柳還保存著自己的夢,白發導演還珍藏著他的回憶,老陶堅決地踏上了重返桃花源的路,無名少女還在一直找尋她的劉子冀。雖然可能再次要遭遇現實的失落,卻保存一份感動和想象,分外的美好和珍貴。
《暗戀桃花源》劇終,兩個導演情不自禁地相互依偎著,慢慢走遠;那個一直不懈尋找的無名少女,也沒有找尋到她的劉子冀,她拾起散落在地上祭奠死人的紙錢,向空中飄灑,祭奠失落的理想。失落于現實我們不應該放棄理想。當直面現實時,戲劇所給予我們心靈的是,多一點的從容和多一點的釋懷,對于現實,對于人生,對于自我。
戲劇讓人與自我、他人和社會真誠對話,讓人更客觀、正確地看待自己、他人和社會。在平等的心靈感受中,戲劇讓我們的情感契合、達成互諒、理解和寬容;在精神的交互中,戲劇滿足我們心靈的慰藉,彌補我們情感的空缺。從心靈開始,戲劇溝通你、我、他。無怪乎,俄國的別林斯基這樣呼吁我們:“啊,去吧,去吧,去看戲吧,如果有可能就在劇院里生,就在劇院里死”。
(作者單位:平頂山學院文學院)
歷代昆曲家都把唱準字音放在首要地位,常把唱曲稱為“度曲”,“度”有按照規矩的意思。曲家也常把唱曲比作說話,李漁在《閑情偶寄》中講:“學唱之人,勿論巧拙,只看有口、無口。聽曲之人,慢講精,先問有字、無字。字從口出,有字即有口。如出口不分明,有字若無字,是說話有口,唱曲無口,與啞人何異哉!”1可見,若是誰唱的字沒有被聽曲的人聽懂,就與啞巴沒有分別。
昆曲的語音是一種美化了的語音,并不是哪一種方言或官話。漢語語音一直都處于一個流變的過程之中,昆曲的語音也在變化。明代唱曲有著“南遵洪武,北據中原”之說,到了清代乾隆年間,昆曲的藝術理論達到相對完備的境地,曲家唱曲都按照沈乘麐《韻學驪珠》中的標注來唱。
昆曲的字音用“反切”來確定。清代李光地《音韻闡微》中把“反切”解釋為:“上一字定母,下一字定韻。”“定母”即定聲母,“定韻”即定介母和韻母。不論是昆曲清唱還是劇唱,唱曲者首先都要把曲文的字音交代清楚。清人徐大椿在其《樂府傳聲》中講:“一字之音,必有首腹尾,必首腹尾音已盡,然后再出一字,則字字清楚。若一字之音未盡,或已盡而未收足,或收足而于交界之處未能劃斷,或劃斷而下字之頭未能矯然,皆為交代不清。” 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