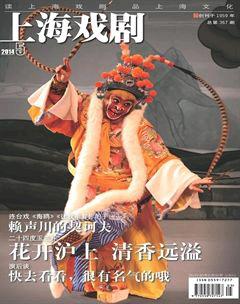昆曲字音芻議
周丹
曲家習慣于把字音的開始部分稱為字頭,即聲母;把字音的后半部分稱為字腹和字尾,即韻母。字頭在傳統上稱為“五音”,這是借用了聲律名“宮、商、角、徵、羽”等,來區別喉舌齒牙唇諸音阻部位。“雖分五層,其實萬殊,喉音之深淺不一,舌音之深淺亦不一,余三音皆然。故五音之正聲皆易辨,而交界之間甚難辨。”3實際上,音阻部位并不能劃分出明確的界限來。《韻學驪珠》把字頭分為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七類,比較符合口腔發音部位。唱字頭時,除了要把發音部位找準確,還要分清楚清濁。昆曲中所謂的“清音”、“濁音”是指聲母的“送氣”與“不送氣”。
《樂府傳聲》中講:“喉舌齒牙唇,各有開齊撮合,故五音為經,四呼為緯。”4四呼是行腔的主要韻母音。韻母有單韻母、復韻母兩類。復韻母又有兩個元音以上組成的韻母和元音后帶有輔音的韻母之分。復韻母中發音較響的主要元音和單韻母,往往都是行腔或延長音中的主要元音,依其發音口形曲家一般粗分“開、齊、合、撮”四類,即“四呼”。
字音尾部的收音亦為曲家所重。古代曲韻家把收音分為七類:收鼻音、收抵顎音、收閉口音、收噫音、收烏音、收迂音、直出無收(a、o、e、i、er者)。昆曲演唱講究吐字有余韻,指字尾之一點收音,唱時不可重濁,貴在若隱若現,方能雋永。
昆曲中還存在尖團音,凡以z、c、s和韻母元音或介音i、ü相拼的字叫尖音;凡以j、q、x和韻母元音或介音i、ü相拼的字叫團音。另外,有清曲家認為昆曲是“無一字無來歷,無一字不講究”,不存在“上口音”;而有藝人則認為昆劇語音中存在“上口音”問題,昆劇中的“上口音”與京劇相仿,“是指在傳統的唱曲與念白中,用北音念作南音時發生音變的字。它是某種古韻異讀,受到方言的影響,成為曲韻中特殊的讀音、咬字的方法”。5
昆曲的字音在不同的地域或群體中存在著不同的“標準”。自魏良輔創立“水磨腔”以來,很多曲家都堅持唱曲應該“土音剔凈”,就連文人作傳奇,都強調少用方言,因此,唱曲應該嚴格遵照韻書的注音來唱。可是,也有一部分人認為昆曲既然起源吳門,就應該盡量保持其吳語音系唱念的特色。盡管昆劇在明晚期成為了全國性劇種,并非吳中地區地方戲,然而昆曲形成于吳中地區,通過長期藝術實踐,歌唱與念白勢必受到了吳語的深刻影響,漸漸形成特有的風格。帶有吳語口音的中州韻念法,南曲界稱為“中州韻姑蘇音”。有關昆曲語音“標準”的爭辯至今仍然存在,即使是在昆曲清唱界也是如此。昆曲起源于吳中地區,后來漸漸脫離地方性而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劇種。筆者認為,從“根源”上說它應該帶有吳儂軟語的色彩,而從藝術的“高度”上講,它應該“土音剔凈”。
昆曲清唱家通常依靠查閱韻書來確定曲詞的讀音,卻未必能完全擺脫方言的影響。這好比會查閱字典、懂得漢語拼音方案的人說普通話時就未必不帶口音。韻書都是以反切法來注解漢字的字音,然而,這種方法并不便利,而且很容易發生差錯。因此,前代的曲律家就提出許多和音韻學有關的理論,如“五音四呼”、“四聲經緯”等等,以便唱曲者更容易掌握正確的字音。用反切法注釋字音還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如果讀不準用以注音的那兩個字,那么被注的字音也就讀不準。在韻書中也存在兩個字互為對方注音的情況,如果遇到這樣的字,就只能通過韻書中相鄰的字來推斷那個字的讀音。此外,韻書也有標記得不正確之處。比如,《韻學驪珠》的東同韻部中,“容”(魚宏切)屬“撮口”,但與之相對應的去聲字“用”(浴橫切)卻標為“滿口”,后者有誤。從《韻學驪珠》中字的排列方式,還可以發現其“開口呼”、“合口呼”等未必與現代音系完全一樣。由于反切法注音還是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曲家雖然懂得關于昆曲字音的理論,但在實際歌唱中,可能不同的曲家通過韻書“揣摩”出的字音就會有差別。再者,語言本身就處于一個動態之中,并不是凝固不變的。一般人通過韻書查字音,也都是以各自掌握的語音來“切音”。在普通話沒有推行之前,曲家可能也都是以自己掌握的語音來“切音”,這就很容易帶有一些方言色彩。
在很多藝人的腦海中,昆曲字音并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藝人很少通過查閱韻書來確定曲詞的讀音。《中原音韻》刊行之后,很少有戲曲藝人參照它來唱曲。“中州韻”是個籠統說法,在戲曲藝人中,更沒有一種公認的明確規范。藝人的發音吐字主要依靠師傅的口傳心授,他們的發音與各自籍貫、師承等有直接關系。此外,由于一些藝人兼演昆劇和京劇,他們唱昆曲的發音可能會受到京劇字音的影響。有位曾經演過京劇的昆劇演員給筆者講解昆曲字音時,就說到某字當歸為“十九韻”、某字當歸為“十三轍”。他所說的“十九韻”是指《中原音韻》中的十九個韻部,“十三轍”是京劇的曲韻,即十三個韻部。由此看來,這位演員是把昆曲的字音和京劇的字音混為一談了。
語言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進行著程度不同的演變,昆曲的字音也會隨之發生一些變異,很難完全遵循“古法”。如《長生殿·聞鈴》【武陵花】中“重疊”的“重”字,在韻書中標為“撮口”,與現代語音差距很大,只有少數曲家和演員把“重”字唱成“撮口”,大部分唱曲者還是按現代語音的發音來唱的。因此,唱曲者對字音的取向不同會使得他們在吐字發音方面存在差異。
徐大椿在《樂府傳聲》中講:“凡唱北曲者,其字皆從北聲方為合度,若唱南音,即為別字矣。況南人以土音雜之,只可施之一方,不能通之天下。同此一曲,而一鄉有一鄉之唱法,其弊不勝窮矣。”意思是唱北曲就不能用南音,否則容易使聽曲的人發生誤解或聽不懂曲詞。徐大椿的這種觀點與魏良輔提出的“南曲不可雜北腔,北曲不可雜南字。”的說法相一致。但是他又說:“凡北曲之字,有天下盡通之正音,唱又不失此調之音節者,不必盡從北字也。……若必盡從北音,則唱者與聽者,俱不相洽,反為無味,譬之南北兩人,相遇談心,各操土音,則兩不相通,必各遵相通之正音,方能理會,此人情之常,何不可通于度曲耶?但不可以土音改北音耳。” 徐大椿也把唱曲比作說話,認為南方人與北方人交談時不能說各自的方言,否則就都聽不懂對方說話,而應該說彼此都能聽得懂的音,這樣才能良好地溝通和交流。唱曲也是如此,若是聽者聽不懂唱者歌唱的曲詞,那也很掃興。所以,只要唱曲者不用“土音”改“北音”,聽曲者基本能聽懂曲詞內容,也就不必對唱曲者的發音過于苛刻。
(本文作者為天津工業大學人文與法學院講師)
1.清·李漁:《閑情偶寄》,《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七》,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101頁。
2.清·徐大椿:《樂府傳聲》,《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七》,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 第170至171頁。3.同上書,第161頁。
4.同上書,第162頁。
5.游汝杰主編:《地方戲曲音韻研究》,商務印書館2006年5月,第61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