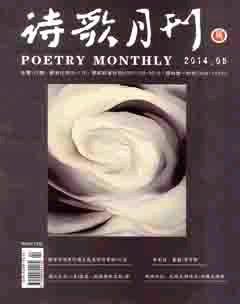紀小樣的散文詩
紀小樣
孤峰頂上
“這里真冷!”“我們這里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聽見江底傳來屈原與李白的對話。
孔丘追著一只青蛾來到了泰山之巔;坐在鯤魚之上呵呵大笑的莊子說:“頂上的那坨大鵬鳥的排遺比任何一場雪還冷絕!”
我亦來此,發現有人先我趺坐;我便蹲跨,在孤峰頂上。沒有任何野獸可以跟我說話;我先用霹靂清洗自己的耳膜,他便幽幽訴說:“考古學家曾經在火成巖的隙縫中挖出來一個笑話——只不過是,大禹對著大地撒尿,竟被人間傳說成天女散花。”他說他也曾經是一個詩人,但卻忘了眼淚的滋味,如果我可以給他一張護照,他就可以到我的詩中來哭!
蹲在孤峰頂上,胯下確實有一點微涼,身上的這一襲破掉的灰色長袍比任何一波白云還要赤裸,所幸,隨便一呵氣就是彌天大霧,而一垂眼,就有“不竭/不潔的智慧”從我眼眸順著黃河的河道奔涌而出……。
呵!所有的呼吸都被誤解為雷聲,我只好繼續蹲著,把一個噴嚏,再忍千年。
真癢啊!感覺無數蛇竄的閃電在我的指尖急欲抽長——而我堅持,緊緊握著拳頭……
雕刻,家
接近子夜。疲憊的雕刻家手握滿是石屑、石粉的刀在工作室里小寐,他突然被一片身旁的啜泣聲驚醒。
雕刻家放下手上的刀,尋找聲音的來源,最后才發現,那聲音來自于一顆日前剛破斧的石頭;不曾有過這種經驗的雕刻家立刻好奇地問:“你,為什么在哭?為什么要哭呢?”
石頭回答:“我哭——因為,因為你不是我想遇見的那個人;我哭——你的刀法太凌厲,雕不出我溫柔的心;我哭——你的刀上、手上沾滿石頭的血;我哭,你不是,不是那一個可以把我完整從石頭里捧出來的人。”
雕刻家聽著……聽著……也哭了,他喃喃白語:“我這大半輩子,算是白活了;現在,我盈耳聽到的是一座一座又一座比五岳、昆侖山脈還重的哭聲……。謝謝你告訴我,讓我知道這一切。雕刻了這大半輩子,我只雕出自己眼角的風霜以及額前的皺紋;為了不再聽見更多你們石族的哭聲,我想就此封刀了!”
想不到哭泣的那顆石頭竟然跳上雕刻家的工作桌,說:“請你繼續雕刻我吧!我已經等待了千萬年——姊妹們總是在錯誤的時間遇上錯誤的人——至少,你是千萬年來唯一聽見我的哭聲的人;請你為我拿起刀吧!”
在子夜,失眠的雕刻家流著淚看著流血的雕刻刀將石頭一路愛撫下去……蜿蜿蜒蜒雕出了,黎明。
一顆荒蕪空漠的腦袋
白天,我把頭租給思想;夜晚,我把頭借給了夢。
思想制造出千萬噸的光,夢把它們沿著密如蛛網的腦血管偷偷運走。
夢中,我確實看見:我的頭把自己塞在思想絕對尋覓不到的陰暗角落,偷偷地哭……
愛的同義復辭
我愛你;直到虎狼脫卸它們的皮毛,變得像綿羊一樣,雪白可親。
我愛你;直到鷹鷲垂下它們的翅爪,變得像和平鴿一樣的優雅溫馴。
我愛你;直到鯊鱷遺忘牛也們的銳齒,變得像……一樣的……
(腰部以下的立法院曾經如此慎重地敲下議事槌,三瀆通過:我愛你!)
是的,你應該知道“我愛你”比土地寬廣。比天空還藍。比海洋還深。
但你不該,不該在月黑風高的夜晚,用那稀薄的月光在自己藍色的恥骨上刺青……你忘了(而我好像突然記起):狼是有爪牙而鷹是有利喙的。
——我不知道為什么當時我可以一邊微笑一邊將你的骸骨收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