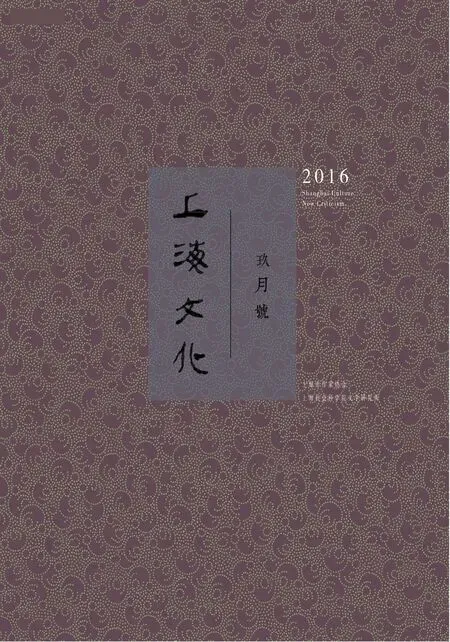拱廊、商品與希望意象
蔣 雯
?
拱廊、商品與希望意象
蔣 雯
一
拱廊街是奢侈的工業的一個新近發明,它們蓋著玻璃棚,大理石鑲嵌的走廊延伸到整個建筑群中,而這些建筑的主人則聯手從事這些企業。這些走廊從上面采光,兩側是最高雅的商店,所以,拱廊街就是一座城市,一個世界的縮影。
沒有什么比拱廊街更能代表19世紀上半葉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盛世了。它在20、30年代達到全盛,一度被視作資本主義商品的廟宇。
拱廊街的繁盛一時,本雅明將之歸結為兩個原因:紡織貿易的繁榮和鋼鐵在建筑中的廣泛使用。拱廊街的建造依賴于社會生產力和技術的發展,它將最新式的材料和建造技術集于一身,“以鋼鐵去建造拱廊街、展覽館、火車站這些供人們穿行的建筑”,并且,拱廊街還是第一個安裝汽燈的地方。
可以說,拱廊街的興建與繁盛,是社會生產和商品消費的必然結果,同時,它也凝聚了一整個時代人們對商品世界的全部理想,這點從它的建筑材料和結構上就可見一斑。以鋼鐵和玻璃為主體的拱廊街成為通往商品夢幻仙境的通道,從中,本雅明既看到了拱廊街作為通往商品夢幻仙境的通道的空間隱喻,也看到了一整個時代投注于拱廊街之上的集體無意識。
首先,拱廊街的建造得益于鋼鐵和玻璃的廣泛應用,鋼鐵的結構支撐透露出“當今建筑的真正美學體驗,透過懸在空中的鐵網柵格可見景物一一掠過——船只、海洋、房屋、桅桿、風景、海港”,就像埃菲爾鐵塔由無數鋼鐵零件和鉚釘裝配而成,文學和藝術追求的拼貼與蒙太奇的手法,早在19世紀的建筑中就運用得駕輕就熟了。那不勒斯的“多孔性”在世界之都巴黎表現為拱廊街、埃菲爾鐵塔、歌劇院和火車站。本雅明敏銳地發現,整個巴黎城的結構不再追求同一的完整,而是趨向于碎片化的拼貼,趨向于分子化的個體流動和整體上結構性配置的宏大與壯觀。當資產階級個體越來越傾向于退回個人反思,而工業化大生產又必然要求群體性的配合與集結,作為19世紀現代之都的巴黎,包含著個體與總體、同質與異質、流動與穩固的多重悖論,一方面,它最大限度地分隔開公私領域,與此同時,商品的本性又要求將“可見性”作為一種“必需的美德”。因而,在本雅明眼中,鋼鐵結構支撐起像拱廊街這樣的龐大建筑物的同時,也支撐起了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和消費文化的集體無意識。
鋼鐵的拼貼結構使建筑“失去原本各自獨立的清晰輪廓”,制造出一種含混和眩暈的視覺經驗。若想將這種城市景觀盡收眼底,“那必須是個不易眩暈的人,一個獨立的,并且,在需要的時候,一個單槍匹馬的工人”。這種景觀在鐵網柵格的間隙,制造出視覺的斷裂和碎片,同時,它又將自身設定為一種可以允許隨時通過和滲透的多孔結構,制造出一種空間的含混,室內與室外的模棱兩可。
對全景圖的興趣是在于看見真實的城市——城市的室內。而真實就是站在無門窗的居室內,同樣,拱廊街也是這樣的無窗之室。由(拱廊街)穹頂的玻璃向下看就如同從車廂上面向內部看,但如此卻完全看不到窗戶之外的景觀。
拱廊街作為19世紀最具代表性的人造物,它模糊了室內與室外的空間界限,遮風避雨的玻璃穹頂和晝夜不間斷照明的汽燈打破了自然環境對商業消費活動的限制,“完全模棱兩可的拱廊街”兼具著作為居室的街道和作為街道的居室的雙重特征。另一方面,拱廊街構建了一種新自然的法則,它是剔除了自然特征的商品世界,同時又制定了一套如自然之力般無可抗拒的“新自然法則”。居于這套法則核心的,是被奉為諸神的商品,它們遵循著“新奇與時尚”的邏輯,最新穎的商品總能受到最熱烈的膜拜,而潮流之外的過時之物則全然被拋棄。這種意義上,拱廊街樹立了資本主義的神話典范,它制造了19世紀現代性沉醉其中的夢境幻覺。
本雅明敏銳地發現,由鋼鐵和玻璃建造的拱廊街正參與制造了這一“無與倫比的幻覺”。如上文所言,拱廊的建筑材料和空間結構制造出一種無處不在的“可視性”,同時又無法看到任何“真實的”東西。整個拱廊街就如同阿拉貢(Louis Aragon)筆下儲存著現代神話的水族館,它致力于構建一種純粹的景觀:商品世界的景觀,只允許觀看和移情,不需要反思和批判,甚至連觸摸也是禁止的。拱廊街兩側的玻璃櫥窗就遵循這樣的法則,玻璃與商品的天然親緣性正在于它們都強化著“可見”與“重復”,大量商品向來往行人投之以愛慕之情,卻無時不在挑選著潛在的買家,它最大限度地允許買家毫無顧忌地打量,卻絕不會向窮人乞丐拋媚眼,也拒絕那些僅僅是進來躲雨的流浪漢。
本雅明指出,玻璃和鏡子的反射、折射的光學把戲,實質上制造出了一種“令人不悅的幻覺”。櫥窗里的商品拒絕向沒有社會地位的人的傾心,力圖在失去光暈的機械復制時代重新建立起一種矯揉造作的膜拜價值,人們的膜拜對象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藝術作品,而是擺在櫥窗里可望而難及的商品。
本雅明正是從拱廊街的建筑材料和空間結構的隱喻中,讀出了資本主義商品世界制造的幻覺及其帶給個體與群體在精神層面的不安。拱廊街制造了整個時代沉浸其中的夢境幻覺,虛構著社會進步與繁榮的信仰,同時,它的空間結構也表露出資產階級內心在外界現實與自我內心的雙重迷惑中進退維谷。作為商品夢境的時代通道,拱廊街最大限度容納了觀看與閑逛,同時又潛在地區隔與拒絕;既喚起具有消費意識和觀光意識的現代主體,又使他們在對商品的迷戀中迷失自我。拱廊街的空間悖論在于真實世界與它所制造的夢境幻覺之間的斷裂,這也正是建造它的時代和社會的集體無意識的癥候顯現。
二
正如紀埃迪昂教我們從1850年代的建筑上讀出當代建筑的基本特征,我們反過來也從那個時代的生活及其似乎次要和失落的形式中辨認出今天的生活。
本雅明特別指出,一個時代的建筑往往凝聚著這個時代的集體夢想,卻不被當時的人意識到,過往的風格通常會在日后的某一特定時刻又悄然而至,獲得“復興”。第二帝國時期的巴黎以鋼鐵和玻璃高隆起穹頂的拱廊街,在本雅明看來,也正是對古羅馬帝國建筑的某種復興,而這種帝國夢想的重臨,往往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顯現。






因此,相較于表征資本主義商品世界最為壯觀景象的拱廊街的全盛時期,拱廊街所經歷的數十年的衰落,及其衰落后留下的商品廢墟,正是作為現代神話的殘留之物,儲藏著大量未被意識到的集體的希望。
三

按照本雅明的思路,衰落后的拱廊街才是能夠進一步闡釋出19世紀資本主義的希望意象。正是基于對新鮮空氣的向往,基于拓寬街道以便于車輛通行的希望,基于拱廊街已不再能夠滿足更多商品的展示與售賣的需求,一個時代對未來的烏托邦想象,卻激活了它被拋之于身后的過去的意象。


與這二者既相關又有所不同的是,本雅明對現代神話的理解,既吸取了超現實主義的夢境意象,也深受馬克思經濟學的影響。在他看來,資本主義通過解除自然和傳統對人的束縛而建起的龐大的“新自然”——大機器生產、新技術、新的工業材料和新的生活方式——仍然處于晦暗不明的境況中,資本主義歷史并未能如其所愿地走出啟蒙理性想要打破的神話階段,而是依然陷入在將“新”看作是對舊事物的延續的傳統想象中。

由此可見,本雅明更傾向于將現代神話看作是一種“集體的無意識”,一個有待去喚醒的集體夢境,并以“希望意象”作為他對唯物主義辯證意象的一個補充。如果說辯證意象提供了一種剝去現代神話的迷霧使歷史的真實面貌展現出來的視角,那么,希望意象則為之增添了烏托邦的維度,為呈現為廢墟的資本主義歷史的救贖留下了通道。
在《拱廊計劃》的“F篇“鋼鐵建造”中,本雅明清楚地闡明,夢境意象(dream-image)不能承擔辯證意象的表征任務,而只有希望意象,才能為未來提供革命的動力,這種動力和潛能儲藏在最近的過去之中,致力于喚醒對遠古神話和烏托邦的記憶寶庫,希望意象除此之外并無其他。這也是本雅明自始至終都關注19世紀舊物的一個重要原因,大到歌劇院、拱廊街這樣的宏偉建筑,小到一個破舊的物什,一件過時的衣服,一種不再流行的潮流,比起源源不斷生產出來的時尚與新奇,本雅明更加關注這些事物“死去”后的生命。在本雅明看來,這些被遺棄的過時之物正是當它們失去了施加于其之上的新奇與進步的魔咒后,在它們無可避免地淪為歷史的垃圾之時,才得以重獲新生。




? 瓦爾特·本雅明:《作為生產者的作者》,陳永國,郭軍,蔣洪生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頁。
? 瓦爾特·本雅明:《巴黎:19世紀的首都》,劉北成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頁。
? 瓦爾特·本雅明:“《拱廊計劃》之N:知識論、進步論”,郭軍譯,汪民安編:《生產》(第一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頁。
? 本雅明在《那不勒斯》(Naples)一文中,將處于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古老與現代、富裕與貧窮的交錯滲透的那不勒斯闡釋為一種多孔性的結構。
? 瓦爾特·本雅明:“《拱廊計劃》之N:知識論、進步論”,郭軍譯,汪民安編:《生產》(第一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頁。
?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s. Trans. Howard S.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32.
? Ibid., p. 538.
? 瓦爾特·本雅明:“《拱廊計劃》之N:知識論、進步論”,郭軍譯,汪民安編:《生產》(第一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頁。


















編輯/黃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