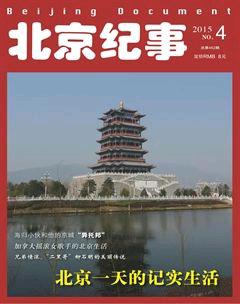鄒博偉:北戲書館給了我藝術的第二次選擇

眼前這位男孩濃眉大眼、高鼻闊口,一張國字臉,人高馬大,十足的將相范兒,然而一開口,卻暴露了他90后的年輕特質,略微調皮的言談舉止間,還是個沒長大的孩子。他的粉絲、常來聽書的大爺大媽們說:這個孩子一上臺,“三請姚期”“岑彭歸漢”娓娓道來、栩栩如生,千軍萬馬都在他一張嘴里,很端得住。一下臺給大家端茶倒水,又成了招人喜歡的活潑小伙兒。一句話,這位北戲書館培養的優秀弟子鄒博偉很有觀眾緣。
許是受爺爺的影響,鄒博偉打小兒就跟著爺爺蹭戲聽,愛上了京劇,4歲時進入北京京劇院學員班學戲。那么小的年紀從基礎練起,沒少吃苦。后來考入天津觀瓔戲校正式入科,學習架子花臉。2012年戲校畢業,鄒博偉考入北京戲曲藝術職業學院,然而卻不是他從小學習的京劇,而是影視表演系。因為變聲期的不順利,嗓音條件受到影響,鄒博偉想到放棄京劇。但是他打小練就的戲曲功底卻讓他成為影視表演系里嗓音條件、戲曲功力最好的學生,這點讓他入學時便引起影視表演系副主任張怡的注意。張怡是著名評書大師連麗如的親傳弟子,她發現鄒博偉很適合學習評書,便在周末帶著他去書館聽書,發現這個孩子很坐得住,對評書也有興趣。后來鄒博偉會很主動地自己買票去書館聽書,聽完還幫著干活。從一年級開始,鄒博偉便跟著張怡老師學書,后來慢慢也上臺說書了。
現在鄒博偉可以在臺上說三四十分鐘的大戲,還有一群鐵桿粉絲,每周六從很遠的區縣專程趕來聽他說書。在張怡老師和客座教授連麗如的指導下,鄒博偉獲了很多獎:2013年鄒博偉用評書的方式演講《北京歡迎你》,參加“最美北京人”宣講比賽獲“最佳才藝獎”,并隨宣講團在北京市巡回演出,很受歡迎;2014年,鄒博偉表演的評書《潼關戰馬超》參加第二屆“藝韻北京”北京市群眾曲藝大賽,獲“最佳風采獎”。在影視表演系12級畢業大戲《光照千秋》中,鄒博偉飾演男主角戚繼光,獲得了很好的反響。
記者:《光照千秋》中你飾演的戚繼光跟以往飾演的角色有什么區別?
鄒博偉:大一時我被借調到當年的畢業班排演畢業大戲《第十二夜》,飾演的是一個丑角;大二時排《雷雨》,我飾演魯貴。在《光照千秋》中我演的是60多歲的戚繼光,跟之前的角色差異很大。戚繼光是完全正面人物,和我之前塑造的有點詼諧的角色很不同。性格上也不符,讓我一個90后去塑造一名古代有擔當有責任的將領,是很有難度的。
記者:你記憶中最難克服的關卡在哪里?
鄒博偉:可能就是戚繼光跟他夫人之間那種相濡以沫、老夫老妻的感情,最難以揣摩。他的老妻陪著他風風雨雨那么多年,我這么年輕,又沒有感情經歷是很難體會的,分寸很難把握,后來在老師的反復指導下處理好了。
記者:演話劇跟說評書相比,你更喜歡哪個?
鄒博偉:我覺得演話劇不如說書過癮。說書的時候能看到觀眾的臨場反應,另外,準備一段書很困難,需要付出很多精力,所以演出成功會很有成就感。話劇是一幫人的團隊協作,評書是一個人說,更過癮。
記者:還有幾個月就畢業了,你畢業后打算做什么?
鄒博偉:很多同學選擇進劇組演戲,我還是想繼續說書。雖然說評書在經濟回報上跟演戲沒法比,但是我興趣在此。并且學校提供了這么好的條件,連麗如大師親自指導,還有書館這個磨煉、實踐的舞臺。我會好好珍惜,把連派評書傳承下去。
指導老師張怡:扶植評書演員
是北戲書館的責任
記者:鄒博偉從小學習京劇,但學習評書只有三年時間,現在已經是不錯的評書演員,是因為他個人的天賦嗎?
張怡:他個人生理條件非常好,這可能跟他的戲曲功底有關。但對他們來說,學評書最困難的是沒有什么生活積累。能在書館登臺說三四十分鐘,每周都有新的內容,對于成熟演員來說不是事兒,但對于剛登臺的孩子來說,這都是“活口”,需要現場跟觀眾交流的能力,這點鄒博偉做得很好。其他學生學評書是一句一句地學,像鄒博偉就沒有這種障礙,每個星期都能跟著準備下一段活,很不容易,可以說他在學書這塊有點天分。另外我們學校給提供了很好的機會,讓學生能夠登臺,不斷地登臺實踐跟觀眾磨合。評書是我們影視系的專業課,有好幾個學生能說一個段子,但是能每周上臺說大書的就是鄒博偉。跟著連先生班子兩年多了,像他這么小能上臺說《東漢演義》,這是連派的代表作,連先生很看好他。連先生也是我們的客座教授,所以他很幸運,有這個機會跟藝術家面對面地學。
記者:從完全的門外漢到專業演員,鄒博偉的成長應該是很迅速的吧?
張怡:學評書第一段書都是死口,一句一句背下來的,完全是準備好了登臺。連先生對于鄒博偉的登臺是親自參與規劃的,讓他從《三請姚期》開始說。大半年了,很多觀眾能看到這個孩子的成長。從開始的十幾二十分鐘,到現在能說40分鐘。上周我身體不舒服,他也能在臺上說:“我們老師感冒了,今天我多說一點兒。”他有一點擔當,說明他是長功了。不僅我能看到,也聽到很多觀眾說:“比原來說得好多了。”剛開始上臺很緊張,眼睛都是空白的,也會有錯。現在在臺上很自然,還會自己跟觀眾開個玩笑,就過去了,接著往下說。現場應變能力有變化,他對說書的理解也有增長。一開始更滿足于在臺上說下來,現在對于塑造人物、情節推進,他都有理解上的進步。有觀眾從很遠的地方專門過來聽書,是對他很大的支持。現在他在馬家堡地區已經有點小名氣了,他下來給觀眾倒水什么的,很受歡迎。
記者:從2014年6月開館到現在,北戲書館取得了哪些成績?
張怡:北京是國際化大都市,演出市場非常繁榮,評書是非常小眾的藝術。已經不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了嗎?但是喜歡的人非常喜歡。它培養了觀眾過周末的方式,花錢不多,打發好幾個小時,來聽一次以后“且聽下回分解”,有長線的吸引力。書館開館的時候劉侗院長也不是以經濟為目的的,我們作為傳承傳統藝術的學校,能帶出孩子來學評書是不容易的。票價我們定得比較低,成人20元,學生票10元,很多家長帶著小孩來聽書,全家的票價買不了一張電影票。我們從沒有觀眾說起來,到現在基本穩定在每場70人左右,已經很不錯了。書館就是我們普通教室,周末變成書館,能坐70人就爆棚了。開始學校在周邊早市和小區做了些宣傳,我們就從馬家堡地區開始的。現在有從很遠地方來的,最遠住在圓明園的一家每周都來。我每周得帶著孩子登臺,不是為了經濟,主要為了從事教育。這個藝術不是課堂上能教出來的,必須有鍛煉的舞臺。在2014年第二屆“藝韻北京”北京市群眾曲藝大賽中,陳豪、張元浩獲得了優秀獎,李若源獲“最佳風采獎”。參賽選手中評書這個門類進復賽的有七八個,咱們學生就有6個,可見書館在傳承、帶演員方面有很大的作用。評書現在是國家級非遺,真正走進大學落地的,僅此一戶。通過大學教育對非遺保護是很好的嘗試,因有劉院長的大力支持,我們才能把這么小眾的藝術在學校扶植起來。
(編輯·麻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