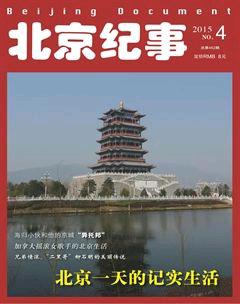父親是新中國第一代建筑工人
紀嵐

父親的家里有三本相冊,那是他積攢了幾十年的影像資料。每一幀老相片都有內容豐富的一段人生故事,父親的青春歲月蟄伏在那些老照片里。有一張攝于48年前的老照片,里面的人物我大都認識,第二排右起第一個便是我的父親,其他人都是我的叔叔阿姨,也是父親的建筑工人朋友。我對那些照片很感興趣,尤其在父親晚年的時候。看著它,父親的許多往事就像電影一樣,一幕幕地在我的眼前浮動。
50年代初,從河北老家來到京城挑磚
父親很愛聊天,但他的故事總是斷斷續續,不長就斷了頭,但跟我講了幾十年。上世紀50年代初,新中國剛剛建立,首都北京的各項事業百廢待興,城市建設一下子擺到議事日程上,急需大批的建筑工人。1952年春天,父親的故鄉河北永定河畔一個古老的村莊,被一場洪水洗劫后,父親跟著幾個老鄉來到京城,參加到北京的建筑大軍中,在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當了一名挑磚工。第二年,只有父親一個人扛著鋪蓋卷腰系一根麻繩又回來了。那是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在建設新中國新北京之初的歲月里,每一個勞動者都以當家作主的自豪感,投入到每一天繁重的勞動中。那時候父親吃在工地住在工地,工地既是家也是他的生活信念,工友們也是朋友,在工地他懷揣著夢想。后來我在電視臺介紹老北京的故事里看到,那時建筑工地上雖然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卻都是人背肩扛,一天的勞動強度可想而知。父親說:“我們當時就是這樣工作的。”他年輕時只有1.57米的身高,父親就是以這樣的身體條件參加到了北京的十大建筑工程建設的。已經有一些生活經歷的我問父親累嗎?他說:“那會兒年輕,不覺得累。那時候有150斤一副的擔子,也有200斤一副的擔子。人家大個兒挑200斤,我不服輸也挑200斤的。”兩年后父親加入了共青團,三年多以后他又加入黨組織,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
父親年輕時給我留下的印象,干起事來總是風風火火閑不住,他走路的頻率很快,總怕落在別人后面似的。他告訴我:“這些人后來也都學習了技術。我學的是機工,開吊機。幾十米高的塔吊我噌噌幾分鐘就爬上去了。和你媽談戀愛時,她離著工地還有好幾里地,我在塔吊上就看見她了。”我記得很多年前,看過一部反映建筑工人生活的電影《青年魯班》。里面講述的是青年工人李三輩,刻苦學習文化知識,并把它們運用到生產實踐中去。針對當時工人普遍知識水平比較低的現實,他研究出“放大樣”的技術。大大提高了施工速度和工藝水平,在建設北京十大重點工程中發揮了很大作用。據說李三輩的生活原型,就來自優秀建筑工人的代表李瑞環、張百發等一批工人的生活經歷。李瑞環后來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張百發也當了北京市的領導,他們都是從北京第三建筑工程公司走出去的,也是我內心十分敬佩的老一代建筑工人。
這以后北京的城市建設以日新月異的速度向前發展著。建筑工人四海為家。父親和他的建筑工人朋友們轉戰于京城各地的建筑工地。1955年他們機械隊五六十人,開赴參加門頭溝三家店磨石口攔河閘工程,地點在永定河上游。當時建筑工人的工作環境是比較艱苦的,都是露天作業。當時正是寒冬臘月,山區的夜里能達到零下20攝氏度。工程又很緊,一個月必須完工。父親說:“我們的腳下淌著水,每天挖掘隧道。冰天雪地,風吹得像小刀子似的。我們工人有時為了保證質量都光著手操作水泥灌漿機趕進度,很多人手上都裂著小血口子,工作起來根本顧不上,等一閑下來鉆心地疼。每頓飯都是食堂給送飯,大家輪流著吃飯,輪到我們吃飯時,饅頭都凍得帶著冰碴。工棚在四野荒郊上,周圍幾里地都沒有人家。我們吃住都在工地,憑著簡單的機械艱苦的勞動提前完成了任務。”1961年冬天,他們又參加了頤和園北邊黑莊戶102重點工程建設。當時我們家住海淀區的五道口,父親每天早晨天不亮騎車上班,一路上坡,要一個多小時。每天下班一路下坡,雖然快些,可一路上黑燈瞎火。有時趕上工期緊,黨組織經常號召黨員團員帶頭加班加點,晚上八九點鐘下班是家常便飯。建筑工人的辛苦受到黨和軍隊領導的關心,中國人民解放軍粟裕大將和軍隊的領導同志親自到工地看望建筑工人,給他們作形勢報告,使每一個建設者備受感動,高質量高速度地完成了工程。
改革開放初,手握珍貴指標不謀私利
父親曾自豪地告訴我:他曾參加過著名的十大建筑之一的華僑大廈的建設施工。他們班組是由一群年輕人組成的,也就是本文提到的那張照片。他們的班組里男的瀟灑帥氣,女的年輕漂亮。小劉叔最年輕,當時不到20歲。李悌叔叔是班組里的知識分子,當時是技術員,后來當了工程師。有個阿姨是統計員。齊叔是開挖掘機的司機,他身材瘦高,平時喜歡打籃球和看籃球比賽,后來他與我們家做過十年鄰居。在我眼里他一直都很帥氣。我父親開塔吊。那時他們是一群充滿著朝氣的青年人,活躍在京城的建筑工地。幾十年后我的女兒曾翻著家里的老相冊,說:“我爺爺年輕時真帥。”1966年初班組里的王敬元、徐桂蘭阿姨調離了。他們的班組集體留念,因此有了這張珍貴的照片。三年以后父親所在的建筑公司又開赴湖北省大山深處的十堰市,參加中國第二個汽車城的建設。從此他們遠離家鄉與家人鴻雁傳書,開始了新的奮斗過程,上世紀70年代中期才又回到了北京。這時父親也調到了市房管局系統,在機械修造廠還是當建筑工人。
那時候父親已經開了幾十年建筑機械,他轉行到機械制造廠,已經是一個經驗豐富的老工人。他們單位生產的攪拌機在市場上旺銷。那時候也正趕上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很多城市就是一個大工地。無論企業還是個人都面臨著一次歷史的機遇和角色的轉變。父親在單位負責銷售工作,經常到江浙和廣東潮汕一帶出差,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外面度過的。中國的改革是從東南沿海開始的。父親每次回來,都跟我們兄妹聊改革給社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的種種變化。那時北京也邁開了改革的步子,但還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體制雙軌制并行。父親在單位里又是個小領導,他的工作崗位在一些人的眼里是個肥差。因為父親的手里握有單位的鋼材指標。
有一年夏天,一個曾經與父親有業務關系的浙江人,在我父親臨下班前來到我們家。我們叫他小黃。他自稱找我父親有點事。后來我們才知道,他是跟我父親要計劃內鋼材指標的,這樣他個人就可以賺到額外的錢,而損害了國家的利益。那天晚上我們讓他在家里吃晚飯,但是一提到鋼材的事,父親的臉馬上沉下來,說:“這事堅決不行!”小黃這人也真是有點韌勁,左說右說,一口一個紀師傅,說了一個晚上。我們家人則在一旁看著一言不發。父親做事有個原則,單位的事絕不讓我們插言。我們就進進出出地看著小黃很尷尬地在我們家待了一個晚上,悻悻地走了。后來我們聽父親聊天時隱約知道,也曾經有人到單位求他辦過這類事,都被他一口回絕了。
父親作為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他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實實做事。他勤勞樸實一世清貧,這種品格也影響了我們兄妹幾人,他的晚年也是幸福安詳的。有一個生活情景我一直記得。那時父親已經退休。有一天傍晚,他買回來一個玻璃魚缸,里面一缸清水,有幾條紅色的小金魚歡快地游動著。我的女兒立刻湊到了跟前。那是一幅生動的畫面,父親的滿頭白發與女兒的一頭黑發,一老一少顏色分明。他們看著金魚,臉上都帶著愉悅的笑容。這樣平淡平靜的生活,我一直覺得很溫馨。
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已經建設得很美的北京城,有許多地方都灑下過我父親他們那一代建筑工人辛勤的汗水。很多年后,我都以自己是建筑工人的兒子而自豪。
(編輯·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