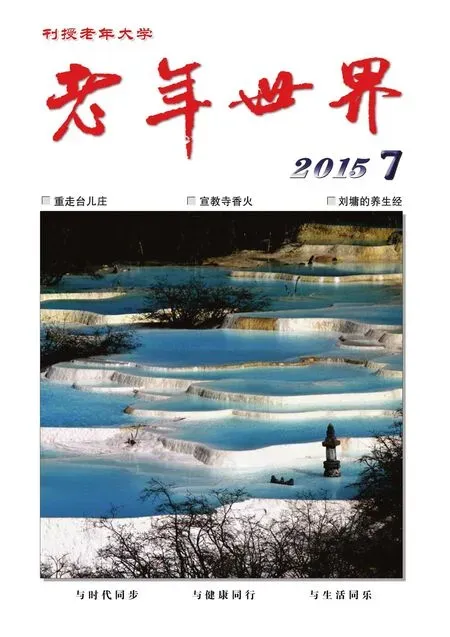土默特第一代蒙古族共產黨人誕生的歷史條件
2015-04-28 09:57:10儲建中
老年世界
2015年7期
儲建中
土默特第一代蒙古族共產黨人誕生的歷史條件
儲建中

五四運動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土默特第一代蒙古族共產黨人迅速誕生、崛起和發展,使得內蒙古的近現代史改變了歷史走向,黑暗陰霾的天空出現了群星燦爛的時刻。
政治條件
回溯歷史,土默特蒙古族在政治方面,自清以來,一直處在清朝政府的嚴格管控和排擠打壓之下。1632年,從皇太極開始,親率大軍西征察哈爾部,林丹汗被迫渡河西逃,卜石兔汗的兒子俄木布洪臺吉與古祿格、杭高、托博克等收集部眾,投降后金。1635年時,有人向鎮守歸化城的貝勒岳脫告密俄木布謀叛,岳脫隨即逮捕俄木布,押送盛京(沈陽)。1636年,清政府將俄木布廢為庶人,編土默特為左右翼兩旗,設都統、副都統、參領等官統治管理旗民。從此,土默特變成“尺地一民不能私為我有”的內屬旗,換句話說,就是把土默特變為嚴厲的皇權控制之下的地方。這是史學界公認的土默特蒙古族政治上受清廷壓迫的重要原因。
緊接著,順治入關定都北京后,據《清史編年》載,其身邊有所謂高明的大臣講“蒙古興則天下亡,天下興則蒙古亡”。當時順治雖只有6歲,但在一班滿漢大臣的輔佐下,開始在政治上對土默特蒙古族分化瓦解。比如,不承認土默特部的“帶地投誠”,比如不斷分割土默特牧地,安插別部蒙古,在土默特西北,安置烏拉特三公旗;在北邊,又于順治六年(1649)、十年(1653)、康熙三年(1664),分別安插四子王旗部落、達爾罕貝勒旗、茂名安旗。……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