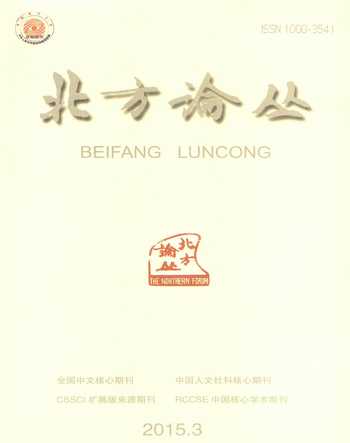融匯眾有,以宋為宗:吳雯詩論
趙麗萍 鐘振振
[摘要]清初吳雯的詩歌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體現了清朝政權穩固之后詩歌的特色與發展方向,吳雯的詩歌能出入漢魏,善于學習唐詩的意境,又有宋詩日常化的特征,是清詩眾多詩人中的典范。從創作方法上來看,吳雯的詩歌得唐詩之貌而難近其神,以學問為詩,能化用前人詩句而不著痕跡,以推陳出新為特色,與宋代黃庭堅主張的“點鐵成金”“脫胎換骨”的詩歌創作方法一脈相承,是清初宗宋詩風的代表。
[關鍵詞]吳雯;清詩;宗宋
[中圖分類號]I206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0-3541(2015)03-0080-04
[收稿日期]2015-02-10
①所引吳雯詩歌均來自《吳雯先生蓮洋集》,吳雯撰;李豫,等點校,三晉出版社2010年版。
吳雯①是清初詩史上雖未被太重視,但絕不可被忽視的人物,是詩界泰斗王士禛最為得意的弟子,王士禛將其視為繼曹子建、李太白、蘇子瞻之后的“仙才”。王士禛認為,吳雯得其神韻說之旨:“余與海內論詩五十余年,高才固不乏,然得髓者終屬天章也”[1](p60)。在明末清初山西詩壇,吳雯與著名學者、詩人傅山并稱為三晉大地的“北傅南吳”,清光緒七年(1881年),張之洞建立了四征君祠,把吳雯與傅山、閻若璩、范鎬鼎合祀,稱四人為“晉士楷模”,并稱“四征君”,后人又將吳雯與傅山合稱為“山西二征君”,在清代地域特征顯著的文學背景下,吳雯是山右詩歌發展過程中不能被忽略的一位,其詩集《蓮洋集》被收入《四部備要》中,曾出現過“一刻于吳中,再刻于都下,三刻于津門”[2](p14)的盛況。對其詩歌的深入研究,對于進一步了解清楚山右詩壇狀況,進一步把握神韻詩風,對于把握清初詩壇宗唐宗宋走向,是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個案研究。
一
明清之際,詩歌繼承了“詩言志”的傳統道路,抒發社會變亂背景之下詩人的情懷,更為強調“以詩為用”,發揮詩歌的實用功能,清朝立國之后,政權漸固,詩歌與一個新的朝代的建立腳步逐漸合拍,呈現出屬于清代詩歌的特征來。郭紹虞先生言:“清代學術有一特殊的現象,即是沒有他自己一代的特點,而能兼有以前各代的特點。他沒有漢人的經學而能有漢學之長,他也沒有宋人的理學而能擷宋學之精。他如天算、地理、歷史、金石、目錄諸學均能在昔人成功的領域以內,自有其成就。即以文學論之,周、秦以子稱,楚人以騷稱,漢人以賦稱,魏、晉六朝以駢文稱,唐人以詩稱,宋人以詞稱,元人以曲稱,明人以小說或制藝稱,至于清代的文學則于上述各種中間,沒有一種足以代表清代的文學,卻也沒有一種不成為清代的文學。蓋由清代文學而言,也是包羅萬象兼有以前各代的特點的。”[3](p278)清代文學具有包羅萬象的特征,清詩也不例外。清代詩歌包羅萬象的特征是從遺民詩人之后的新朝詩人開始的,這也是在詩歌發展中,清詩特征漸次形成的一個時期,這樣的特征形成,在吳雯的詩歌中表現得尤為顯著,其作品展示了清代詩歌自我特征的凝定。吳雯存詩兩千多首,其詩歌由王士禛刪定而為《蓮洋集》,綜觀其兩千多首詩歌,能廣泛吸收前代傳統。
(一)漢代詩歌以民歌和文人詩為主,漢樂府民歌古樸清新,《古詩十九首》 借事寄情,意蘊深長,淺貌而深衷,被視為是五言抒情詩的典范。吳雯的詩歌與漢代詩歌有著不可忽略的藝術淵源關系。
明謝榛在《四溟詩話》卷三中言:“《古詩十九首》,平平道出,且無用工字面,若秀才對朋友說家常話,略不作意。”吳雯的詩歌在以《古詩十九首》中詩歌為題的作品中,能深入淺出,以家常語道出,融入了淺顯質樸的民歌風味。如《行行重行行》:“離亭送君去,三里馬悉聲,五里馬無跡,十里云樹平。嗟彼云樹繁,不知人有情,乾坤靜如掌,萬里見君行。”這是一首送別詩,延續并繼承了《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的離別主題,同時又糅合了樂府民歌的特點,用“三里”“五里”“十里”構建了一個行人漸行漸遠的畫面,寫了馬蹄聲逐漸消失,到離人蹤跡全無。最后將離別的悲傷放在對云樹的嗟怨上,認為是樹遮擋了遠去行人的背影。如果樹知人意,不去遮擋,那么就是遠隔萬里,也會看到對方的身影。詩歌沿用樂府古體,沿用《古詩十九首》題材,當然,也糅合了盛唐闊大的意象,是在漢代詩歌的藝術土壤上滋生出的藝術花朵。
在吳雯的詩集中,除了直接使用漢代詩歌的題目,還有和漢代詩歌尤其是文人古詩的作品格調非常相似的作品。如:“出門春草生,入谷夏鶯滿。客子思故鄉,去去不能緩。忽忽事行邁,悠悠增別心。天涯非所難,所難新知音。倦我西山樵,愧爾東蒙客。百年如流水,歡此數晨夕”。該詩從初春寫到入夏,延續了《古詩十九首》中強烈的節序感,該詩語言淺顯易懂,沒有刻意雕琢的痕跡。
吳雯的部分詩歌還有漢樂府民歌的風味,漢樂府民歌《江南》:“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該詩輕快流暢,不避重復,生動活潑,吳雯的《邯鄲歌》的創作手法與其極為相似:“暮踏邯鄲月,曉踏邯鄲塵。邯鄲朝復暮,不見邯鄲人。”再如《女朝汲》:“郎行秋澗上,妾行秋澗底。秋澗濁水泥,不入銀瓶里。”王士禛對該詩置評:“此首有樂府意。”[4](p536)
(二)對魏晉南北朝田園詩人精神的繼承和山水詩人寫景手法的學習,是吳雯詩歌的另一個特點。吳雯的詩歌以山水詩居多,在吳雯的山水詩歌當中,既有陶淵明田園詩的神韻,又有晉宋之際謝靈運、謝朓重于描摹景物的特征。
吳雯在精神氣質上與陶淵明非常契合。吳雯深于性情,淡泊名利,冥于自然。吳雯在青年時期曾經奔走于名門,追求顯達。中年之后,吳雯的心靈歸于沉寂,以追求生活的閑適和寧靜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吳雯在京師求薦時,“獨耽寂守素,不與他人走,膠牢淡泊,門可雀羅”[4](p125)。吳雯不止一次地描寫自己所希冀的隨性自然、自由自在的生活,“洗馬村東一頃田,王官谷口聽飛泉。”(《途次偶意》)“中條如愛我,我亦愛中條。三月忽相見,愁心一倍消。紫芝春送曲,黃獨夏生苗。還挹青蓮色,天風萬里招。”(《喜歸至都下》)“積雨生秋晦,飛泉出半山。歸鴻度嶺急,落葉對人閑。竹嶼隨高下,僧樓借往還。孤情何所得,終日有潺湲。”他說:“得失本一致,陶然返舊林”,“綠樹方垂蔭,黃鸝正好音。”(《留別阮亭先生六首》其一)儼然一位歸去來的隱士。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中創造了一個超然于污濁鄙俗塵世之外的安樂美好的仙境,從此,桃花源成為一代又一代文人情感上的退路、精神上的歸宿。吳雯生長于永濟王官谷,他將這里看成是自己心靈中的桃花源:“朱樓復殘雪,花葉無冬春。眾水急爭壑,一峰閑對人。白云識心素,空心留皇醇。晚來鷗鷺侶,接翅桃源濱。”(《萬山》)除此之外,吳雯還在詩歌內容和藝術方面繼承陶淵明。吳雯的詩歌中不乏描寫平常鄉村景色和農家生活的作品,感情真摯而恬淡,語言明朗而省凈:如《晚歸》:“鼎原猶夕照,谷口秋煙生。歸騎緣南澗,前山蟬亂鳴。野花垂晚實,叢菊抱新英。是處堪招隱,何人識姓名。”非常接近陶淵明的作品。
魏晉南北朝時期,除陶淵明的田園詩,山水詩也在謝靈運、謝朓手中得到長足發展。吳雯詩歌的取材選景,既有對大謝的繼承,也有對小謝特征的延續。謝靈運多登臨游覽,詩歌典麗,謝朓多以游宦為主,詩歌清新,吳雯的詩歌也有許多登臨之作,他多借鑒謝朓遠景登臨的方式,以景寫情,如其作品《鄉寧山城即景》:“山云啟新霽,林屋含清暉。風吹兩黃蝶,時繞山樓飛。老農向煙且驅犢,谷女背人猶浣衣。”此詩寫在詩人行走于鄉寧路途中,寫云朵、黃蝶,寥寥數景,淡筆一揮,即寫出了天剛剛晴朗之后的場景。后兩句寫老農驅犢,谷女浣衣,富有生活情趣,又帶有疏淡寧靜的特征。
(三)吳雯的詩歌中也有色彩艷麗的詩歌,這一點又與齊梁詩歌非常接近。
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說:“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佰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5](p67)《物色》中也說:“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鉆貌草木之中”[5](p694)。齊梁詩歌一直被視為是綺艷華美的代表,體現了詩歌發展過程中對唯美主義的追求。吳雯詩歌有的在內容上與齊梁詩歌非常相近:“花枝蒙蒙繞金屋,蝴蝶一雙兩雙宿。風歇香輕歸鏡臺,曲屋羅屏畫生綠。美人曉起幽夢闌,啼鳥隔樹雕窗寒。見春欲問春深淺,自卷珠簾帶月看。”(《有題》)“轆轤啞軋宮井澀,花影玲瓏半簾月。美人睡起梳曉鬟,錦帆過處雕窗黑。”(《春曉曲》)“珠樓十二嚙金蟾,樓外春風打帽檐。齊到天香何處落,不知人在水晶簾。”(《珠樓》)有的在風格上有齊梁色彩:“美人一端綺,文彩美且良。珍重惜剪裁,藏之黃金箱。一朝奉君子,上衣為下裳。榮華對知己,顏色生輝光。此心結三載,徘徊立中堂。何日理瑤瑟,彈成雙鳳凰。”(《雜詩二首》)這首詩詞贍華麗,用詞秾艷,風格接近齊梁,但在內容上,又與齊梁不盡相同,有嚴肅的求遇思想,蘇爾飴評價該詩:“秀而能老,逸而能壯。源流乎?風雅始克臻此。”[2](p54)可見,吳雯得齊梁之形而越其神。
(四)從詩歌的外在風貌來看,吳雯的詩歌有近唐詩風調的,也有近宋詩特色的。
黃叔琳《刻吳征君蓮洋集序》中言:“征君詩骨力清挺,波瀾老成,五言得唐人三昧,風格在右丞襄陽之間。其奇逸之致,則太白長吉也……七言兼有李、杜、韓、蘇諸大家之勝,而放筆所至,自成一家,不可拘以格調。”[2](p14)可見,吳雯的詩歌不論五言、七言都有得唐詩風調的作品。吳雯接近唐詩的作品,主要見于以下兩種情況:首先,吳雯常常化用唐詩中的句子,形成自己詩歌中新的意境,如《柬張象賢》:“麥垅青青山徑斜,竹林深處有人家。相逢不惜今朝醉,猶喜尊前有杏花。”在該詩中,“竹林深處有人家”化用杜牧“白云生處有人家”而來,唐代賈島有《尋隱者不遇》:“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該詩為五言絕句,以問答場景結構詩篇,以物喻人,白云比喻隱者精神的高潔,蒼松引喻隱者的風骨,簡練而意蘊深廣,吳雯仿效此詩:“白云滿前山,山門亂溪水。幽人何處尋,立久聞松子。”(《訪隱者不遇》)吳雯的詩歌幾乎沿用了賈島詩歌中所詠的意象,如白云、松下及其隱者,二者不同的是,吳雯以寫景作為開端,賈島以敘述作為開端,吳雯的詩歌中表現了靜等隱者的靜謐,賈島詩歌中表現了尋找隱者的急切。其次,吳雯詩歌中不少以神韻見長的詩篇,深得唐詩氣韻。如《聞喜題壁》:“山客復還山,歸來山更好。叢桂近如何?應發煙中道。”《見山色不斷口號》:“芳草正萋萋,垂楊絲不齊。青山如送客,直過雁門西。”《見曹正子綠水送春帆之句偶贈》:“春帆一片曉云開,綠水鱗鱗畫舫來。重見江南斷腸句,不須低首賀方回。”《一片》:“一片花飛點客衣,纏綿珍惜不多時。可憐都作關心夢,忘卻東風喚子規。”《懷山堂》:“山中有草堂,未得山中住。白云不讓人,占盡讀書處。”唐詩以深邃而豐富的意境以及精神世界見長,多風神氣韻,吳雯的以上絕句在字詞意象上非常接近唐詩,神韻悠然,情致秀雅。清林昌彝在《射鷹樓詩話》中言:“蒲州吳天章諸生雯,著有蓮洋集,集中短篇詩出入騷雅句,如‘潮來全楚白,云上半江陰,則入盛唐之室。”[6](p211)可見,吳雯詩歌中是不缺乏唐詩風格的作品的。
除了有接近唐詩意象的作品,吳雯的詩歌還有宋詩特色的作品,與唐人相比,宋代詩人少了浪漫的情懷,在藝術上,追求淡美之境,在生活態度上,和光同塵,與俗俯仰,其審美態度世俗化,在這樣的審美情趣轉變的背景下,宋代文學體現了以俗為雅的特征,這種態度使詩歌更加貼近日常生活,詩歌體現出日常化的特征。如吳雯的作品《虞鄉口號二首》:“舍南舍北蔓寒瓜,東門有池方漚麻。老農何處牽黃犢?行過一灣紅蓼花。”“楓林颯颯石磷磷,垅上饑鳥飛趁人。烹羊釀秫勞田父,打鼓攤錢賽社神。”詩歌以詩人在虞鄉路上所見為表現對象,描寫了富有三晉風味的農村風光、風俗和農家生活。吳雯的部分詩歌既有生活化的傾向,也具有宋詩的以理趣見長的特征。如《野渡》:“野渡忝秋水,危橋一線通。臨深能自力,終不污泥中。”在唐人的筆下,“野渡”往往帶有“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的蕭疏散淡的空靈意境,但在吳雯的筆下,卻以過橋時處處小心為體悟點,以面臨深潭,不陷于污泥之中比喻人生中能處處保持人格的高潔。
吳雯對傳統的繼承,是融化之后的吸收。包羅萬象,而兼有各代特點,正是吳雯詩歌的典型特征,同時,也意味著經過遺民詩人的奔走呼喊之后,到了清初,清代詩歌的自我特征日益明顯。當然,需要說明的是,吳雯的詩歌能學習漢魏,熔鑄唐宋,但吳雯的詩歌卻沒有超越前面的山峰。
二
從總的面貌上解讀吳雯詩歌,可見其能廣泛學習前人,熔鑄前代詩歌的各種特色,能結合眾代詩歌創作經驗,呈現出多樣的詩歌創作風貌,但是,從創作的精神內核上來看,吳雯的詩歌創作方法是最接近宋詩創作方法的,他是遠唐近宋,以宋為宗的。唐宋之后,元明清尤其是明清的詩歌、詩歌理論就在宗唐與宗宋的框架內前行,作為清代詩歌創作洪流中的一員,吳雯的詩歌不能沒有時代的烙印。在宗唐與宗宋的詩歌理論或創作主張的博弈中,清代從錢謙益開始,出現了合流的傾向。錢謙益在唐宋兼宗的主張之下,一改明代及清初云間派的宗唐之風,肯定了宋詩,王士禛更是依據詩風的轉向,出入于宗唐和宗宋之間,不局限于“詩必盛唐”一尊,倡導宋詩,成了清代宋詩派創作的開端,同時,他不斷地自覺地調整著所持詩論,希冀詩歌朝著一條更好的道路發展。在這樣的詩學背景之下,吳雯以其創作實踐,昭示著自我對于宋詩創作手段的遵循。這種不自覺的遵循,見于以下幾端:
(一)從創作的精神內核上來講,吳雯對于唐詩的學習,是得其貌而難近其神的。唐詩的創作精神內核,不是外在的風神氣韻所能概括的,最根本的還在于其精神風貌,這種精神風貌源于一個蓬勃熱烈時代下所激發的昂首闊步的精神姿態、積極樂觀的自我認同和建功立業的遠大理想,唐人在詩歌中灌注了生命的激情、樂趣,以及情趣。這是中國傳統社會、文化上升時代所呈現出來的精神文明結晶后來的時代,無論怎樣學習唐詩,由于文化背景與時代背景的轉換,缺乏了積極向上的時代氛圍,缺少了文化的全面繁榮和刺激,缺少了精神的強大和自信,往往是得貌而缺神的。吳雯的詩歌對于唐詩的學習就帶有這樣的特征,對唐詩的學習,往往能模擬唐詩的意境、風味,如“白云滿前山,山門亂溪水。幽人何處尋,立久聞松子。”(《訪隱者不遇》)賈島的《尋隱者不遇》,將隱者放置在云深之處,不辨來往,在渾茫無端中增加了隱者的神秘性,增添了藝術的色彩和魅力,吳雯的《訪隱者不遇》,“幽人何處尋,立久聞松子。”精神姿態是靜止的、內斂的,沒有去積極地尋找,而是久立聽松子掉落的聲音,在內核上與唐詩有了明顯的界限。
(二)從創作方法上講,吳雯的許多詩歌,都以推陳出新為特色,與宋代黃庭堅主張的“點鐵成金”“脫胎換骨”的詩歌創作方法一脈相承。面對唐詩這座難以企及的高峰,題材、意境無所不有,修辭手段爐火純青,藝術、內容結合得天衣無縫,宋詩采取了一種回避唐詩、立意求新的方法,尤其以黃庭堅為代表。黃庭堅強調對前代詩歌積極借鑒,點鐵成金,取古人陳言自己點化翻新,從而達到脫胎換骨的效果。黃庭堅倡導的這種詩歌創作方法,是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的創新,要求自己的詩句沒有古人的痕跡,與自己所要表達的思想情感渾然一體,化腐朽為神奇。吳雯對前代優秀傳統的借鑒,就是對這一詩歌創作方法的實踐,例如,吳雯最為著名的代表作品《明妃》:“不把黃金買畫工,進身羞與自謀同。始知絕代佳人意,即有千秋國士風。環佩幾曾歸夜月?琵琶唯許托賓鴻。天心特為留青冢,青草年年似漢宮。”在歷代昭君題材的基礎上,變悲怨為清麗,在主題意蘊上翻陳出新;再如其作品《答人》:“自卜條南舊隱居,明星玉女對攤書。門前萬里昆侖水,千點桃花尺半魚。”清沈濤《匏廬詩話》中言:“初吳天章‘門前萬里崑侖水,千點桃花尺半魚二語為新城尚書所稱。‘尺半魚三字,乃用寧戚《飯牛歌》‘河中鯉魚長尺半也。風調固佳,下字亦俱有來歷,商寶《意舟行雜詩》:‘平添新漲琉璃闊,二寸公蝦半尺魚。改尺半為半尺,便覺杜撰不僅效顰貽誚耳。”[7]吳雯還常常翻用前人詩句,如《詠風帆》二首:“五兩飄搖楊柳津,波心片影暗輕蘋。眼前畫舫須臾過,愁煞朱樓望遠人。”化用了溫庭筠的《望江南》:“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另一首“蘋末生時動遠林,芙蓉干閃紫濤深。黃龍青雀中流急,真快平生破浪心。”化用李白的“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他的《安昌絕句》詩:“半是愁中半病中,傷心不為夢黃熊。蔗漿難解櫻桃熱,愿乞仙人寶扇風。”化用王維的“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漿寒”(《敕賜百官櫻桃》)詩句而來。吳雯化用前人詩句,無雕琢痕跡,自然貼切,正是對宋詩中黃庭堅詩法的遵循。黃宗羲先生曾言:“天下皆知宗唐詩,余以為善學唐者唯宋。”[8](p634)黃宗羲先生此言非常公允,其實,不論是學唐,還是學其他各代詩歌,其根本的創作方法還是歸于宋代的,此種釋詩視角正好可以解釋吳雯融會百家面貌,而又同時是對宋詩的繼承的創作風貌。
(三)“以才學為詩”是宋詩的一大特色,吳雯的詩歌中處處可見“以才學為詩”的影子。四庫館臣評價吳雯:“雯天才雄駿,其詩有其鄉人元好問之遺風。惟熟于梵典,好拉雜堆砌釋氏故實,是其所短。”[9](p4536)事實上,吳雯有許多清新可喜的作品,所以,這一評價并不能全部概括吳雯的詩歌特征,但是,就吳雯的一小部分詩歌來看,這一評價還是站得住腳的。“以才學為詩”的創作方法使得吳雯的詩歌呈現出學問化的特征,如使用代字:《即事》:“階前已開紅躑躅,枕上飽聞黃栗留。一卷南華溫未熟,野人相喚啟新篘。”篘即一種竹制的濾酒的器具。紅躑躅為杜鵑花,黃栗留為黃鸝。再如吳詩喜歡使用典故,吳雯詩歌中的典故來源廣泛,有來自史書的,如其詩《感詠》:“威鳳本潔清,豈云啄腐鼠。自有瑯玕寶,皇天報辛苦。人生墮名行,一失百無補。慎守東崗陂,篤信師前古。”“東崗陂”句用周燮典,語出《后漢書·周燮傳》。其他有來自佛典的,也有來自小說的,不一而足。
吳雯的詩歌在創作精神、手法的選擇上與宋詩接近。吳雯生活的時代是清代初年,詩歌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前代的優秀詩歌創作傳統對于他來說,像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成為他的師法對象,另一方面,又為他樹立起了重重藩籬。在這樣的詩歌創作環境下,吳雯自覺不自覺地選擇了宋詩的創作方法。吳雯是清朝初年的典型代表,這一時期的詩人,不自覺地表現出融匯眾有但又難以超越前代的清詩特征,同時,也沒有擺脫宗唐與宗宋的兩條創作道路的無奈選擇。對于吳雯的這種特色的把握,為清晰地把握清初詩歌創作面貌,提供了一個微觀而個體的視角。
[參考文獻]
[1]王士禛撰,張世林點校. 分甘余話[M]北京:中華書局, 1989.
[2]吳雯撰;李豫,點校.吳雯先生蓮洋集[M]太原:三晉出版社,2010.
[3]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
[4]王士禛.帶經堂詩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3.
[5]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6]林昌彝著;王鎮遠,林虞生標點. 射鷹樓詩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7]沈濤.匏廬詩話三卷[M]清刻本.
[8]蔣寅.清代詩學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9]永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趙麗萍:南京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鐘振振:南京師范大學教授,文學博士,博士研究生導師)
[責任編輯吳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