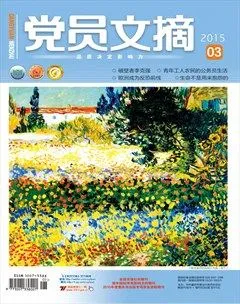青年工人農民的公務員生活
陳卓
為了向省里來的領導匯報工作,馬竹林為此花了好幾天時間,準備了六頁發言稿。陜西省咸陽市秦都區釣臺街道辦事處的這位工作人員,會議開始前還在會場里偷偷念了幾遍。“一定要講普通話。”他叮囑自己。可作為會上的第一個發言者,他一開口還是濃重的陜西腔,“念了一半才發現不對”。
“可能還是有點兒不適應。”他面露難色地說。與自己的許多同事不同,成為公務員之前,30多歲的馬竹林是位農民。除了在陜西師范大學在職進修的法律事務專科學歷外,他的最高學歷為“中專肄業”。
轉變的契機出現在2013年。陜西省當年開始從優秀工人、農民中考試錄用公務員。目前已有733位工人、農民和馬竹林一樣,成為公務員。
“在我的人生中,從來就沒有想到有一天能成為國家公務員。”盯著匯報材料,馬竹林認真地說。
“意外”
“意外”往往是這些工人、農民出身的公務員首先想到的詞語。
同馬竹林一起被錄取的秦濤記得,宣布錄取那天,村委會主任在村里的大喇叭中吆喝村民都去秦濤家里祝賀,“村里的鑼鼓隊也來了”。那時,秦濤是村里唯一一名公務員。
“村里人都說想不到,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也能當上公務員。”秦濤回憶道。
對不少被錄取的工人、農民來說,進入公務員系統是他們一直追求的目標。大學畢業后隨丈夫一起到咸陽市武功縣的李艷,參加了很多公務員考試,“就連社區的也考過”。
2008年大學畢業時,秦濤也曾報考過公務員,但連筆試都沒過。這帶給他的直接后果是,在學校談的女朋友回到家就掰了。“人家父母說了,咱閨女一定得嫁個工作穩定的”。
“村里的人,對吃上一碗公家飯還是看得很高的。”秦濤說。剛回到農村時,在大學一直成績不錯的秦濤 “思想波動特別大,不知道干啥”。他曾想當兵,因母親身體不好而作罷。后來,他在當地新成立的養牛農業合作社里當拌草料的工人。村里人對其他同齡人出路的議論,讓他壓力很大。
“每天心里都裝著事兒”
曾涵飛因為辦事,曾與地方上的公務員打過幾次交道,但經歷不算愉快。對方接待他時有些不耐煩,他當時很不理解。
不過,當曾涵飛來到咸陽市禮泉縣西張堡鎮上班后才發現,“一個問題一天不停地反復解釋,難免感到煩躁”。
跟這些他原來“感覺很威風”的公務員聊天后,他才知道,他們也面臨孩子上不了學、老人生病住不進醫院的煩惱。“這讓我挺意外的。”曾涵飛說。
由于自己有過不愉快的經歷,曾涵飛在接待前來辦事的人時,盡量更加小心,避免無意間傷人。而需要他花更長時間適應的,是這里的工作節奏。“跟下地干活兒不一樣,以前在農村,農忙時把活兒干完就沒什么事兒了,現在每天心里都裝著事兒。”上班剛兩周的曾涵飛說。在西張堡鎮不大的服務大廳里,他被分配在計生服務窗口。但在工作臺后面,整理填報信息,下鄉宣傳,甚至網絡不穩定,也需要這個曾經開過網吧的青年上手擺弄。
至于秦濤,直到現在他還記得,第一天到鎮政府報到,就趕上下鄉檢查衛生工作。“去的時候特意打扮打扮,穿了西服皮鞋,回來以后我的媽呀,全部灰頭土臉的”。
盡管依靠自己和妻子經營的農業合作社,馬竹林早已衣食無憂,但他依然認為,有保障的收入意義重大。“以前村委會主任累死累活只有300多元的補貼,有能力的人誰還樂意干?到最后就只有村霸或有錢人才能競選。”現在依然兼任村委會主任的馬竹林說,“如果有更多的村委會主任像我一樣有體制內的工資,就能吸引更多能人治村。”
在向領導匯報工作時,馬竹林專門把這一點編成短信存進手機里,但他想了想,還是沒說出來,感覺“在領導面前說這個好像有點兒不合適”。
被村民當作孩子的榜樣
在上崗前,這些新入行的公務員都在陜西省委黨校參加了嚴格培訓,內容不僅涉及理論知識、法律政策,還有包括公文寫作在內的實際知識。在兩個多星期全脫產封閉培訓期間,“每天晚上都要查寢,外出要向班主任請假”。這給這些學員帶來了不少改變。
而公務員的身份對馬竹林的改變,已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把價值五六十萬元的汽車,換成了十幾萬元的車,手里攥著的手機,也從一萬多元的變成了幾千元的。
飯局上喝酒的習慣,也被他戒得差不多了。“現在咱是體制內的人了,酒駕是要觸犯法律、開除公職的啊。”他說,“公務員嘛,要注意形象。”
2013年轉換身份的馬竹林,如今大多數時間里依然和村民打交道。不過,在他的電腦收藏夾里,收藏了從中央政府到咸陽市政府的各級政府網站,“每天都要上網看看新文件和新精神”。就連手機鈴聲,都換成了一段關于“中國夢”的講話。
“感覺最難的就是寫文章。”做了六年村委會主任的馬竹林說,“以前在村里都是干些跑腿的活兒,不怎么接觸這方面。”為了準備這次會上的匯報材料,他專門去求助在市里做秘書的朋友,最終把自己一年來的工作總結為“三個沒想到”“三個轉變”和“三個加強”。
已經工作一年多的裴沛覺得,這份公務員工作,顯然比國企工作更耗費精力。為了檢查安全生產情況,他幾乎每天都要往轄區的企業跑,“一上午跑四家”。由于街道沒有執法權,不少企業不配合,“有的就是不讓進”。
對這些公務員隊伍的新面孔而言,他們和體制之間的磨合才剛剛開始。
無論如何,對這些曾經的農民和工人而言,身份的轉變帶來的是一系列的改變。即使工作只有兩周的曾涵飛,也能明顯感受到自己比以前更被人看重了。他舅舅需要在鎮上辦農機補貼,“已經湊齊了所有手續,只要自己來一趟就能辦好”,但老人家堅持要求在政府上班的外甥和他一起去辦。
而直到現在,秦濤進村時,還經常有人沖他喊,“農民工來了!”這是當地人對他“農民公務員”身份的簡稱。這名有包村任務的基層公務員下村時,除了要了解村民情況,幫助村里完成大大小小的事務,還經常被村民樹為孩子的榜樣,被拉到家里,“給娃們講講是怎么考上公務員的”。
(摘自2014年12月19日《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