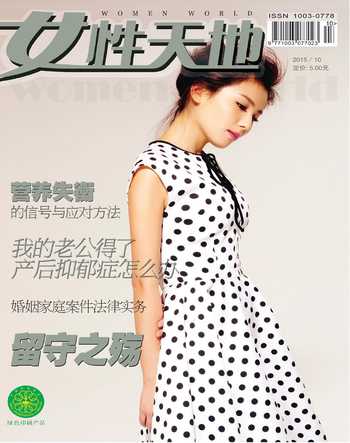留守之殤
梁巧娜
2015年6月9日,貴州畢節,留守的四兄妹在家中喝農藥自殺。這一慘案引發了媒體和社會對“留守兒童”這個特殊群體的再次聚焦。這一次,令每一個有愛心的國人痛徹心扉的,不再是他們因物質生活貧困而導致無法上學或無錢治病這些問題,而是他們堅定地自我封閉的精神世界。據媒體報道,畢節四兄妹臨死之前,家中尚有存糧,卡中仍有余款。但是,他們卻選擇了棄學,拒絕與他人交流,以沉默來抗拒外部世界關切地伸向他們的每一雙手,最后選擇一起走向不歸路……
四兄妹中最大的男孩還不到14歲,三個女孩依次是9歲、7歲和5歲,正處在義務教育階段。因為逃學棄學,不時有學校老師、鄉鎮干部登門勸學,亦常有村鄰出于關心主動親近。但四兄妹家中那扇緊緊封閉的鐵門卻始終沒人能夠敲開。他們所居住的那棟三層小樓,永遠緊閉著的大門非常堅決地擋住了一切訪客。這扇門,從來就只有父母能夠打開,這個家,從來就只有父母能夠進入,四個孩子,恐怕從來就只聽從父母的吩咐。然而,直到死亡降臨,他們的父母卻一直沒有出現……
進入21世紀后,中國的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加快,農民背井離鄉,進入城市務工已經被視為一種生活常態。他們的戶籍上標注的身份是“農民”,但他們在城市各個建設工地里干著最苦最臟最累的活,“農民工”成為他們新的身份標簽。從農村到城市,從耕田種地到修橋鋪路,他們隨工地的變換而改變著自己的行蹤和居所。流動打工、不斷遷徙,已經成為他們生活的主要內容。他們在為中國現代化進程做貢獻,也收獲著在田間勞作無法獲得的報酬。在大多數農村,青壯年勞力外出打工已經成為養家糊口的主要方法。留在家鄉田園的,是他們家中衰弱的老人和他們未成年的孩子。
中國現行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是農民工子女隨同父母進城就讀愿望實現的最大障礙。戶籍制度規定了城鄉居民可享有的各種不同權利和待遇。城市的每個工地都有可能接納農民工的勞動,但城市的每個學校都有可能拒絕接納農民工的孩子入讀。于是,家庭殘缺,親子分離,成為農民工們生活的常態。隨著進城務工的農民人數不斷增加,留守兒童的隊伍也日益龐大。數以千萬計的孩子生活在殘缺的家庭中,長期缺乏父母關愛和監護。缺乏親子互動的兒童情感變化、情感體驗漸趨貧乏,很難形成健全的個性和人格。由于缺乏家庭教育,不少留守兒童的不良行為難以獲得有效的校正,埋下了日后違法犯罪的隱患。
“留守兒童”已經成為當下中國社會一個定期發作的“痛點”,幾乎隔些日子就會發作一番。自殺、犯罪、失學常常是引發“痛點”擴散的因由。每到這個時候,社會的關注通常聚焦于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外部因素。比如物質的貧困、學習條件的惡劣、遭受的各種不公平待遇之類。而后,都有政府的相關職能部門和社會愛心人士攜帶物資去送“溫暖”。現階段的人們理所當然認為,物質的滿足自然而然能帶來精神的滿足。殊不知除了物質,留守兒童更缺乏的是正常的親情互動,以及在這種互動中才能培育成長的健康的情感品質。
據心理學和社會學研究顯示,親子分離的生活狀態會增加兒童人格扭曲的概率。由于父母外出打工,家庭結構殘缺,兒童在成長過程中與父母缺乏親密互動,造成親子關系隔膜。他們更容易輕視親情,不愿與父母,更不愿與外人溝通交流,因而心理問題更難以被發現。進入青春期的孩子也更容易因生理變化產生心理困惑和情緒障礙,形成自我封閉或叛逆性人格的概率會更高。由于親子分離,孩子遇到困難時得不到父母及時幫助和強有力的支持,易導致兒童心理失衡,挫折感與恐懼感會更強烈。內向、孤獨、自卑、壓抑、偏執、任性、沖動都是親子分離家庭中兒童常有的人格特征。
迄今為止,國人更多選擇用物質的形式向世界展示我們的實力。當然,國力強盛、財富增長是我們可引以為傲的資本。但是,被光鮮華麗的現代化表象遮蔽住的中國社會底層那千瘡百孔的精神世界,應該引發我們高度地關注和深刻地反思。現在的兒童就是祖國的未來,每一個熱切希望中國有更強大美好未來的人,都有理由憂慮,數千萬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留守兒童在親子分離、親情破碎的環境中成長,他們依靠什么來健全自己的人格,培育起自己對世界對未來的信心?
奧地利著名的精神分析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很早就指出,缺乏親密的互動和溫情的家庭,會摧殘兒童的心理健康。孩子從父母處得不到溫情,自然也難以激發出自己的溫情表示,他們會采取逃避的姿態來應對生活中的一切問題,對所有外部的愛和溫情也抱持逃避的態度。 畢節四兄妹的生活環境與人生選擇,印證了阿德勒的觀點。
好久沒人牽我的手
好久沒人摸我的頭
冰涼的小手
發燙的額頭
生病是最想你們的時候……
但愿留守兒童那一聲聲悲戚的哀號,能打動更多父母的心。愿天下為父母者除了給孩子建樓匯款之外,更多時候要牽著孩子的手。愿畢節四兄妹那樣的慘劇不再重現。愿所有的父母都明白,給現在的孩子更多的溫情,其實就是給我們的未來更多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