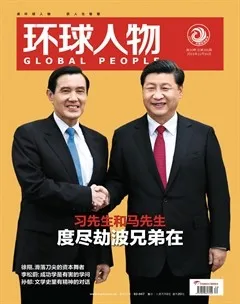三千里上學記



清華園,歷來是北京的寧和靜謐之地。1937年的這個夏日,清華園的寧靜卻被打破了。
“風物涼爽,窗外荷池猶存紅花一朵。哀蟬寒蟄,鳴不絕響……”“七七事變”后,時任清華大學教授吳宓在日記里寫下清華園的如此景象——槍炮聲中,他多次冒險回校,流連忘返。清華的師生們如此留戀這片凈土,但他們都知道,在日本人的鐵蹄下已不可能在北平繼續靜心讀書了。
為國家和民族“死中求生”
北平淪陷后,日軍占領清華。一片凈土,被蹂躪得面目全非:學校成為日軍的兵營和傷兵醫院,學校設施、儀器設備、圖書均遭受洗劫,體育館被用作馬廄和食物儲藏室……
侵華日軍每攻占一個城市,均有計劃摧毀和破壞中國文化:焚毀出版機構、破壞大學、占領學術機構、劫掠圖書文物、殘害知識分子……清華大學的厄運,成為日寇摧毀中國文化機構的一個縮影。
《北京市抗日戰爭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一書顯示:北平淪陷期間,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均遭洗劫。清華大學從建筑物到圖書、儀器,均遭到日軍瘋狂毀壞和掠奪;北大沙灘紅樓淪為日軍憲兵司令部,多位留守教職工遭受嚴重身心折磨,日軍還劫掠了北大圖書館館藏珍品《俄蒙界線圖》,這一孤本文獻,迄今下落不明……
北平淪陷之初,這里的知識分子,都在面臨艱難的抉擇。吳宓深感悲憤無望,在日記中這樣寫道:“聞報,知戰局危迫,大禍將臨……今后或自殺,或為僧,或抗節,或就義。”同為清華大學教授的朱自清、聞一多等也在為國家的命運憂心忡忡:到底該以羸弱之軀親赴戰場,還是該保住文脈,使“弦誦不斷絕”。
1937年7月29日,南開大學遭到日軍轟炸,校園被焚毀。日軍指揮官在記者會上宣布:“我們要摧毀南開大學,這是一個反日基地。中國所有的大學都是反日基地。”
隨著一座座大學的被占、被毀,中國高等教育步入了生死存亡之境。
1937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決定將北大、清華和南開合并,在長沙成立一所臨時大學,指定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為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
三校南遷,并非當時特有的現象。據統計,從抗戰爆發到1938年8月底,中國108所高校,有91所遭到破壞,10所遭完全毀壞;25所因戰爭而陷入停頓。為此,全國106所高校進行了300多次搬遷,遷校3次以上的有19所,8所高校遷校達4次。
而成立不久的長沙臨時大學,剛剛上完一學期的課,便再次面臨戰火進逼的困境。再次遷徙被提上日程。
血氣方剛的青年學生,在國仇家恨面前,很多不愿意“逃命”。學校支持那些棄筆從戎、奔赴戰場的學子,但學校更認為,日后中國建設需要專業人才,不能讓大批的大學生上前線。梅貽琦說:“一個民族,生存的最根本價值是什么?我們都是教書的,我們的責任,是要去塑造一個民族的靈魂,難道這不比打仗更艱巨嗎?”
不悠閑的“旅行團”
1938年2月19日,學子們從長沙出發,奔向西南,當時有3條路線:大多數教師、家眷及部分女同學從長沙乘火車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車入滇;經濟條件較好的男同學和少數女同學,由長沙乘火車到廣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車途經柳州、南寧、鎮南關進入越南,轉乘火車入滇——這一路人數最多;而最艱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發,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團”。旅行團由267名家庭貧困的男同學和11位中青年教師組成,配有4名軍事教官及隊醫等。他們跨越湘、黔、滇三省,翻過雪峰山、武陵山、苗嶺、烏蒙山等崇山峻嶺,步行3600里。
文人長征,曠古未有。雖名“旅行團”,但絕無旅行之悠閑。據記載,“湘黔滇旅行團”出發之前,每人發給軍裝一套,綁腿、草鞋各一雙,油布傘一把,限帶行李8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需的生活用品。這批學子腳踏草鞋,行進在泥濘的湘北大地。頭幾天還有人打傘,可細雨似乎永無停止地下著,為了行走方便,大家將油布傘往背后一擱,不撐了。棉衣濕透了,到宿營地用火烘干,第二天再穿。
參加過這次“旅行”的人回憶說:在路上時間長了之后,隊伍越拉越長,首尾相距竟有十多公里。為了照顧那些掉了隊的人,負責后勤的人一般每天下午5點以后就開始找地方宿營,飯做好后,把所有的碗集中起來,以每人盛一碗為限,先到者先吃。晚上9點以后,各隊隊長清點飯碗,只要碗都空了,就說明人員全部齊了。每天最后一個到的總是化學系教授曾昭掄——曾國藩的后人,我國近代教育的改革者和化學研究的開拓者。

西南聯大的校歌,第一句便是關于這次旅行:“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事實上,這些學子們選擇的路徑,有些的確與當年紅軍長征時走過的重疊,一路上還能看到紅軍當年留下的標語。
令后人感慨的是,在漫漫長路上,師生們也沒有放棄對知識的追求。在行軍兩個月期間,中文系學生劉兆吉根據路上所見所聞,寫成了《西南采風錄》一書;外文系學生查良錚(即詩人穆旦),行前先在長沙購買英文小字典一冊,途中邊走邊讀,背熟后陸續撕去,抵達昆明,字典完全撕光;學美術出身的教師聞一多沿途作了50多幅寫生畫;生物系的李繼侗、吳征鎰兩位先生,帶領學生采集了許多動植物標本;經過礦區時,曾昭掄帶著理工學院的同學,指導了當地的礦工冶煉;地質學家袁復禮則幾乎一路都在不停地敲石頭,向學生講述地質地貌。在這200多名穿著草鞋走中國的學子當中,還出了后來著名的哲學家任繼愈、量子化學專家唐敖慶和航天工業巨匠屠守鍔等人。
西南聯大的史料搶救者與研究者、作家張蔓菱曾在北大有過一次演講,在談到“湘黔滇旅行團”一路有驚無險到達昆明時,她說愛才是中華民族的風尚,當時整個社會,包括下層都是這樣。旅行團走到貴州等非常貧困的地方時,發生過很多事情,都有文字、照片記錄。比如,當地的“片兒警”,也就是地保會出來敲鑼,說:鄉民們注意了,今天老師同學們要從這兒路過,今天集市不許漲價,要方便老師同學。還有一個布告,是玉屏縣縣長寫的,說:今有大學師生路過我縣,國家危難關頭,這些大學生都是未來民族振興的領袖,所有民眾必須予以保護,予以愛護。所以師生一路走來,從來沒有什么地方故意抬高物價、不讓住等,都是給予方便。即使在匪患屢禁不絕的湘西,學子們也沒有受過騷擾,或許連土匪都知道,這一群人,是這個國家的未來吧。
衣服能丟,書不能丟
經湘、黔、滇三省,歷時68天,1938年4月28日,“旅行團”師生們到達昆明。對這批學子們來說,這次“長征”總算走完,而對全國其他一心向學的學子來說,他們的“長征”才剛剛有了方向。
鄧稼先,北平淪陷時正讀中學,在日本人組織的慶祝會上憤怒地撕碎了日本國旗,為避禍逃離北平,途經上海、香港和越南的海防、老街,到達昆明。1941年考入西南聯大物理系。
1942年,一個瘦弱的16歲少年在江西贛州找到一本關于牛頓定理的大學叢書,他看得入迷,又覺得某個地方不對,就把自己的發現告訴老師。老師覺得這少年是瘧疾發作了,頭腦不清醒。這個少年就是日后的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李政道。
當時,李政道確實患上了瘧疾。他不甘心在日軍的刺刀下讀書,從上海逃出后,先在浙江嘉興一個窩棚上學,日軍迫近后,他與二哥李崇道一路向西,因患瘧疾,半途留在贛州讀書。隨后又從江西經廣東進入廣西,再從廣西轉入貴州。
后來李政道回憶說,他不但感染過瘧疾,還患過痢疾,身上長滿疥瘡,活像一個流浪的乞丐。每天瘧疾發作,如寒流來襲,顫抖不止。高燒、惡心、嘔吐又頻頻瀉肚。他無藥可服,備受折磨,幾致喪命。路程中大家都在逃難,不前進就要掉隊,后果難以想象,李政道咬牙堅持。翻不盡的高山大川,攀不完的懸崖峭壁,有時走一天還過不了一座山。進入貴州,“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山更高了,路更難了。可是希望就在前面。
這個未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在西進的路上,有兩個細節值得后人銘記:其一,李政道給茶館做過清掃工。敵機轟炸時老板都逃到防空洞去了,他卻在機槍的掃射下堅持收拾,因為老板答應他可以吃別人剩下的東西;其二,他一路上把衣服丟得精光,但書卻一本未丟,反而一次比一次多。
1944年,李政道終于到達西南聯大。
何兆武、朱光亞、潘際鑾……在時空的長河里,這些個體的上學之路實在太短太微不足道,但對我們民族而言,足以凝結那個特殊年代最高昂的精神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