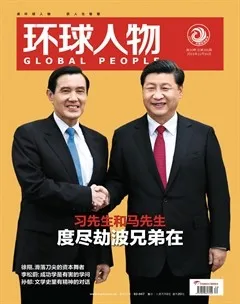李松蔚:成功學是有害的學問

人物簡介
李松蔚,1985年生,四川樂山人,北京大學心理學博士畢業,供職于清華大學,是目前最有人氣的心理學者之一。
李松蔚高且瘦,目光炯炯,頭發根根分明地立著,臉上也多棱角。說起話來卻溫和平緩,即便你覺得應該有頓挫起伏之處,他的語調依舊是波瀾不驚。這或許和他的職業有關——心理咨詢師。其實更多時候,他是一個敏銳且冷靜的觀察者,看穿、寫盡現代城市人的困惑、空虛。
所以,如果用一件器物來形容李松蔚,應該是茶壺吧——陶制,質地細膩,外表卻質樸;圓肚細嘴,平和內斂,內里再多也是不徐不疾。
“恭喜你來到人類的世界”
相比專欄作家抑或心理咨詢師,李松蔚的本職工作似乎并沒有那么為人所知:清華大學學生心理發展指導中心老師,日常的工作就是給在校學生做咨詢——對于這個稍顯冗長的單位名,他調侃道:“我自己都念不順。”每天一早,他先把孩子送到幼兒園,然后乘地鐵15號線從望京到清華東路西口,8點準時上班,下午5點下班。
就在前幾天,孩子哼哼唧唧不想上幼兒園,李松蔚一把把她抱起來,“我要上班了,你別給我在這多事,”然后氣沖沖地去了幼兒園。他和同事聊天,“我現在已經會對我孩子說出‘你要再這樣我就把你扔出去了’這種話,我覺得我墮落了。”同事就笑:“恭喜你來到人類的世界,正常人都這樣。”
就像醫生也得病一樣,心理咨詢師也有著與常人一樣的七情六欲。這位出入于北大、清華的“85后”,也有自己的焦慮。“在這種地方混,不焦慮點都不好意思見人。”
2011年,李松蔚的妻子懷孕了,當時李松蔚讀博士,妻子在中央美院讀碩士。他們在回龍觀租了一個兩居室,一個月3700元的房租讓他們差不多成了月光族。妻子去上課,要從龍澤站——那一站人多得只能用“震驚”來形容——坐地鐵13號線,李松蔚每次會把她送到車廂,等車廂門關上再走。他也想過打車,但沒錢,只能看著妻子大著肚子在人群中擠來擠去。
博士,博士后,留校任教,再一步一步往上走,對這條所謂的“正道”,李松蔚充滿了各種懷疑,“那會,我挺難受的,也挺迷茫的,不知道讀個博士出來能干什么。”
2014年,李松蔚從清華心理系博士后出站,面臨著選擇:想留校任教要先出國做一年訪學;可自己走了對家里的經濟幫不上任何忙。更重要的是,他深深體會到青年教師自由美好生活的另一面,“每天都過得很焦慮,職稱、論文、項目,這些都是慢性壓力。因為你每過一分鐘,只要你沒有在工作、看文獻或者寫論文,就會覺得自己在浪費時間。”最終,他選擇了現在這個單位,雖然上班時間長,但沒職稱、論文的壓力,“我一下子覺得自己解脫了。”
現在,李松蔚依舊有他的心事,他坦率地說,為了買現在這套房子,舉全家之力,還貸了款。但他不那么焦慮了。
李松蔚的困惑、焦慮、心事是個人的,但又不僅僅是他個人的。面對困惑、焦慮和心事,他給出的是思考方向與解決方法——人只有在不斷看清和選擇中,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只能放棄一些東西,才能得到想要的。”
沉下去,而不是站在陽光下
在知乎上,李松蔚人氣頗旺。他的簽名是:不灌雞湯,不玩玄學,不輸出價值觀。
“東方之星”沉船事故后,他寫了一篇文章,不見悲情與煽情,而是理性探討了不可抗力的責任歸屬問題。“不可抗力讓我們正視人類的脆弱,而脆弱催生出另一種堅強。在這種時刻,人類最大的法寶就是聯結。聚到一起,讓苦痛者略覺安慰,讓絕望者不至于孤立無援。”
李松蔚是一個很理性的人,幾次提到自己時,都會說一個詞:現實——想法很現實,選擇很現實,對心理學的認識也很現實。2008年汶川地震,我國第一次啟動了大規模的災后心理干預,李松蔚是男生又是四川人,被導師推薦加入其中。但他發現,這些來自學院派的理論并不能為災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我們拿著心理學量表請他們填,他們根本搞不懂上面那些名詞是什么意思。”另一方面,他看到某位專業人士在媒體前各種作秀,還逼著年紀幼小的受災者“回憶”父母親遇難時的場景。結果,倒是青城山的道士們給災民帶去了不少心理慰藉。
當初,李松蔚剛上心理系,學長們就告訴他:這個專業不好找工作。但到了災區,更大的疑惑來了:心理學到底有什么用?他的答案是:必須以現實為基礎。“心理學應該做的是幫助人們去認清現實,而不是去逃避現實。”
因為過于理性,也有來訪者抱怨說李松蔚不像他們期待的那么溫暖。這時,李松蔚會問對方:“你希望我是什么樣子?如果我溫暖一點,感性一點,我和你的關系會有什么不同?”

對于理性和溫暖,李松蔚看著《環球人物》300期雜志封面星云大師的照片,對記者說:“我覺得像這些高僧,他們挺溫暖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其實我也挺溫暖的,因為我們對人是保持著一種基本的關注和關心。但我覺得高僧們也挺冷的,就像你在寺廟里看到的菩薩,很多時候是冷峻的表情。這個冷、理性就是一種現實吧,比如說生老病死看得太多了,就會變理性。”
在他看來,那種一見到人就滿面堆笑,只講一些積極的、正面的、樂觀向上的人,不是心理學家,只能算是熱心人。“理解或者幫助一個人的時候,我們需要沉下去,跟那個人待在一起;而不是站在一個被陽光照得到的地方,說:你上來啊,你看這里陽光多明媚。”
網購讓人更加孤獨
李松蔚喜歡打太極拳,喜歡看東野圭吾、村上春樹、張大春的書,“最近在看老樹的《在江湖》,我覺得他是在世界里邊泡過,又把自己給拎出來,既出世又入世的一個人,我還沒有達到。”
他曾這樣寫自己,“我是一個內向的人……直到現在,我仍然享受把自己關進一間小屋里的感覺:安全,自在,坦然。有人問我:‘這樣不孤獨嗎?’有這種疑問的人,多半是外向的。他們總以為內向的人只不過是在忍受獨處,就像我們也無法理解外向的人怎么可以‘享受’那么多人聚在一個地方。”
這個對孤獨安之若素的人,在當下都市人身上看到的一大問題是:找不到人生的意義。“現在的年輕一代大部分是獨生子女,對人有種天然的警覺和不信任,加之城市化、網絡化,原本的社會結構被打破,加劇了人與人之間的隔離感。這種對自己的不滿意,對于生命意義、人生意義的不確定性,沒有存在感,人際關系看上去好像很熱鬧,朋友圈里一大堆人,但是沒幾個人可以聊天,這種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一類人的縮影。”這和價值觀偏差不無關系。“現在的價值觀非常單一,馬云說什么了,誰30歲就財務自由了,誰40歲就幾個企業上市了。成功人人都想要,但如果把它作為一個目的去追求,有時候反而是一個壞事——成功學是非常有害的學問。因為成功學會讓你覺得自己非常不成功,甚至厭惡當下的自己,這種厭惡又可能會妨礙你成功。馬云也不是奔著要成為馬云,才取得今天的成就的,但今天很多人在復制他的道路,這個目的性是有害的。”
在李松蔚眼中,現代都市人的另一個問題是:成癮。打游戲、淘寶購物、刷朋友圈……成癮背后是,想借此抵消人生無意義帶來的壞感覺,但這樣做又讓人更加孤寂。但相對于好與壞的簡單價值判斷,李松蔚更樂于提供另外一種看事物的角度。“人的感覺,固有好壞之分。但凡是感覺,無論舒服與否,都有著鮮活的勁兒。借著這些好受與不好受的勁兒,我們才能與他人發生聯系,日子才有了變化和新鮮。有感覺就等于活著,充實、有生命力、不孤寂。失去感覺就仿佛是死亡,或者至少是沒了生機。”
不要跟紅塵俗事離得太近
很多人知道李松蔚是通過網絡。2012年,他開始在網上回答問題。“我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產后抑郁是怎么回事兒。答了之后,也沒什么人關注,我覺得自己還做了一個挺有趣的事。”
幾個月后,李松蔚看到一個網友的提問:現在只能在北京很偏的地方買個小房子,但一直想買個大點的,怎么辦?這個問題嚴格來說和心理學關系不大,卻讓他很有同感。李松蔚勸道:要想買又能買的話,就先買一個再說,“我想用自身的體會提醒你,僅僅因為自己沒房這一現實,過分沉浸在悲觀、絕望這樣的情緒中,乃至于自我懷疑、自我否定,恐怕會讓你失去更多。”
相似的年紀,相似的經歷,相似的困惑,讓李松蔚與很多提問者感同身受:拖延,沉默人格,選擇恐懼,偽裝高大上……在回答“為什么心急如焚時間很緊的人反而更愿意選擇游戲”這個問題時,李松蔚分析:“問題的關鍵在于,你面對的任務讓你痛苦。至于打游戲,只是掙扎的一種渠道而已。真正出了問題的,是生活本身。為什么生活對我們來說竟變得如此艱難?如果能解決這個問題,找到一種安定平和的心態,也就比較容易在適當的時間,做適當的事了。”
還有人問李松蔚是如何靠知乎賺錢的?他也如實回答:“有些人看了我的回答,會給我發私信預約咨詢。另外,線下預約我的來訪者也多了不少,很可能因為我在知乎增加了一些知名度……在知乎基本是不賺錢的咨詢和寫稿。”他還調侃,“別說6位數,離5位數都差得遠。”
同時,他也不忘提醒與反思,“勵志的答案總是會被頂到很高,這多少能反映出用戶的一部分心態,高票的答案又會強化更多人的這種心態。對此,我謹慎地表示憂慮。”
雖然成名于網絡,但李松蔚還是盡量和網絡保持著一定距離。“咨詢師應該保持一個比較節制的狀態。那所謂節制,就是你做好你自己就行了,不需要跟紅塵俗事離得太近。”
鏈接 "李松蔚答網友問
Q:內向、不善社交的人如何建立人脈?
A:如果不是主流話語體系把“獨處”說成“孤獨”,就像見不得人的毛病一樣;同時又給“圈子”“人脈”賦予了絕對的價值,內向的人本來安安靜靜地活得舒舒服服。一個人活得越像自己,就越會吸引同類——這是網絡最好的地方,它讓氣味相投的人更容易發現彼此。每個人在這個世界都有同類,通過知乎的一次問答,或者陌陌的一個群組,同類之間就可以毫無困難地接上頭。你不去找圈子,圈子也有的是辦法找到你。
Q:為什么在做重復勞動時,必須開個視頻聽個響才做得下去?
A:有些人是要不斷地以“新鮮感”喂食的,如果一段時間內沒有新鮮的體驗,就會產生出一種對生活本身的厭倦感。重復勞動是能讓人感覺枯燥的,進而感到厭倦。畢竟這個世界奇妙豐富,特別是有了網絡以后,就可以無比便利地、幾乎不花成本地引入一些新鮮體驗。
不過,有人也許會想:總是“打開視頻聽個響”,到最后會不會久而久之也變成一種“重復”,也產生厭倦感呢?答案是:有很大的可能。到那個時候,就只能反觀枯燥本身,就地尋找出口——那便是另一層修行了。
Q:怎樣克服選擇恐懼癥?
A:小時候考試,遇到兩個看似都可能正確的選項,我會蒙一個。朋友羨慕我的效率,為了幫他提升做題速度,我苦口婆心給他講道理。可他一句話就把我頂了回來:“廢話,你錯得起,我錯得起嗎?!”現在回頭去看,這句話揭示了一個冰冷的真相:我之所以果決,并不是因為我的決斷力,僅僅因為我成績好。
我們有一個幻想:仿佛這個選擇對我們的生活是至關重要的,重要到足以掩蔽其他一切不滿足。幻想的功能,永遠是為了掩蔽現實中的不滿足。就像我那位朋友,在一兩道題上反復較勁,用以逃避他因為學習成績而產生的挫敗和無助。
Q:人既然知道努力就可以進步,為什么還是會不努力?
A: “努力就可以進步”這個信念本身就是沉重,這句話可以翻譯如下:現在這樣,是我不滿意的;我不想繼續像現在這樣;我希望能夠針對我不滿意的方向,持續做一些特定的事情(我知道需要克服大量的痛苦)……
“做事就可以有結果,不管做的是什么事,都一樣。”這句話和“努力就可以進步”,實質上是一回事,但是它們背后的情感含義完全不同。如果你用這句話來取代“努力就可以進步”,也許做事對你來說就會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