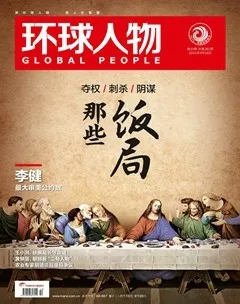哥倫比亞,被咖啡拯救的土地
這片曾經種滿罌粟的罪惡之地,如今是享譽世界的咖啡天堂
我的哥倫比亞咖啡之旅是3年前,從委內瑞拉移居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開始的。在委內瑞拉時,我就常聽別人說:“委內瑞拉在發現石油之前,咖啡可比哥倫比亞的咖啡出名多了。”而哥倫比亞人卻說,這只是委內瑞拉人一廂情愿的懷舊——畢竟經過幾十年的品牌經營,哥倫比亞咖啡已經取得國際公認的好名聲。

現在,大家說起最地道的南美咖啡,大抵上想起的都會是哥倫比亞咖啡。
像喝紅酒一樣喝咖啡
初到波哥大,我對這個城市的第一印象就是濃濃的咖啡香。在薩利特商業中心二樓,十幾家咖啡店聚集在中庭附近,咖啡的香氣在整個空間蔓延;在城市的街頭,隨處可見熱情的咖啡小販,他們拖著小車,手提著裝滿咖啡的保溫瓶,兜售著自制的咖啡。當然,要品嘗到正宗的哥倫比亞咖啡,還得深入城市老區的那些咖啡館里。
我就住在老城燭臺區旁邊,這個區在19世紀前曾被西班牙殖民者統治,如今已經成為歷史文物保護區,也是旅游者必到之處。很多老房子都用來作為各類博物館、學校、小賣店、餐館和咖啡館。這里每一家餐館和咖啡館的裝修風格都不一樣,每天逛不同的餐館和咖啡館成為一種樂趣。據說上世紀40年代,馬爾克斯在波哥大讀大學時,就時常流連于這些精致的咖啡館,這里算是他寫作生涯的起點。
在老城附近的眾多咖啡館中,我最常去的就是黃金博物館樓下的圣阿爾伯托咖啡館。設立于1939年的黃金博物館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器博物館,收藏了約3萬件公元前20世紀至公元16世紀印第安人制作的精美金制器物,是波哥大人氣最旺的旅游景點之一。但大部分來這兒的游客,都忽略了樓下還有一家連哥倫比亞人都嘖嘖稱贊的咖啡館——圣阿爾伯托的咖啡館。
雖然有名,但這家店的咖啡并不貴,兩美元就能喝到一杯。店員告訴我,為這區區兩美元,他們得花上近20個小時。他們采用冷滴法泡制咖啡,這是最需要時間和耐心的。必須先將冷水一滴一滴地滴在一個盛咖啡粉的濾器里,讓水滴慢慢滲透咖啡粉。最后清水在濾器中完全吸收了咖啡的味道,再一滴一滴地滴到下面的咖啡壺里。整個滴漏過程需要7個多小時,之后還要將盛在咖啡壺里的冷咖啡放到冰箱里冷藏12個小時才算大功告成。
除了制作方式,這里咖啡的喝法也甚是講究。服務員先把盛紅酒的酒杯從冰箱取出,對著燈用紙巾仔細擦干凈。再放在電子秤上,放入兩塊冰,最后往里倒入咖啡。這番景象真是讓我受寵若驚——不過就兩美元而已,怎么竟要如此大動干戈,是要營造氣氛還是顯示精貴?服務員把杯子交到我手中后,才告訴我答案:這種喝法叫做“一杯紅酒咖啡”,需要像喝紅酒一樣品嘗,才能嘗出咖啡里的香氣和醇厚。我擦去杯子表面的霧氣,只見咖啡真的就像紅酒一樣晶瑩剔透。
波哥大最大的咖啡連鎖店不是星巴克,而是兩個本土品牌:胡安·帝滋和歐瑪,在市中心繁華地段幾乎到處可見。除了出售有各種調配方法的咖啡外,它們還準備了一些西式點心。當地人晚餐吃得少,經常就是一杯咖啡加面包,所以,面包店和咖啡館是生意最好的地方。


胡安·帝滋是哥倫比亞最出名的咖啡牌子,除了連鎖開店之外,還賣一些咖啡用品和衣帽類的東西。也許是因為這種本土咖啡店太受歡迎,導致星巴克這樣的國外品牌很難滲透哥倫比亞市場,直到去年,星巴克才在波哥大開了第一家門店。
深山里的咖啡種植園
嘗過地道的哥倫比亞咖啡,就更想了解咖啡的種植和生產過程。以前因為種種社會問題高發,為安全起見,游客很難見識到純正的哥倫比亞咖啡種植園,最近十幾年隨著政府對暴力組織打擊力度的加大,越來越多的游客得以見識深山中的咖啡種植場,目睹咖啡生產的全過程。
哥倫比亞咖啡種植園主要集中在“咖啡金三角”,即麥德林、阿曼尼亞與馬尼薩雷斯這三個重要產區形成的三角地帶。這里所產的咖啡在哥倫比亞全國產量中比重最大,質量最優。
我在一個清晨來到“咖啡金三角”。飛機降落在阿曼尼亞時,只見云霧繚繞的山頭一片蔥綠,晨曦給綠野披上了一襲金色的薄紗。接機的司機還沒等我坐穩,就飛一般地朝預定好的農莊駛去。一路上經過的小鎮和田野,彌漫著懶散清閑的氣息,沒有疾馳的汽車,沒有趕路的人們,牲口也是優哉游哉、漫無目的地閑逛,這就是哥倫比亞農村的生活。
司機告訴我,“金三角”其實是安第斯山脈在厄瓜多爾邊境進入哥倫比亞,東西分支后分裂出的一片谷地。這里有火山噴發后形成的肥沃土壤,全年平均氣溫大約攝氏18度,年降雨量為2000至3000毫米,這些天然優勢讓哥倫比亞成為世界上少數能全年收獲咖啡的國家之一。
在哥倫比亞,基本上所有咖啡園都是沿著山脈的高地開辟的,我們開進山里許久才到達目的地——阿格拉多咖啡農莊。接待我的約翰是個高大英俊的年輕人,在這里負責技術和管理工作。他告訴我,“咖啡”一詞源自希臘語“Kaweh”,意思是“力量與熱情”。他說,雖然沒有具體的記載,但現在普遍認為非洲是咖啡的故鄉,當非洲奴隸被販賣到也門和阿拉伯半島等地時,咖啡也就被帶到了沿途各地。哥倫比亞種植咖啡的歷史,則可以追溯到16世紀的西班牙殖民時代:有人說是從加勒比海的海地島,經中美洲的薩爾瓦多從水路傳來的;也有人說由一名牧師從法屬安的列斯經委內瑞拉將咖啡豆首次引入哥倫比亞。
約翰帶我來到莊園的樹蔭下。在那里,已經有幾位小姑娘把桌椅、器具等準備好,正等著我去品嘗咖啡。她們用不同的器具來沖泡咖啡,讓我品嘗后加以比較:傳統的濾紙方法能嘗到咖啡柔軟的酸度;用虹吸壺泡制的方法能更全面地體會咖啡的特質;而針筒壓力法則把咖啡的精華全部擠壓出來,味道更醇厚。除此之外,她們還向我展示了精美的咖啡器具,以及嫻熟的洗杯、燙杯等咖啡藝術。
走進咖啡種植園,只見一片郁郁蔥蔥的綠色中零星點綴著鮮紅的咖啡豆。約翰告訴我,這些樹果采摘后還會被剝殼浸泡18小時。質量好的果子會沉入水中,浮在面上的則去掉,連同殼一起發酵后用作肥料。哥倫比亞非常注重環保,所有能循環利用的物料絕不浪費。最終,留下的咖啡豆還要經過日曬、風干和篩選等步驟。
如此復雜精細的流程,使得烘焙后的哥倫比亞咖啡散發著淡淡而優雅的香味,不像巴西咖啡那么熱情濃烈,也不像非洲咖啡帶著酸意,而是一股甘甜的幽香,有著紳士般的優雅,口感綿軟、柔滑,因此哥倫比亞咖啡又被稱為“綠色的金子”。
一個“不按牌理出牌”的地方
臺灣女作家三毛在游記中形容哥倫比亞是一個“不按牌理出牌”的地方:它的國民一面享受著悠閑的咖啡時光,一面經歷著社會的動蕩;它的土地一半種著金子般的咖啡,一半種著魔鬼般的罌粟。據哥倫比亞最大媒體《時代日報》報道,全球93%的海洛因產自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爾交界。毒品的種植、加工、販賣和轉運確實是哥政府最為頭疼的問題。
1927年,政府組織成立了“哥倫比亞咖啡生產者協會”。這是一個服務于哥倫比亞咖啡農的非營利性組織,也是哥倫比亞唯一的官方咖啡專業行會。80多年來,它為哥倫比亞咖啡的種植、技術培訓和資金支持以及咖啡文化的傳播保駕護航,不僅讓社會治安得到了巨大改善,還造就了哥倫比亞咖啡在世界上的盛譽。因此,它也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行會之一。
在“哥倫比亞咖啡生產者協會”工作的朋友告訴我,協會另一個職責就是嚴格把控咖啡出口,“只要質量不符合高標準,產品不得出口”。也許對于哥倫比亞人來說,咖啡就是這個國家的一張名片。
咖啡的作用已然顯現:去年,英國新經濟基金會評選的全球十大幸福地區,哥倫比亞赫然在列。很多人對此不解,但我卻一點也不意外。在我眼中,哥倫比亞人的確是非常會享受生活的:波哥大市中心的步行街是文藝天堂,隨處可見雜耍、跳舞的藝人;在馬爾克斯文化中心,市民安靜地閱讀著文學大師的巨著《百年孤獨》;而談生意或逛街走累了的人,就會在咖啡館品一品咖啡,歇一歇,聊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