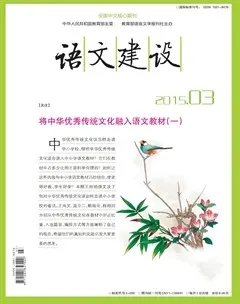語文與傳統文化:從課程說到教材
人類之所以比其他動物高明,就是由于我們總是能夠不斷繼承前人取得的成就,在前人的基礎上向前進步,而不像其他動物那樣每一代都從零開始。研究語文教育,也有一個優秀傳統的繼承問題,先哲說得準確、正確而且又相當透徹的事實或道理,我們倘若不以為意或視而不見,恐怕都不是明智的態度。關于語文與中華傳統文化,據我在寫作這篇短文時的粗略了解,相關的資料少說也有數十萬字,相關的問題也幾乎都有涉及,尤其是葉圣陶、呂叔湘等前輩語文教育家所發表的許多真知灼見,至今仍然值得我們認真參考。
任何人都無法割斷歷史,不管是否愿意,就像人不可能抓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一樣,我們也絕對沒有可能拒絕傳統而不生活在傳統的影響之中。同樣,教育也不可能完全擺脫傳統的懷抱,我們所應做、能做的是自覺積極地熏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自覺積極”說的是態度,“優秀”指的是內容,兩者缺一不可,而且互為因果。當然,我們不是為傳承而傳承,而是為實現教育的根本日的,即人的不斷發展和完善。馬克思所說的“每個人的全面和自由發展”雖然日前還不是我們教育的現實目標,但畢竟是我們的努力方向,而這—努力又哪能離開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呢?我們不是魯迅所說的“孱頭”“昏蛋”“廢物”,要—把火燒掉祖宗留下的大宅子。當然,傳承也不是一定要穿上古人的服裝在孔子或父母面前三跪九叩,而是出于造就一代新人的需要。
就中小學教育而言,首先,我認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不應該也不可能單由語文課程獨自大包大攬,有關思想品德、科學、社會的課程都有實施的必要和空間,大家既各有所司又分工合作。必須特別強調的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在各門課程的教學中不但不應是額外的負擔,而且應該使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起碼不會影響它們完成各自課程標準所賦予的教學任務。其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除了大家常說的古代傳統文化,也不應該輕視更不應該忽視或排斥五四新文化以來的傳統。再說,傳統文化的內容也是豐富多元的,單就人文學科而言,哲學、政治、倫理、歷史、文學等都有極其寶貴的遺產。譬如先秦諸子,儒家同然熏要,其他各家也都頗有值得我們繼承的東西;而漢唐直至五四以來對儒學的反思、批判也有許多閃光的篇什,倘若一慨棄若敝屣,也將使我們成為中華民族的不肖子孫。
平心而論,語文課程應當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要課程之一。就說語文教材,如果剔除我們古代的和五四以來的文化瑰寶,就會瘦弱得十分可憐,以致不成樣子,貽笑大方。不過我們討論的重點可能主要還是古代遺產,就是大家常說的古詩文。這里似乎有一點應予提醒,就是不能將古代文化遺產和語文教材里的古詩文完全等同起來,例如孔子、孟子關于“仁義”的論述,不能僅僅被視為“古文”。——是的,它們的的確確是古文;但我們之所以將其選為課文,又不僅僅南于它們是古文,更有古代文化史這一角度的考量,即由于它們在古代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課文還是這幾篇課文,但在我們語文教育工作者的心目里,又不僅僅是語文課本里的課文。當然,從思想史的角度衡定唐詩宋詞的價值,那也是一個笑話。
語文課程必須培養學生正確理解與運用祖國語言文字的能力,用葉圣陶的話來說這是語文課程的“獨當之任”,必須努力完成,沒有價錢可講。古代文化遺產都是文言作品,因而從另一面看,學習古代優秀作品也就是在學文言。文言和白話是兩種不同的語言體系,雖然兩者關系甚為密切,學習文言有助于學習白話,學習白話也有助于學習文言,但它們畢竟不能相互取代。我們也根本不可能給文言作品脫下文言的“外衣”而穿上白話的“時裝”,因為語言不是作品的衣裳,即使把它翻譯成白話,它同時也就失去了原汁原味。
文言白話兩者都學,我們就必須面對一個比重的問題。由于我們現代中國人使用的都是白話,這就使古代的書面語言(甚至包括當時的大白話)——文言變得難懂難學。假如我們單從學習文言這一角度來看待以文字為載體的古代文化遺產,可能其中不少篇目就不一定要選人語文教材,甚至還在刪除之列。呂叔湘早在1962年就曾指出:“在充分掌握了現代漢語的基礎上,學習文言,達到能讀一般文言的程度,我估計至少得五六百課時,差不多要占去高中階段全部語文課的學習時間,課外作業時間還不算。”而在高中課程改革背景下,高二、高三語文課程每周只有三四課時;加之學生掌握現代漢語的狀況,又遠不如當時,要在有限時間里達到“學習文言”的目標,難度更大。從另一方面看,白話也是要學的。白話不學,其后果可能比不學文言更嚴熏,而且嚴重得多,這不單單南于繼承五四以來新文化的需要,更主要的還是我們今天的生存和發展都離不開白話的緣故。因此,關于上面所說的“比重”,似乎可以肯定應以白話為主。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明確指出:
九年義務教育階段的語文課程,必須面向全體學生,使學生獲得基本的語文素養。語文課程應激發和培育學生熱愛祖國語文的思想感情,引導學生豐富語言的積累,培養語感,發展思維,初步掌握學習語文的基本方法,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具有適應實際生活需要的識字寫字能力、閱讀能力、寫作能力、口語交際能力,正確地理解和運用祖國語言文字。
一般而言,“語文”“祖國語文”“祖國語言文字”可以而且也應該包括文言,但實事求是地說,上引課標文字中之所指應該主要就是現代語文、現代白話,而不可能是文言,因為九年義務教育階段絕對沒有可能達到讓學生獲得基本的文言素養、正確理解和運用文言的程度。這也就決定了義務教育階段乃至整個基礎教育階段語文教學必然以現代語文即白話為主,課標的精神應該說和葉圣陶、呂叔湘、張志公等三老的主張是—致的。文言呢?當然要學,而且非學一點不可。如果一個接受過基礎教育的中國公民,根本不知道孔孟老莊、李杜蘇陸為何人,《桃花源記》《岳陽樓記》為何物,還能算是合格的中國人嗎?我以為,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語文教材,都應當有計劃地選入我國古代頂尖級思想家、文學家的作品。至于相關部分的教學目的,我覺得教育部高中語文課標必修課程之“閱讀與欣賞”部分第九和第十兩條“課程目標”已經說得相當清楚、全面、準確,只是第九條似可補上一句關于培養民族自豪感的內容;而且我還認為,語文教材選編古代文化遺產的代表作品,同然也就是在學習文言,起碼有利于學習文言,但應側重于其文化內涵。
這里要注意幾種比較極端的片面看法。或認為白話三歲兒童就會說了,無須再學,大不了也就是在小學里學會識字而已。其實,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經過百余年的發展,現代語文已經成為一種成熟、精致的語言,和文言相比,它的詞匯更豐富,語法更嚴密,表達也更精確,需要中小學生認真去學。許多優秀的現代語文作品富有很高的審美價值或學術價值,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地位,也值得中小學生認真去學。我們千萬不能低估白話在我國現代文明進程中不可或缺的偉大貢獻。另一種片面看法是呂叔湘早已指出的:“說不學文言就學不好白話文”,“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理論。”還有人認為,文言典雅,白話淺俗。其實,既有淺俗的文言,也有典雅的白話,雅俗不能光以文白來分。
“比重”問題若能從大的方面定下來,所要商量的就是教材里文言和白話的具體比例問題,為主的“主”頗具彈性。我的建議有三點。一是關于文言篇目的編選一定要慎之又慎,精益求精。如《出師表》無非一個“忠”字而已,且其所忠非人,行政又重在“人治”,從作品思想性而言似可撤下。民國語文教材曾編人的黃宗羲《原君》,閃爍著民主性的光輝,理應把它請同課本。李贄《題孔子像于芝佛院》敢于堅持不一概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觀點,語言淺近,文章短小,說理透徹,似可進入待選的行列。我這里只是略舉幾例而已。由于“名額”有限,十分珍貴,因此必須徹底清除次品。二是文言詩文在課本中的分布問題,小學、初中、高中應逐段增加,每段之內則是逐級增加,到了高三,五五之比似乎可以考慮,“五五”已由“為主”轉向“并重”了。三是適量增加有關傳統文化的選修課和課外活動,選修要做到真正選修,參加相關課外活動也必須要真正自愿,以便給對傳統文化特有興趣的學生提供一個多學一些的平臺。例如,古人非常講究詩文的聲律,《文心雕龍·聲律》謂:“故言語者,文章關鍵,神明樞機,吐納律出,唇吻而已。”今人若要真正走進古代詩文的感情世界,絕對不能無視平仄這道門檻。我們的古代詩文教學不講平仄已經多年,好像已經成為新的傳統。這白有它的必然之理,我絕對不主張中小學生去學平仄;但可以甚至應該為欲學者列入相關的選修課作為教學內容,以為今后愿意從事文、史、哲研究者打下一個初步的基礎。
教材還有一個編排問題。這次我特地略翻了幾種教材,印象是散和亂,古詩文東一單元西一單元,單元內也往往是東一篇文章西一篇文章,隨意性較大。教材關于傳統文化的編排還有較大進一步改善的空間,我的想法是相關課文在每冊里還是獨立成為一個部分為宜,而每冊的這一部分,義務教育階段和高中階段應當通盤考慮,相互照應,從而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不能各自為政,自立山頭。例如,上文提到的孔子、孟子有關“仁義”的論述,兩個階段都應當有,但其內容應據兩個階段不同學生的年齡特征而有不同的側熏。兩個階段內部各自也都應是有機的整體,各年級、各冊、各單元乃至各課之問雖各有個性,但都是同一網絡里的一個節點,決非烏合之眾。換言之,如果將它們從課本里抽取出來合在一起的話,那就是一本極好的有系統的古代文化讀物、有代表性的古詩文讀物,而不是勉強湊在—起的散兵游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