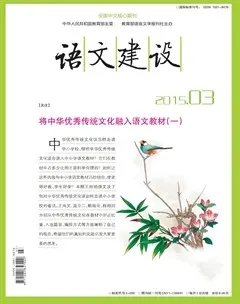“水月之喻”與“物不遷論”
宋神宗元十五年(1082),蘇軾游覽黃州赤鼻磯,寫下了“空曠高邈,敻不可攀”的《赤壁賦》。全篇以跳宕灑脫的單行奇句,沖破了韻語整飭板滯的文勢,真正如萬斛泉涌,縱恣自然。從文體來說,這是一篇文賦,即以古文之筆法來寫“四六”。賦的特點之一,便是“主客問答”,《赤壁賦》也遵循了這種同有的寫作程式;只不過,這篇文章中那個吹洞簫的“客”,確又實有其人。他叫楊世昌,“原是綿州武都山的道_上,與東坡誼屬同鄉(xiāng)”。歷代讀者也都會覺得,這是一篇道教色彩十分濃郁的文章,如宋代謝枋得在《文章軌范》中,就曾明確指出“此賦學(xué)《莊》《騷》文法”。
然而,清代宋長白卻也曾指出了一個頗為奇怪的現(xiàn)象:“今畫家作赤壁圖,不畫道士,而畫一僧,指為佛印,且又指一人為黃山谷,不知何所據(jù)耶?”(《柳亭詩話》卷二一)在這里,宋長白對《赤壁圖》只畫和尚、不畫道士感到十分不解。其實,這種不解也就從一個側(cè)面揭示出了《赤壁賦》與佛教的淵源。清代儲欣在《唐宋八大家類選》中也曾說,該文“出人仙佛,賦一變矣”。“出入仙佛”,白是有佛。林云銘《古文析義》更是指出,“迨至以水月為喻,發(fā)出正論,則《南華》《楞嚴》之妙理”。《楞嚴》,即《楞嚴經(jīng)》,是一部大乘經(jīng)典,也是末法時期佛教最重要的一部經(jīng)典。
本文認為,《赤壁賦》更多的只是化用了一些儒、道的語典,儒、道對其影響主要集中于文學(xué)技術(shù)層面,是一種創(chuàng)作手法的表現(xiàn);而真正促成蘇軾由“悲”轉(zhuǎn)“喜”的,其實是佛教思想。下面,筆者將主要從文本中的佛教語匯以及“物不遷論”對“水月之喻”的影響兩個方面,來具體分析一下禪佛思想對《赤壁賦》的影響。
一、對禪佛語言的化用
《赤壁賦》的文本中雖然出現(xiàn)的道家語匯比較明顯一些,如“羽化”“飛仙”等;然而,這篇課文中佛家的語典也不少,如“一葦”“無盡”“無盡藏”等詞語。下面筆者逐一加以分析。
“一葦”這個語典出于《詩經(jīng)·河廣》:“誰謂河廣,一葦杭之。”隨著達摩泛海東來,便也留下了“一葦渡江”的傳說。“達摩于梁武帝普通元年,自西土泛海至金陵,與武帝語,師知幾不契,遂去梁,折蘆渡江,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因此,這里的“一葦”,視作佛家語也不是不可以的。
“無盡”這個詞出白于佛教。《大日經(jīng)疏》卷十四:“無盡者,即是無相別名。”《華嚴大疏》卷十六:“無相如空。”因此,這里的“無盡”就是“空”的意思;除此之外,“無盡”在佛經(jīng)中還有一種意思,即永恒不變。《維摩經(jīng)·菩薩行品》日:“何謂無盡?謂無為法。”僧肇《注維摩詰經(jīng)》卷九:“無為法無三相,故無盡。”三相,指事物的產(chǎn)生、變異和消亡等三種形態(tài),無三相,即無始終,自然是永恒不變的超時空的絕對。故《般若心經(jīng)》日:“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凈,不增不減。”“可知,蘇軾所謂‘白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說的正是‘萬物與人類一切皆空’的意思。”
“無盡藏”也源自佛教。《佛地經(jīng)論》卷五:“陀羅尼者,增上念慧,能總?cè)纬譄o量佛法,令不忘失。于一法中,持一切法;于一文中,持一切文;于一義中,持一切義。攝藏?zé)o量諸功德,故名無盡藏。”無盡藏,也就是說佛德廣大無邊,作用于萬物,無窮無盡。《大乘義章》卷十四:“德廣難窮,名為無盡。無盡之德苞含日藏。”唐法藏《華嚴探玄記》卷十九:“出生業(yè)用無窮,故日無盡藏。”
二、“水月之喻”與“物不遷論”
《赤壁賦》的情感線索,一般都會用由“樂”生“悲”,再南“悲”轉(zhuǎn)“喜”來概括;當(dāng)然,這樣概括沒有錯,卻流于表面化,未能從深層次上說明作者情感的變化過程。筆者認為,作者情感變化大致是這樣的:“美人”遠在天一方,想望而望不見;望“美人”不見,便欲“挾“飛仙以遨游”;但求仙也不可驟得,于是,便只能通過“水月之喻”來安慰自己,給自己尋出一條精神解脫之路。“美人”喻指君主、朝廷,此時蘇軾的儒家濟世之志受挫,轉(zhuǎn)而想追求道家所宣揚的遺世長生;然而,道家這種求仙飛升的想法畢竟也太過縹緲虛幻了,很難令蘇軾真心信服,所以,他只能從禪佛中尋求自我解脫的法門。
《赤壁賦》中,蘇軾以“水月之喻”論證“變”與“不變”,其實就是源于佛家。據(jù)《朱子語類》載,朱熹的一個弟子就曾對這段議論提出異議:“此語莫也無病?”朱熹回答說:“既是‘逝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虛如代’(筆者按:據(jù)《朱子語類》載,朱熹曾親見《赤壁賦》的東坡手稿,“盈虛者如彼”寫作“盈虛者如代”),如何不消長?既不往來,不消長,卻是個甚么底物事?……東坡之說,便是肇法師‘四不遷’之說也。”(卷一三0)朱熹這里所謂的“肇法師”,就是僧肇。關(guān)于這個問題,朱熹在《朱子語類》另一處說得更加明白:“今世所傳《肇淪》,云出于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兢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岳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卷一二六)南開大學(xué)陳洪教授也指出:“通常的看法認為這是老莊哲學(xué)的翻版。就其中復(fù)歸自然、順命乘化的人生態(tài)度而言,這也是有道理的。不過,更直接的思想淵源,還是應(yīng)追溯到佛門。論近源,這段話的核心觀點與禪理相通(尤其是南宗禪);論遠源,則與《肇論》有十分密切的關(guān)系。”
僧肇,東晉僧人,曾師從鳩摩羅什研習(xí)佛典。現(xiàn)存《肇論》,為后人所編,收錄僧肇佛學(xué)論文七篇,其中《物不遷論》即是《肇論》中的一篇。“僧肇在此論中討論了客觀事物的運動和靜止問題,得出運動是假象、靜止為恒定的結(jié)論。”僧肇在《物不遷論》中說:
尋夫不動之作,豈釋動以求靜,必求靜于諸動。必求靜于諸動,故雖動而常靜。不釋動以求靜,故雖靜而不離動。然則動靜未始異,而惑者不同。緣使真言滯于競辯,宗途屈于好異。所以靜躁之極,未易言也。
這段話對“動”與“靜”的關(guān)系做出了極為辯證的闡釋。湯用彤就曾明確指出:“肇公之學(xué)說,一言以蔽之日:即體即用。其所著諸論中,當(dāng)以《物不遷論》為最重要。論云:‘必求靜于諸動,不釋動以求靜。’又言‘靜而常往,往而常靜。’均主即動即靜。”“動而常靜”“靜而不離動”“動靜未始異”,動靜是相對的、辯證的;但“物不遷論”,其實是更強調(diào)了“靜”。“南‘物不遷’的觀點看來,運動是俗見,是假象;靜止才是佛見,是根本。”《赤壁賦》中,蘇軾認為從“變”的角度來看,萬物都在動,沒有什么是能夠長存不朽的;若從“不變”的角度來看,自己就會和那“水”“月”一樣都是無盡的,這其實也就是所謂的“物不遷”。課文中,蘇軾也就是以這種“物不遷”的“佛見”來開導(dǎo)“客”,從而使其轉(zhuǎn)“悲”而“喜”了。僧肇在《物不遷論》中還說:
夫人之所謂動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動而非靜;我之所謂靜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靜而非動。動而非靜,以其不來;靜而非動,以其不去。然則所造未嘗異,所見未嘗同。逆之所謂塞,順之所謂通。茍得其道,復(fù)何滯哉?
這一段話,不僅意思對“變”與“不變”存在著影響,甚至連語言的表達方式都給蘇軾以直接的參考。“茍得其道,復(fù)何滯哉”,與“而又何羨乎”的語氣是多么相似!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jié)論:在《赤壁賦》中,雖然出現(xiàn)了不少儒、道兩家的語匯,但這種語匯更多地表現(xiàn)為一種文學(xué)創(chuàng)作層面的化用,如“逝者如斯”等;而真正使“客喜而笑”,促成作者思想轉(zhuǎn)變的則是佛家的“物不遷論”。儒釋道三家在這篇文章雖都有體現(xiàn),量而言之,《赤壁賦》中儒家思想最淡薄,儒道互補,道家雖在試圖“補”儒,但也未能解決問題,更像是在為最后佛教思想引入而做鋪墊。因此可以說,佛教思想才是這篇充滿縹緲仙氣的《赤壁賦》之精神內(nèi)核。
元豐二年,蘇軾因被誣以詩譏刺朝廷,讓人關(guān)進了御史臺監(jiān)獄。出獄后,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元豐三年二月初一,蘇軾到達黃州。在等待家眷到來的過程中,他曾一度寓居于定慧院。寓居期間,他和僧人一同吃飯散步,開始親身經(jīng)受佛法熏染。正如柳宗元所言,“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恥制于世者,則思人焉”(《送玄舉歸幽泉寺序》)。身罹大難,蘇軾“開始沉思自己的個性,而考慮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寧。他轉(zhuǎn)向了宗教”,而他轉(zhuǎn)向的宗教,就是“大而多容”的佛教。
蘇軾自己在《與章子厚參政書二首》中也說,“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jīng)以遣口”(《蘇軾文集》卷四十九)。在《安國寺記》里,他也曾說:“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蘇轍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中也說:“既而謫居于黃,杜門深居……后讀釋氏書,深悟?qū)嵪啵瑓⒅住⒗希┺q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欒城后集》卷二十二)在黃州期間,蘇軾還自號“東坡居士”。“居士”一詞為梵語意譯,“原指古印度吠舍種姓工商業(yè)中的富人,因信佛教者頗多,故佛教用以稱呼在家佛教徒之受過‘三歸’‘五戒’的在家教徒”。《維摩詰經(jīng)》稱:“維摩詰居家學(xué)道,號稱維摩居士。”慧遠《維摩經(jīng)義記》:“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為居士。”南此可見,黃州時期,佛教思想對蘇軾影響之深。
《赤壁賦》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寫作出來的,因此研究其中的禪佛思想,對于準(zhǔn)確而全面地分析這篇課文自然也就不無裨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