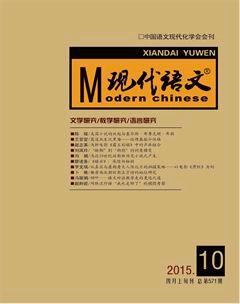蘇軾晚年詩歌中的道教環境分析
摘 要:蘇軾作為北宋三教調和的代表,其思想中存有道教的因子。究其一生,他仕途坎坷,命運波折,思想和創作中道教的成分也越來越濃,特別是在被貶嶺海以后,對仕途的失望和對每況愈下健康狀況的擔憂,常常促使其投向道教。東坡晚年詩歌中,經常會出現關于道教環境詞匯的描寫,來抒發自己想擺脫現實、羽化升仙的愿望。
關鍵詞:蘇軾晚年詩歌 神仙 丹道
道教是一種關懷生命的宗教,給人以精神上的慰藉,使人能從現實痛苦中得以解脫和超越。北宋中后期黨爭傾軋不斷,蘇軾個性和政治立場鮮明,常與當權派政見相齟齬,仕途坎坷,數遭貶謫,晚年更被貶至地遠天荒的海南島。此時,詩人已是垂暮之年的老人,經濟狀況窘迫,生活環境惡劣,身體健康也每況愈下,詩人大半生儒家經世致用的熱忱逐步消退,內心也更加向往單純、寧靜和安定的生活。道教追求天人合一,物我兩忘,逍遙自在,這一理念正契合了飽經滄桑的詩人之心,晚年東坡[1]耽于佛禪的同時,亦頗醉心道教,以排遣內心憂慮,擺脫世俗牽絆,他也利用丹道促進健康、延年益壽。因此,晚年蘇軾及其文學創作同道教的關系密切,本文試以其晚年詩中的神仙環境描寫為研究對象,做一簡要闡述。
一、東坡晚年詩中的道教環境典故
神仙原本并不存在,是由人類想象出來的,故而他們也必然帶有人的色彩,需要生活起居,居有定所。在道教典籍中,仙人生活的地方一般都遠離鬧市,處于偏遠而空曠的山澗或叢林密布的洞穴。那里幽謐、安靜、清雅,溪水潺潺,云霧繚繞,和諧地與大自然為伴,是仙人們修煉和生活的理想之地,其居室特點往往是:或青山秀水環抱屋宇,或樓臺亭閣充滿靈異,或泉源飛瀉掩蓋洞穴,或流霞云霧彌漫山峰,宛若人間仙境,世外桃源。
道教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以及各種宮觀、仙島、靈山等,處于大地名山之間,是由上帝派來的真人治理,也是這些神仙得道之所。司馬承禎在《天地宮府圖并敘》中說:“夫道本虛無,因恍惚而有物;氣元沖始,乘運化而分形;精象玄著,列宮闕于清景;幽質潛凝,開洞府于名山。……至于天洞區畛,高卑乃異;真靈班級,上下不同。”[2]指出了神仙居處產生的原因及其特點。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作為社會的有機組成,每個人都無法避免各種拘束與煩惱,身心不得自在,于是人類便想象出神仙仙境。那里環境優美,遠離世俗,不受任何制度的制約,無拘無束,也沒有任何疾病與災難,任意逍遙。蘇軾作為一名在籍官員,仕途頗為坎坷,晚年身處海南,時時要面對政敵迫害,外加環境不適、經濟窘迫、疾病發作,現實政治環境和自然環境如此惡劣,更促使他努力追求神仙仙境,希望在那里可以放下世間的煩惱,得到解脫。因此,在蘇軾晚年詩歌中,出現了很多有關道教神仙居住環境的描寫。這些環境若按類型來分,主要有以下幾類:一是與水有關的,有天池、洞庭;二是名山大川,有岷山、王屋山、九嶷山、會稽、都嶠、三島(蓬萊、方丈、瀛洲)、潛山、天柱山、虔州崆峒山;三是生活環境,有紫翠、玉京、石門;四是宮觀,有玉局。在這四類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蓬萊”,其次是“紫翠”,最后是“玉局”。
道教有十大洞天,處大地名山之間,是上天遣群仙統治之所。王屋山由西城王君治之,是第一洞天,號稱小有清虛之天。第九洞天林屋山在洞庭湖口,屬北岳真人治之,黃帝曾率眾神在洞庭湖畔歌舞。三十六小洞天和各處福地,是由一般神仙治理。第十會稽山洞,由仙人郭華治之,因大禹會計功于此集諸侯,故名會稽。第二十都嶠山洞,名曰寶玄洞天,仙人劉根治之。第二十三九疑山洞,屬仙人嚴真青治之。舜曾被胡人授《十轉紫金丹方》,轉至南巡九嶷山,后尸解而去。左慈曾在潛山煉丹,也一度于天柱山中精思,得神人所授金丹仙經。“瀛洲”“方丈”“蓬萊”三島自古以來就是人們向往的神仙仙境,那里地處東海,云霧繚繞,有仙草神水,神仙云集。“瀛洲”島上有“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名之為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3]“方丈”島“群仙若欲升天者,往來此洲受《太上玄生箓》。仙家數十萬,瓊田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亦有石泉,上有九原丈人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蛇巨鯨陰精水獸之輩。”[4]“蓬萊”更是求道之人津津樂道的去處,經常出現在文人詩文中。由于地勢險要,唯有飛仙才能到達那里,因此也更容易引起人們的好奇之心。這些仙居都頗有特色,或紫翠縈繞,“時出紫翠風”(《過廬山下》)、“遙知紫翠間,古來仙釋并”(《碧落洞》)、“飛上千峰紫翠間”(《浴日亭》)、“縹緲新居紫翠間”(《白鶴峰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二首》之一)、“南嶺過云開紫翠”(《三月二十九日二首》之一),繁花似錦,若隱若現,飄渺云海;或玉京般撲朔迷離,“高處連玉京”(《碧落洞》)、“人間有次白玉京”(《游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恍兮若兮,令人遐想無限;或石門高聳,“果然石門開,中有銀河傾”(《碧落洞》),幽靜孤寂,神秘而仙氣十足。
二、東坡的“玉局”情結
在這里筆者想著重說一下“玉局”。四川是道教興起和繁盛之地,青城山歷來就屬于道教名山,在這樣的環境氣氛中,川人好道并非偶然。蘇軾是四川眉山人,其思想中有道教的影響,尤其是晚年表現的更為明顯,經常會想起故鄉的名山,以及故鄉的宮觀“玉局”。據《云笈七簽》“二十四治”所載:“第七玉局治。在成都南門內,以漢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太上老君乘白鹿,張天師乘白鶴,來至此坐局腳玉床,即名玉局治也。治應鬼宿,千丈大人發之,治王三世。”[5]
六十而知天命,對大部分人來說已過人生大半,宦海一生,此時會選擇退隱還鄉,享受天倫之樂。但對晚年蘇軾來說,卻連遭厄運,被貶至偏遠的海南島,生活的不適和內心的凄苦可想而知。無論是出于傳統思想,想落葉歸根,還是出于對現實的失望與無奈,羽化升仙,總之,晚年蘇軾雖然在艱難中也能勉強寫出“海南萬里真吾鄉”的詩句,但和早年詩歌中善于享受眼前快樂相比,此時懷鄉之心卻更為濃烈。南下途中,眼看離故鄉越來越遠,他想起了青城山山頂上清宮的天池,“天池水落層層見,玉女窗虛處處通”(《壺中九華詩》),也想起了道教靈山岷山,“岷峨家萬里”(《望湖亭》),而且還實際探索了具體回鄉之路,“似聞崆峒西”(《次前韻寄子由》)。此處“崆峒”是指虔州之山,其西乃歸蜀之路,也是黃帝謁廣成子學道之處,詩人希望能借助神仙的幻術早日歸蜀。想必當局也一定熟知蘇軾好道的習性,所以貶他為成都玉局觀提舉,這也正符合了詩人此時心境,雖然仕途不順,但至少可以回歸故鄉,專心修煉,遠離官場的是是非非,不受世間煩惱的侵擾,獲得內心的寧靜,所以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詩中多次提及“玉局”。北歸途中,詩人難掩興奮之情,此刻他想起的不是汴京,而是遠在千里之外的故鄉,“劍關西望七千里,乘興真為玉局游”(《過嶺二首》之一)。歷經半生榮辱,詩人深深體味到“寵辱能幾何?悲歡浩無垠。回視人間世,了無一事真”(《用前韻再和孫志舉》),還不如回到故鄉,做一個道士“灑掃古玉局,香火通帝闉”(《用前韻再和孫志舉》)。蘇軾四十歲以后身體漸趨衰朽,到晚年愈烈,特別是痔疾屢屢發作,詩人見到和自己同齡的清都觀道士仍是童顏鬒發,不免唏噓,慨嘆道:“鏡湖敕賜老江東,未似西歸玉局翁。敧枕未容春夢斷,清都宛在默存中。每逢佳境攜兒去,試問行年與我同。自笑馀生消底物?半篙清漲百灘空。”(《永和清都觀道士,童顏鬒發,問其年,生于丙子,蓋與予同,求此詩》)還未去玉局任上,蘇軾已心起擔憂,希望自己到成都后,能專心學道,不要被朝庭政局所干擾,陷入黨爭漩渦。他借徐佐卿化鶴的典故把這一憂慮婉轉的傳達出來,“玉局西南天一角,萬人沙苑看孤飛”(次韻郭功甫觀予畫雪雀有感二首》之二)。
總之,處于現實社會中,由于種種限制和約束,人總在壓力中求生存,伴有各種遺憾和缺失,由此才幻想出一個神仙仙境,那里沒有煩惱,自由自在,可謂世外桃源,能躲避人間的種種災難和不幸。作為蘇軾本人也是如此,生活和仕途的挫折,逐漸磨平了他內心的斗志,逐步走向道教,希望在神仙的世界里能暫時慰藉那顆疲憊的心靈,哪怕只是片刻的停留,由此,他在晚年寫了大量關于道教神仙的詩句。
注釋:
[1]本論文研究東坡晚年道教詩,參照王文誥校箋《蘇軾詩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本)和馮應榴輯注《蘇軾詩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本)為底本,詩歌卷數和所引用的頁碼,以王文誥本為主。蘇軾晚年詩歌以王文誥校箋《蘇軾詩集》來界定,時間劃定為:起于紹圣元年(1095年),終止于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7月28日詩人病卒。從詩人的年齡跨度來看,是其59歲至66歲這7年中心路歷程的體現,共有詩作458篇。
[2][3][4][5][北宋]張君房:《云笈七簽》,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608頁,第593頁,第602頁,第645頁。
參考文獻:
[1][宋]蘇軾撰,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2.
[2][宋]蘇軾撰,[清]馮應榴輯注,黃任軻,朱懷春校點.蘇軾詩集合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宋]張君房編,李永晟點校.云笈七簽[M].北京:中華書局,2003.
[4]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M].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
[5]鐘來因.蘇軾與道家道教[M].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6]葛兆光.道教與中國文化[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7]葛兆光.想象力的世界[M].北京:現代出版社,1990.
[8]葛兆光.中國思想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
[9]孫昌武.道教與唐代文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10]陳平原主編,葛兆光著.中國宗教、學術與思想散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11]卿希泰主編,詹石窗副主編.中國道教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胡浮琛,呂錫琛.道學通論:道家·道教·丹道[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13]雷曉鵬.蘇軾的道教審美人格理想[J].安徽大學學報,2006,(2).
[14]李豫川.蘇軾與道教[J].中國道教,1996,(2).
[15]郭鵬.宋詩革新與淡泊精神[J].人民政協報·學術專刊,1999,(19).
(安麗霞 北京語言大學漢語學院 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