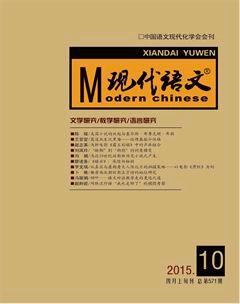一種故事,兩種講法
摘 要:知俠的《鐵道游擊隊》[1]和管樺的《辛俊地》[2]都是十七年時期的革命歷史作品,二者在對歷史圖景的建構及歷史中作為個體的人的塑造等方面呈現出很大的差異,顯示出兩位作家不同的寫作姿態和文學立場。
關鍵詞:十七年文學 《鐵道游擊隊》 《辛俊地》 比較研究
十七年文學的外在時代特征是政治文化高度發達,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和革命浪漫主義情懷成為其特有符號和標志。面對高揚的政治理想和紅色激情的社會氛圍,十七年文學不可獨善其身。作為對時代精神的積極呼應,絕大多數作家主動接受時代召喚,調動自身個體經驗和寫作資源,表現出強烈的敘事愿望和敘事沖動。其所建構的文本世界中關于革命、階級等種種政治功利化色彩不可剝脫,成為當時文藝界的創作主流。當然,也有極個別作家在面對紅色時代時并不是一味地“隨聲附和”,多少保留著自身獨立的文學寫作,在文學創作中流露出與時代不合拍的“異端”思想,成為文藝界創作的支流并因此而受到批判。
本文以十七年革命歷史小說中同樣講述抗日故事的《鐵道游擊隊》和《辛俊地》為例,比較研究二者在對革命歷史敘事中呈現出的文本風景及其背后的深層意義。
一、英雄塑造:群體與個體
知俠的《鐵道游擊隊》發表于1954年,是一部關于抗日英雄的傳奇故事。單從小說書名來看,其對英雄形象的塑造是以群體團隊的形式呈現的,和《敵后武工隊》的命名一樣,塑造的是集體英雄群像。
它以山東魯南地區一支游擊隊的戰斗經歷為故事原型,經過藝術加工和想象,塑造了一系列如劉洪、李正、王強、彭亮、魯漢、芳林嫂等傳奇英雄形象,他們風華正茂,朝氣蓬勃,充滿生命活力的形象,給革命帶來無限希望和光明。他們融洽相處,同仇敵愾,肝膽相照,形成溫暖的革命集體。他們的抗日傳奇故事驚天地泣鬼神,搞敵人機槍、拆敵人炮樓,夜襲臨城,決戰微山湖等情節曲折驚險,引人入勝,緊緊抓住讀者的心弦。在他們身上既有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和理想主義激情,也充滿了令人無限想象的神性色彩,特別是他們進山受訓之后,身上原本的草莽色彩幾乎消失殆盡。
在談起對這類英雄形象的建構塑造時,知俠曾經談起他們的原型問題。鐵道游擊隊隊長劉洪形象原型是現實中大隊長洪振海和劉金山兩人,由于微山湖之戰失利,導致洪振海犧牲。“老洪在這次戰斗中,表現得是絕頂勇敢的。可是從軍事觀點看,這次戰斗是違反游擊戰術原則的。”“而老洪是小說里的主要英雄人物,在即將最后勝利的時刻,竟在一次不該進行的錯誤戰斗中倒下,有損這一人物形象。”“我把兩個人物的性格糅合在一起,使他成為一個經過加工制造的完整的英雄形象。”[3]經過藝術加工的劉洪在文本中非但沒有犧牲,反而像《林海雪原》中的楊子榮一樣鮮活地存在于文本中,更幸運的是他還收獲了芳林嫂的革命愛情。政委李正形象則是現實生活中杜季偉和其他三個政委的“集合體”。據作者講述,杜由于愛上被游擊隊員打死的附敵妹妹,和劉金山、王志勝發生決裂,被迫調動工作離開游擊隊。而小說中的李正形象經過典型化處理,成為在政治道德方面完美無瑕的英雄。小說中林忠、魯漢等幾位英雄形象的原型則是現實中一名叫徐廣田的甲級戰斗英雄,因他身上的“個人英雄主義”和解放戰爭期間復雜的個人歷史而被排斥在文本之外,最終無法進入讀者的閱讀視野。
管樺的中篇小說《辛俊地》發表于1958年,是關于革命英雄的另類文本,呈現出另類的革命歷史風景。它以英雄個體命名,投射出革命英雄本身的獨一無二性。文本敘述的是發生在1940年春天冀東根據地的抗日故事,聚焦表現的是“一個人的抗日”及其悲劇下場。辛俊地作為年輕的游擊隊員,對日作戰異常勇敢,但他自由散漫,具有個人英雄主義傾向。他擅自打死偽警備隊長(實為八路軍的“關系人”),并在游擊隊伏擊戰中,違反紀律過早開槍,破壞整個作戰計劃,致使戰友們死傷嚴重,給革命事業帶來嚴重損失,他卻仍然執迷不悟,拒絕政委教育和戰友批評。在被逐出抗日隊伍后,他開始了單槍匹馬的個人抗日,但個人英雄主義和自由散漫的習性依然如故。最后,在跟蹤特務的路上辛俊地被尾隨的地主徐懷冰開黑槍打死。
很顯然,與同是講述抗日故事充滿傳奇色彩的《鐵道游擊隊》不同,這位英雄形象更多帶有鄉間樸實農民的特征,包括農民的正直善良,也包括農民的瑕疵缺陷。他的身上少了其他作品中英雄身上的政治道德色彩,多了平凡世俗和“原生態”性質,因而具有作為歷史中的“人”的寫實傾向和自然主義特征,其年輕短暫的人生經歷也因而有了更復雜豐富的內涵。在這個英雄人物身上,典型性格就是被集體隊伍所詬病的“個人英雄主義”,這與劉洪、李正、王強等傳奇英雄們光輝高大的革命形象形成鮮明對比,顯得格外獨異。他的這一思想理念是如此“頑固不化”,革命思想和政治覺悟在他身上始終停留在模糊曖昧狀態。他始終以“自我”為中心,自以為是,和集體隊伍產生矛盾和隔閡,排斥集體的批評教育和政治改造,至死都沒有進行精神成長和思想升華的歷程。這與《鐵道游擊隊》典型化處理英雄形象的方式大相徑庭,也與塑造完美無瑕的道德理想主義英雄的十七年文藝要求相沖突。
在十七年革命歷史文學敘事中,政委和隊長形象往往就是英雄們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家長”,引導著他們的精神成長和思想進步。政委和隊長們往往高瞻遠矚,行為果敢,決策正確,對戰斗起著重要作用,在戰斗集體中也有威信。如《鐵道游擊隊》中政委李正對劉洪、小坡等人的思想政治改造。《辛俊地》的政委和隊長形象的塑造顯然少了道德理想主義色彩,同樣具有了和辛俊地一樣的人的世俗性,少了“黨性”和“神性”。游擊隊伍的政委李興性格性情溫和,缺少雷厲風行的果敢作風。當要開除辛俊地時,他袒護說:“我參加革命的時候,才懂多少事情?還不是黨教育了我們。”白虹作為一隊之長,性情急躁,工作作風簡單粗暴,在辛俊地無意打死“內線”時他并未耐心地從政治高度對其進行教育開導,以擔當革命導師和政治家長的責任,而是異常憤怒,意氣用事地將辛俊地逐出抗日隊伍,“我們隊伍里不要你這種人,給我滾!滾!”。自尊心受到傷害的辛俊地也賭氣地說:“我走,我走,離開你們一樣抗日!”當辛俊地受到敵人威逼利誘時,他表面答應敵人不抗日,再次找到政委和大隊長時,他卻被當作叛徒看待,白虹甚至要求將他送交軍法處審判,顯示出革命集體中相互不信任的蕪雜一面。
辛俊地的戰友們同樣是作為有缺陷的鄉間凡人形象而存在的。在他犯了嚴重錯誤時,他們嚴厲指責其“個人英雄主義”,諷刺他要是當了大總統,不是獨尊就是獨裁。這種無情的挖苦諷刺,哪里讓人感受得到革命同志之間的革命友誼呢?小說無意間揭去革命隊伍中溫情脈脈的面紗,暴露了革命集體內部的矛盾及不和諧的音符。同時,文本打破十七年文學中常見的“勝利大團圓”結局模式,以英雄人物的死亡作結,充滿了濃厚的悲劇氛圍,在這個拒絕改造和精神成長的英雄身上包含了作為歷史中平凡個體的復雜性和多元性。
二、愛情言說:圓滿與悲劇
愛情是人類永恒的話題,也是文學表現的常見話題。在文學臣服于政治的年代,文本中的愛情言說顯然是出于“受控”狀態的。又由于“英雄+美人”比較符合傳統大眾讀者的閱讀口味,因此,無論是十七年的農村小說還是革命歷史小說多少都涉及英雄們的愛情敘事。當然這種愛情敘事和傳統文學中講究社會身份、財富、地位等多方面的“門當戶對”的愛情敘事不同,它們大多是染上政治色彩的,屬于革命化、政治化的愛情,講究的是革命、階級和政治身份的“門當戶對”。愛情雙方往往是文本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包括志同道合的革命男性和革命女性,他們經歷革命和愛情的雙重磨難,最終收獲革命和愛情的果實,實現革命和愛情的“大團圓”。“世俗幸福的獲得者終歸還是革命者。此時期的革命意識形態對世俗幸福的態度,是既有排斥,又做了‘定向控制和‘定向分配。”“革命文本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宣告了革命者對優質情愛資源的最終占有,并賦予這些優質愛情以神圣的革命意義。”[3]
《鐵道游擊隊》中的愛情言說是非常稀缺的,唯一的愛情線索是劉洪和芳林嫂之間并不那么明顯的愛情故事。在劉洪受傷被芳林嫂照顧的日子,這個豪情萬丈的傳奇英雄流露出其作為“人”的柔情一面,文本細膩描寫了此時的劉洪對芳林嫂的深情思念,暫時脫去了其神性光環,也隱約透露出革命對愛情的抑制。芳林嫂被捕,游擊隊員們想方設法營救,最后,他們的愛情終于歷經磨難修成正果。其他游擊隊員們包括政委李正的情感生活則處于“空白”“不在場”狀態。令人深思的是政委李正的現實和生活原型杜季偉正是因與附敵妹妹發生情感糾葛而和革命隊伍發生了矛盾分裂,這種文本外在歷史的復雜含混性在革命文學表現中自然是被過濾和篩選掉的。
《辛俊地》的愛情言說意外地沒有遵循當時文藝創作的“潛規則”。英雄辛俊地的愛情故事無關革命、階級、政治等宏大話語。小說的愛情敘事具有“三角關系”的模式。辛俊地和地主的女兒桂香發生愛情,同時不拘小節和偽軍妻子張二嫂打情罵俏,這種較為復雜的愛情敘事在十七年多少讓人詫異其“越軌”,也難怪被批判為“毒草”。
與劉洪與芳林嫂的愛情故事相比,辛俊地和桂香的愛情故事包含了更復雜的內涵。作為地主的女兒,作家從女性深刻的生命體驗角度細膩傳達出動蕩年代里具有特殊身份的大齡“剩女”痛苦、苦悶、空虛、恐懼等復雜隱秘心理。歲月無情,紅顏易逝,這個將近三十歲的老姑娘對愛情的渴望可想而知。而父母對婚姻的挑剔和“門當戶對”的講究使她的青春逐漸成為明日黃花。為了抓住青春的尾巴,體驗愛情的甜蜜,她瞞著父母大膽愛上曾是她家年輕長工的辛俊地。盡管她知道這會遭到父母的反對而不會有美滿結局,還是義無反顧地傾心于他,既痛苦又甜蜜。讓她心碎欲裂的是:在愛情與親情的兩難選擇面前,她為救父母卻不料成為父親的幫兇,將辛俊地推入死亡的深淵,他們的愛情只能以悲劇和殘破收場。小說結尾,這個地主的女兒只有抱著辛俊地冰冷的身體絕望痛哭,凄厲而無助。這既是英雄辛俊地的悲劇,也是動蕩年代有著特殊身份的女性的悲劇。
小說中另一女性人物張二嫂對英俊、年輕的辛俊地有著復雜隱秘的愛情心理。因對不務正業的偽軍丈夫極度失望,她轉而將情感寄托在辛俊地身上。她的理想就是:“她想要找到一個伴侶,一個熱愛她的人。他們共同的勞動、生活,正經的過一番日子。她后半輩子也有個依靠。她選擇了辛俊地。”敵人進村時,她敢于把辛俊地藏起來情愿自己挨打。辛俊地死后,張二嫂的理想破滅,“每逢想起這英俊勇敢的小伙子,不知暗暗地流了多少眼淚”。作家在塑造這個女性形象時同樣摒棄了階級、政治視角,而從鄉村民間立場看待一個鄉村少婦對無責任感丈夫心灰意冷后的情感渴望。這種復雜的感情關系與《鐵道游擊隊》中的愛情言說相比,不再那么單一、明朗、純凈,而是顯得斑駁蕪雜,更具凡俗性質和鄉間原始色彩,也給讀者留下了更多空白和思考。
三、敘事結構:緊張跌宕與舒緩平和
《鐵道游擊隊》屬于十七年時期革命歷史題材文學的“革命英雄傳奇”類別,具有傳統傳奇文學的特征即奇特與夸飾,“施之澡繪,擴其波瀾”。傳統的傳奇文學興起于盛唐,是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至明清時代,這類小說發展到高峰,呈現蔚為大觀的景象,《水滸傳》《三國演義》《說岳全傳》和《三俠五義》等是其代表。
十七年革命作家們多數從小接觸這類小說并受這種傳奇文化潛移默化的熏陶和影響。知俠曾談到在創作《鐵道游擊隊》時曾認真剖析研究《水滸傳》的結構特點。從其敘事結構看,它的故事情節環環相扣,險象環生,英勇的游擊隊員們神出鬼沒,屢建奇功。打票車、襲洋行、扒鐵軌、炸橋梁、打岡村等一系列傳奇行動顯示出他們的機智驍勇和英勇無畏。在打票車小故事中,足智多謀的游擊隊員們精心策劃,巧妙布置,讓魯漢、林忠等隊友打扮成商人模樣,上了車后與押車日軍小隊長故意打得火熱,又是喝酒吃肉。同時,彭亮和劉洪乘機占據車頭,控制火車,強行通過王溝車站,把火車開到事先設置埋伏的三孔橋跟前,埋伏在車廂里的游擊隊員們出其不意,一舉殲滅了守車日軍,繳獲大量物資和槍支,整場戰斗干凈利索,有驚無險。這類緊張曲折、跌宕多姿的敘事結構讓讀者和小說里的英雄人物共同經歷了“戰爭歷險”,滿足了讀者的閱讀審美期待。
當然,在游擊隊員們節節勝利時,偶爾也有“受挫”“受阻”的時刻,如游擊隊員們在和狡猾敵人周旋的過程中,曾被追得無處藏身,被迫棲身在寒冷冬夜的田野雪地里。但這種傳奇行動的“倒退”現象只是暫時的,是最終勝利洪流中的小插曲,使得文本故事有了離奇多變、跌宕多次的效果。
和《鐵道游擊隊》的敘事結構不同,《辛俊地》的敘事結構舒緩平和,文本營構的畫面更多是鄉村間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人與事,正如鄉間緩緩的溪流,其寫法帶有自然主義傾向。它也有戰斗場面的刻畫,但不像《鐵道游擊隊》那類作品那樣緊張曲折、跌宕多姿。抗日故事只是鄉村日常生活中的一個部分,而非全部。整部作品將鄉村詩意盎然的自然景觀、鄉間復雜多變的三角情感關系、鄉村倫理關系與抗日故事復雜交織在一起,組成一幅戰爭年代的鄉村奇異畫面。正如管樺所言:“我的職業是把我在生活中認識過的各種各樣的人物,帶到讀者面前,介紹給讀者……講述他們平凡而又帶點傳奇色彩的生活和戰斗,講述他們的愛情,他們的悲苦和歡樂,他們的幸運和不幸。”[4]
在《辛俊地》建構的文本世界,旖旎多姿的田園風光在動蕩的戰爭年代顯得同樣詩意盎然、生機勃發。它們在作家平靜舒緩的敘述中充滿牧歌情調,具有強烈的審美性質。這里有“可愛的藍天”“平靜的水面”光滑如油的“水中玉蘭花的葉子”和“貼著水面低飛的黑絨般的細腰水蜻蜓”,有戲水的鴨子,遠方的樹林,金黃的麥田,歌唱的黃鶯,高聲呼喚的布谷鳥,種種鄉間田園的風物意象顯出自然的蓬勃自在和萬物應時而動的生命節律。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主流話語規訓的一種偏離。
與寧靜平和的鄉間田園牧歌情調相映照的是世俗鄉村世界的人情味和樸素性,體現出較少的鄉村倫理敘事。辛俊地稱張二嫂當偽軍的丈夫為“二哥”,并和她開玩笑說:“怎么,要我把二哥找回來嗎?”“打個埋伏,給你活捉回來!”他還稱呼地主徐懷冰為“大叔”,麥收時,主動幫徐懷冰家拔麥子。而徐懷冰這個地主形象膽小怕事,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地在動蕩年代的夾縫中求生存。他破口大罵日本人為“狗日的”“敵人”,最后,出于懼怕日本人報復自己全家的本能心理,他開槍打死了辛俊地。這是一個在亂世縫隙中自私懦弱只為自己討生存的“小人物”形象,也是一個復雜的地主形象。
四、結語
從以上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語境中,同樣是講述特定時代的歷史卻有不同的敘事選擇,體現出不同作家的寫作姿態和文學立場。《鐵道游擊隊》是一種向主流意識形態和革命政治話語靠攏臣服的姿態,呈現出政治道德性質的理想主義傾向,因而被大力弘揚廣泛傳播。《辛俊地》則是一種與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革命話語抗拒疏離的姿態,更具自然主義色彩,也包含了更豐富復雜的內涵和闡釋空間,它展示了作為知識分子身份的創作主體的人性思考、主體意識和精神立場,雖遭遇被批判的命運,但它具有了類似后來“新歷史小說”的“萌芽”。
注釋:
[1]知俠:《鐵道游擊隊》,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2]管樺:《辛俊地·管樺中短篇小說集》,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3]余宗岱:《被規訓的激情》,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72-73頁。
[4]管樺:《管樺中短篇小說集·后記》,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508頁。
(李彥鳳 貴州興義 黔西南民族職業技術學院 56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