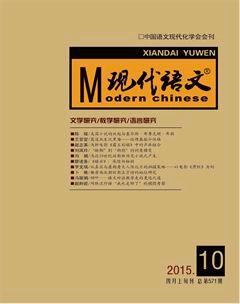從凈化到快感
摘 要:本文通過探討亞里士多德的文學理論名著《詩學》中提出的對于西方文學至關重要的悲劇觀念,試圖厘清作為西方文學源頭的悲劇這一文學樣式的主要功能及其價值,從而發現在這些功能與價值背后所隱含的對于西方文化核心觀念的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詩學 悲劇 凈化 快感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里是這樣定義悲劇的:“悲劇是對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模仿,它的媒介是經過裝飾的語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別被用于劇的不同部分,它的模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動,而不是敘述,通過引發憐憫和恐懼使這些情感得到凈化”。[1]
最后的“通過引發憐憫和恐懼使這些情感得到凈化”明確地指出了悲劇所能引發的人類的特殊情感以及這種情感對人類自身所產生的作用。它們涉及的是悲劇的效果和作用的問題,這是文學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問題,它直接關系到文學自身的聲譽。悲劇究竟能產生怎樣震撼人心的效果,它又是怎樣產生的?
一、悲劇的效果
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要引起觀眾的憐憫、恐懼、驚異等感情,他說“悲劇情節所模仿的應是能引發恐懼和憐憫的事件”,悲劇應包容使人驚異的內容,悲劇的情節必須能使觀看者感受到恐懼和憐憫、驚異等悲劇特有的感情,這是悲劇的特征之一,也是悲劇最基本的任務。
悲劇模仿的不僅是一個完整的行動,而且是能引發恐懼和憐憫的事件,此類事件若是發生得出人意料但仍能表明因果關系,那就最能取得上述效果,如此發生的事件比自然或偶爾發生的事件更能使人驚異,因為即便是出于意外之事,只要看起來是受動機驅使的,亦能激起強烈的驚異之情。
要想獲得悲劇的效果,那么悲劇的情節就必須要出人意料,但又要在情理之中,能體現出因果的邏輯關系,這是情節必須滿足的兩個基本條件,因為這樣的事件比自然或偶爾發生的事件更能產生悲劇的效果,自然或偶爾發生的事件屬于歷史事件,而文學的情節決不是對歷史事件的簡單模仿,文學的真實高于歷史的真實,文學的普遍性高于歷史的特殊性。
關于應該怎樣安排情節才能使作品具有最佳的悲劇效果,即關于悲劇情節的創作技巧,他總結出以下幾點:
1.悲劇不應表現好人由順達之境轉入敗逆之境,因為這既不能引發恐懼,也不能引發憐憫,倒會使人產生反感。
2.不應表現壞人由敗逆之境轉入順達之境,因為這與悲劇精神背道而馳,在哪一點上都不符合悲劇的要求,既不能引起同情也不能引發憐憫或恐懼。
3.不應表現極惡的人由順達之境轉入敗逆之境,此種安排可能會引起同情,卻不能引發憐憫或恐懼,因為憐憫的對象是遭受了不該遭受之不幸的人,而恐懼的產生是因為遭受不幸者是和我們一樣的人,所以此種構合不會引發憐憫或恐懼”。
以上提出的是三種不能引發悲劇效果的情節,好人由順達之境轉入敗逆之境不能產生悲劇效果,反而會使人產生反感;壞人由敗逆之境轉入順達之境更是與悲劇精神背道而馳,是最壞的情節;極惡的人由順達之境轉入敗逆之境也不能產生悲劇效果,盡管這種情節能引起同情。在這里,亞里士多德強調了同情和恐懼憐憫是不同的,他細致地區分了二者的不同之處。
悲劇情節所引發恐懼與憐憫的情感效果是特有的,恐懼由劇中人物遭遇苦難逆境而引起,憐憫是對劇中人物遭受不應當遭受厄運的一種同情。在《修辭學》中,亞里士多德定義恐懼是一種對降臨的災禍因意想到它會導致毀滅或苦難而引起的痛苦不安的情緒,人們聽到比自己更好或自己相似的人受到禍害,推人及己,想到自己也可能受害,就會有恐懼心態。他定義憐憫是“因看到不應受害者身上落有毀滅性或痛苦的災禍,覺得自己或親友也有可能遭受相似災禍,就會引起憐憫這種痛苦情感”。而極惡的人由順達之境轉入敗逆之境這種情節引起的只是同情,而并不是悲劇所特有的那種恐懼和憐憫,因而也便不能產生凈化的作用,更不能使欣賞者得到悲劇的快感。
他說“如果是仇敵對仇敵,那么除了人物所受的折磨外,無論是所做的事情,還是打算做出這種事情的企圖,都不能引發憐憫,最糟的是在知情的情況下企圖做出這種事情而又沒做,如此處理令人厭惡,且不會產生悲劇的效果,因為它不表現人物的痛苦”。
這些具體例子都是不能產生悲劇效果的情節,那么他認為哪些情節或手段是能引起悲劇感情的呢?他說“突轉和發現能引發憐憫或恐懼,在所有的發現中,最好的應出自事件本身,這種發現能使人吃驚,在處理突轉和簡單事件方面,他們力圖引發他們想要引發的驚異感,因為這么做能收到悲劇的效果,并能爭得對人物的同情,寫一個聰明的惡棍被捉弄,或一個勇敢但不公正的人被擊敗,便可能產生這種效果”。
突轉和發現,是達成悲劇效果的手段,因為這兩種情節的處理方式具有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效果,恐懼和憐憫這兩種情感應出自悲劇中突轉和發現的情節,它是有著特殊審美意義的悲劇效果,人們能從中獲得悲劇所特有的快感。
他說“恐懼和憐憫可以出自戲景,亦可出自情節本身的構合,后一種方式比較好,組織情節要注重技巧,使人即使不看演出而僅聽敘述,也會對事情的結局感到悚然和產生憐憫之情,這些便是在聽人講述《俄底甫斯》的情節時可能會體會到的感受,靠借助戲景來產生此種效果的做法,既缺少藝術性,且會造成糜費。那些用戲景展示僅是怪誕而不是可怕的情景的詩人只能是悲劇的門外漢。”
情節比戲景更能引發悲劇效果,通過戲景達到的效果只是怪誕而不是真正的悲劇精神,戲景只是悲劇中的輔助手段,悲劇的效果主要依靠情節的巧妙布置。
二、卡塔西斯
在悲劇的定義里,他提出了著名的卡塔西斯說,但對此論述極為簡略,卡塔西斯是希臘文“凈化”的音譯,凈化本是古希臘奧菲斯教的術語,指依附肉體的靈魂帶著前世的原罪來到現世,采用清水凈身,戒欲祛邪等教儀,這樣便可使靈魂得到凈化。恩培多克勒秉承此義寫過宗教哲理詩《凈化篇》,這是在宗教的意義上對其的使用,而希波克拉底學派在其醫學著作中,把這個詞又轉用為醫學術語,指宣泄,即借自然力或藥力將有害之物排出體外。后來,亞里士多德又在《詩學》中借用卡塔西斯一詞,用它來論述文學中悲劇產生的效果。
目前學術界對“凈化”有兩種看法,第一派主張悲劇的功用是道德凈化,第二派主張悲劇的功用是宣泄情感,達到心緒平和心理健康。卡塔西斯的義素中包含有凈化、純化、澄清的意思。凈化、純化的意義是強調觀眾的心理過程,凈化指驅除不需要的情感(憐憫和恐懼),這是基于醫療的模式;而純化則假定這些情感未被驅除,而受到減弱或抑制,這是基于道德完善的思想;而澄清的意義則是針對劇中發生的凈化。
在《政治學》中他為了闡述音樂的目的也提及了卡塔西斯,意即音樂也能使人得到感情的凈化。他談及音樂能使人感受真實的愉悅,培育良好的藝術鑒賞力,而在藝術鑒賞中的凈化,是一種諧和情感的心理治療。亞里士多德舉例說:“一些人沉溺于宗教狂熱,當他們聽到神圣莊嚴的旋律,靈魂感發神秘的激動,我們看到了圣樂的那種使靈魂恢復正常的效果,仿佛他們的靈魂得到治愈和凈洗。那些受憐憫恐懼及各種情性影響的人,必定有相似經驗,而其他每個易受這些情感影響的人,都會以一種被凈洗的樣式,使他們的靈魂得到澄明和愉悅。這種凈化的旋律同樣給人類一種清純的快樂,凈化能導致快樂。”
三、快感的來源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里,多次使用了快感這一詞,亞里士多德的快感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實際上他的快感并不僅僅指普通意義上快樂的感覺,他的快感所包孕的內容更豐富,是一種悲劇所獨有的,能給人帶來獨特享受的復雜情感。
在論述文藝的起源時,他提到了快感:“詩藝的產生有兩個原因都與人的天性有關。1從孩提起人就有模仿的本能,通過模仿獲得最初的知識。2每個人都能從模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因為求知不僅于哲學家,而且對一般人來說都是一件最快樂的事,人們樂于觀看藝術形象,因為通過對作品的觀察,他們可以學到東西,倘若觀賞者從未見過作品的原型,他就不會從作為模仿品的形象中獲得快感。在此種情況下能引發快感的便是作品的技術處理、色彩或諸如此類的原因”。
快感的來源很多,通過模仿獲得知識能給人帶來快感,作為模仿品的形象能給人帶來快感,作品的技術處理、色彩等也都能給人以快感。
他說“一幅黑白素描比各種最好看的顏料的胡亂堆砌更能使人產生快感”。
“即便是有名的事件,熟悉它們的也只是少數人,但盡管如此,它們仍然能給大家帶來愉悅”。
“能引起驚異的事會給人快感”。
“詩人應通過模仿使人產生憐憫和恐懼并從體驗這些情感中得到快感”。
“滑稽的事物,或包含謬誤,或其貌不揚,但不會給人造成痛苦或帶來傷害,現成的例子是喜劇演員的面具,它雖然既丑又怪,卻不會讓人看了感到痛苦”。
合理的安排而非胡亂的堆砌有時甚至比材料本身的性質更能導致快感的產生,著名的事件也是快感的來源,而滑稽的事物卻并不能給人類的心靈帶來什么影響,至多是一種怪誕,卻不能感染人,不能帶來恐懼和憐憫這種悲劇所獨有的快感。
音樂也能給人帶來快感,而且它還是構成悲劇效果的重要因素,他說:“悲劇有一個分量不輕的成分,即音樂,通過它悲劇能以極其生動的方式提供快感,無論是通過閱讀還是通過觀看演出,悲劇都能給人留下鮮明的印象,集中的表現比費時的沖淡了的表現更能給人快感。”
早期的悲劇中歌隊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恰當的歌唱和音樂效果必然能更好地體現悲劇所要表現的情感,使觀賞者更深切地體會到悲劇的精神,得到凈化,獲得快感。
四、快感的種類
亞里士多德不僅強調了快感的重要性,而且還區分了快感的種類,在他那里快感并不是一種單一的簡單的感情,它包含著不同的種類,其中有著細微的差別。
他在《詩學》里說“我們應通過悲劇尋求那種應該由它引發的而不是各種各樣的快感,有的詩人被觀眾的喜惡所左右,為迎合后者的意愿而寫作,但是這不是悲劇所提供的快感,此種快感更象是喜劇式的。悲劇比史詩更好的取得此種藝術的功效,它們提供的不應是處于偶然的,而應是上文提及的那種快感”。
上述引文中他談到了各種各樣的快感,有喜劇式的,悲劇式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對文藝作品能給人帶來的不同感受是有著細致的區分的。快感有著不同的種類,悲劇提供的不應是處于偶然的那種快感,那不是真正的悲劇的快感。
綜上所述,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清理出這樣的一條線索,它在邏輯上有著這樣的脈絡,即憐憫、恐懼、驚異(效果)——凈化(手段)——快感(目的)——悲劇精神。即悲劇首先能引發起觀眾憐憫、恐懼和驚異的感情,然后通過凈化使得這種感情達到疏導宣泄、陶冶和升華,最后觀看者獲得了悲劇的快感,而這種快感不是普通的平凡的,而是悲劇所特有的,而這也就是真正的悲劇精神所在,是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快樂與痛苦的感受,是真正體現悲劇精神的快感。
注釋:
[1]以上引文均出自陳中梅譯,[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著:《詩學》,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
(趙莉莎 大連外國語學院文化傳播學院 116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