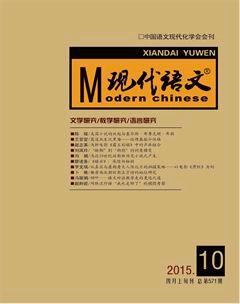《長安古意》之我見
《長安古意》被定義為宮體詩,而卻又是宮體詩的超越,被稱為“墮落宮體詩盡頭的最后轉機”[1]。因為相對于陳、梁著意于追求感官聲色的享受和淫靡放蕩的生活,以及唐初詩壇以上官儀等為代表的宮廷詩人粉飾太平的迎合之作,盧照鄰的《長安古意》顯然超過了這些詩的價值,這是它歷來被贊美和肯定的原因。在今天,很多人對該作品進行鑒賞及分析,其中也產生了分歧,筆者也將就幾個焦點問題進行討論。
一、內容描寫:盧照鄰筆下的豪華生活
全詩分為四個部分,其中三個部分都是寫上層社會豪華奢靡的生活狀態:
長安大道連狹抖, 青牛白馬七香車。
玉葷縱橫過主第, 金鞭絡繹向侯家。
龍街寶蓋承朝日, 鳳吐流蘇帶晚霞。
百尺游絲爭繞樹, 一群嬌鳥共啼花。
啼花戲蝶千門側, 碧樹銀臺萬種色。
復道交窗作合歡, 雙闕連甍垂風冀。
梁家畫閣中天起, 漢帝金莖云外直。
樓前相望不相知, 陌上相逢詎相識?
借問吹簫向紫煙, 曾經學舞度芳年。
得成比目何辭死, 愿作鴛鴦不羨仙。
比目鴛鴦真可羨, 雙去雙來君不見?
生憎帳額繡孤鸞, 好取門簾帖雙燕。
雙燕雙飛繞畫梁, 羅幃翠被郁金香。
片片行云著蟬鬢, 纖纖初月上鴉黃。
鴉黃粉白車中出, 含嬌含態情非一。
妖童寶馬鐵連錢, 娼婦蟠龍金屈膝。
壯麗寬闊的皇城大道、華美考究的香車在權貴宅邸中穿梭,絡繹不絕。各種琳瑯滿目的飾物,一派鶯歌蝶舞,整個長安的上層生活可謂窮盡奢華。再將目光轉向隨從貴族出游的歌兒舞女們,生活也隨之奢靡。嬌鳥啼花,姿態萬千,建筑是修得富麗堂皇,高樓亭臺交錯。
“曾經學舞度芳年”這不禁讓我們想起白居易《琵琶行》里面的“老大嫁作商人婦”的琵琶女。我們也能想象在歌舞教坊里面,“五陵少年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的景象,貴族公子尋歡作樂,留戀情色。或許他們當中,也有人曾經有美好的誓言“得成比目何辭死,愿作鴛鴦不羨仙”,也向往有“吹簫向紫煙”里面秦穆公女兒弄月隨丈夫比翼雙飛成仙的美好愛情。可是“比目鴛鴦真可羨,雙飛雙去君不見。”這不過是煙花之地的逢場作戲罷了,最后背棄誓言,富家公子另覓新歡是常有之事。或許這些女子當時會有一時的癡情,有一時的傷心難過。可是長期沉溺于酒色之中,煙花女子也似乎看透了這些,繼續“片片行云著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精心打扮,出沒在各種香車豪府之間,繼續過著糜爛放縱的生活。
第二部分,詩人著力描寫“游俠”這股黑暗勢力:
御史府中烏夜啼, 廷尉門前雀欲棲。
隱隱朱城臨玉道, 遙遙翠憲沒金提。
挾彈飛鷹杜陵北, 探丸借客渭橋西。
俱邀俠客芙蓉劍, 共宿娼家桃李蹊。
娼家日暮紫羅裙, 清歌一囀口氛氳。
北堂夜夜人如月, 南陌朝朝騎似云。
南陌北堂連北里, 五劇三條控三市。
弱柳青槐拂地垂, 佳氣紅塵暗天起。
漢代金吾千騎來, 翡翠屠蘇鸚鵡杯。
羅襦寶帶為君解, 燕歌趙舞為君開。
由長安大道的繁華轉向街頭巷里的娼家,夜夜歌舞笙簫,紙醉金迷。而俠客猖狂,肆意為非作歹,和金吾沆瀣一氣組成了一股黑暗勢力。相對比的是“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雀欲棲”,掌管彈劾的御史和司法官廷尉門可羅雀。可想城中權貴,惡少橫行,御史和廷尉完全沒有實權,這樣的社會風氣腐敗難行,底層人民的日子可想而知。
第三部分,上層統治階級以及文武官員之間為自身利益相互傾軋的黑暗內幕:
別有豪華稱將相, 轉日回天不相讓。
意氣由來排灌夫, 專權判不容蕭相。
專權意氣本豪雄, 青虬紫燕坐春風。
自言歌舞長千載, 自謂驕奢凌五公。
節物風光不相待, 桑田碧海須臾改。
昔時金階白玉堂, 即今惟見青松在。
朝廷官員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爭斗,不擇手段。官場如此,下層人民的生活又會是什么樣的?而腐朽的政治統治能持續多久?正所謂“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日的繁華轉瞬滄桑,再多奢華昳麗,驕橫得意,夜夜笙歌,都如煙花消散得迅速,不著痕跡。而正是因為上層階級糜爛的生活,黑暗的內部斗爭,腐朽的統治,這根基薄弱,禁不起時間的撼動,走向衰亡是常理。
二、情感表達:盧照鄰對所寫豪華生活的態度
(一)閣樓上的女子為何人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樓上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拒相識”。樓閣上的女子是什么人?王明好教授理解為貴婦,“高樓鳳閣中、錦衣繡戶里生活的貴族女子”[2]。而筆者對此有不同的看法。我們必須正確理解這里的正確代指,因為這關系到能否正確理解盧照鄰寫詩的真正意圖和對豪華生活的態度。根據上下文理解,在“高樓”憑欄倚靠的女子一般有兩種女人,一種是如《古詩十九首·西北有高樓》的貴婦,在高樓彈琴尋覓知音,追求的是一種精神上的寄托。而另一種女人便是《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里面“昔為娼家女,今為蕩子婦”的妓女,她因為“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而想要追求一種情愛享受。聯系《長安古意》的內容大意,以及后面“曾經學舞度芳年”可以知道,這里應該是指妓女,而不是貴族女子。所以前面第一部分繁華秾麗的景物描寫也不是為了突出貴族女子的孤獨,而是作者為了最后的批判做足鋪墊。
(二)盧照鄰是否向往豪俠
自古以來,人們都崇拜豪俠,敬仰那些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劫富濟貧的英雄豪杰。古典小說里經常有這樣英雄人物的塑造,很多詩歌里也有歌頌這樣的英雄豪杰。那么盧照鄰是否也一樣崇尚豪俠呢?
王明好教授認為“盧照鄰本有豪俠情結,朝廷權臣,豪縱俠客,哪一個角色不是詩人所向往,所心儀?”[3]而問題是盧照鄰是否真的向往豪俠?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要搞清楚這里的豪俠所指的是怎樣的人。他們“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這些豪俠和“金吾”禁衛軍勾結在一起,謀殺官吏,害人性命,無視法律,尋歡作樂,夜宿娼家。他們是一股黑暗勢力,或許也是上層階級相互斗爭、相互傾軋的工具。連御史和廷尉都沒有實際作用,權貴就成了真正權力的象征,整個社會的風氣可想而知。人人爭相巴結權貴,而權貴一手遮天,更加加重對底層人民的壓榨和壓迫。豪俠就成了這些權貴的打手,那么盧照鄰會向往這樣的豪俠嗎?
(三)盧照鄰的真實意圖和態度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盧照鄰其實是通過長篇幅的豪華場面的描寫以及上層階級的縱欲享受,以四句“節侯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 即今惟見青松在。”冷靜客觀地揭示了當時社會上的腐朽奢靡之風,和對這種生活方式以及態度的批判。同時也揭示統治階級最終不可避免沒落和衰敗的結局。
所以,就不是王明好教授所認為的,盧照鄰是想“要投入繁華的洪流中去,去成就一番偉業”[4]。詩歌前面的描寫,也不是詩人因為國家的繁榮發展而有的“澎湃的激情,沸騰的熱血”[5],或者詩人有一顆和“時代脈搏共同跳動的心”。或許曾想過要在國家蒸蒸日上的大環境下,憑著一身才氣去建功立業,最后能功成名就。或許他也曾經體驗過或者目睹過上層社會的生活,否則可能寫不出如此形象細致的場面。誠然,他在入鄧王府作典簽的時候,確實也受鄧王器重過,而且被謂之“相如”。可是最后晚景凄涼,因不堪病痛,跳穎水自殺了。而正是因為他早前體驗過上層階級的生活,他才看清了統治階級的面目,最終下了決心要像揚雄一樣,不羨慕富貴,專心治學。所以也寫下了最后一部分:
寂寂寥寥揚子居, 年年歲歲一床書。
獨有南山桂花發, 飛來飛去襲人裾。
最后一部分雖然短,但是卻達到了極高的思想高度。盧照鄰以楊雄自喻,用冷峻的眼光審視著污濁的周遭,表達對上層社會的蔑視和奢靡之風的不滿,更是對黑暗統治的諷刺。正因為短短四句,使得這諷刺更加冰涼刺骨,直抵人心。
三、詩歌結構:最后一部分是否為“一點點藝術的失敗”[6]
就整首詩的結構而言,結構似乎已經完整了,因為“節侯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 即今惟見青松在。”這四句似乎已經達到了升華主題,表達了詩人的態度和觀點,已經算是“畫龍點睛”了。那最后一部分是不是“畫蛇添足”了呢?
筆者認為最后一部分的四句恰恰是最巧妙的地方。
首先,最后四句帶出了抒情主人公。回顧整首詩歌,前面所敘述的視角沒有抒情主人公,那么就像散落的花瓣,無法形成一朵絢爛的花。隨著最后抒情主人公的代入,奠定了詩歌的感情基調,豐富了詩歌的情感,使整首詩歌更加完整和飽滿。
其次,最后四句給讀者營造了淡雅而悠長的意境。我們要弄清楚詩人把桂花寫進詩中是何目的,就首先要清楚桂花這一意象所代表的涵義。桂花最開始是出自吳剛砍桂樹這個故事。傳說月中有桂樹,高五百丈。漢朝河西人吳剛,因學仙時,不遵道規,被罰至月中伐桂,但此樹隨砍隨合,總不能伐倒。千萬年過去了,吳剛總是每日辛勤伐樹不止,而那棵神奇的桂樹卻依然如故,生機勃勃,每臨中秋,馨香四溢。只有中秋這一天,吳剛才在樹下稍事休息,與人間共度團圓佳節。而后,許多文人墨客也歌頌桂花,桂花就代表著芳潔這一高尚的品質。而且作者一生官卑位低,也可能繼承香草美人傳統,借用桂花,抒發芳香無人賞,自己的才華得不到施展的情感。
全詩以桂花這個美好的意象結尾,留給讀者一種清新又沁人心脾的桂花香的意境。簡簡單單的四句凄清寂靜與之前長篇幅的眼花繚亂的豪華場景對比,讓人回味無窮又發人深省。
四、小結
《長安古意》為浮艷的宮體詩敲下了一記重音。詩人盧照鄰在宮體詩中諷刺現實社會,在宮體詩中注入自己強烈的感情,是對宮體詩的超越。同時,也是“初唐四杰”對詩歌改革的具體實踐。盧照鄰推動了宮體詩發展的浪潮,并使之最后到達了《春江花月夜》的頂峰,《長安古意》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就詩歌本身而言,結構的完整,情感的強烈,思想的深刻,可以說該詩是不應該遭到詬病的。而隨著時間和歷史的見證,《長安古意》必將會繼續流傳下去。
注釋:
[1][6]聞一多:《宮體詩的自贖》,《唐詩雜論詩與批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
[2][3][4][5]王明好:《一場視覺的盛宴——<長安古意的鑒賞>》,電影評介,2010年,第9期,第99-100頁。
參考文獻:
[1]林家英.顛狂中有戰慄——淺談《長安古意》的批判精神[J].名家欣賞,1982,(4).
[2]郭預衡.中國古代文學史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郭預衡.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二[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卿燕 四川師范大學 61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