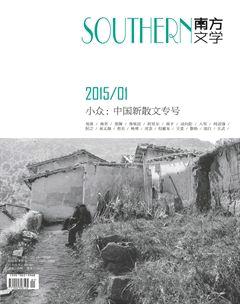他志(三篇)
龐白
黑皮大哥
他的皮膚是那種不能僅用黑來形容的黑,他的皮膚黑得深淺不一,黑得沒有規矩。打個比方,如果他掉進了煤灰里,找他的人肯定一眼就能找到。他會比煤灰黑,黑得發亮和粗糙。他的膚色黑,實在找不出一點遺傳的理論依據。我和他是同學,見過他的父母和妹妹。他的父母和妹妹,膚色都很正常,甚至比普通人還白一點。尤其是他母親,現在已是六十大幾的人了,依然腰板挺直,風韻猶存。他的母親不僅是他和他妹妹的母親,還是另一個女孩子的母親。他的母親在我們畢業前,改嫁給了后來我們服務的公司的一個干部,并生下一個女孩。那個女孩長大后也成了我們的同事,我們都叫她細妹。
我們校長是海軍潛艇退役艇長,他認為甚高甚大甚黑的他,畢業后要解決個人問題會是個大問題。所以在某個月黑風高的晚上,校長拉了我們幾個班委去散步。他讓我們去和衛校、師范學校搞活動時,關照關照,多帶他去。我們每次都帶他去,只是我們這老兄,嘴倒是不笨,但是講的全是街道、江湖上的話,我們都聽得別扭,人家女孩子就更不愿意聽了。要命的是他不但黑,那雙手,也粗糙得跟樹皮差不多。每每伸手要幫人家忙,人家的手一般都會嚇得猛地趕快縮回去,從來沒有過握住人家嬌嫩雙手的記錄。后來快到要畢業了,他老兄不算急,我們想想卻覺得不對頭。大家同學一場,平時沒少在他們家吃,真擔心他老兄下船后,要打一輩子光棍。如果是那樣,大家臉上都不好看。商量了一晚,決定由鋼筆字已頗有架勢的高佬記錄,大家口述,當晚炮制七封情書,分七天,寄給老江的一個筆友。那年頭,時興交筆友,喜歡畫畫的老江的筆友不太遠,是一個鄉鎮的小學語文老師。老江和筆友交往了一年多,雖然沒任何進展,但現在要貢獻出來,還是心如刀割。所以兄弟們都佩服老江高風亮節,阿高還為此去樓下買了燒酒回來,大家一邊口述,一邊喝,弄了一晚,天亮后,寄了第一封出去,大家才各自睡覺,白天的課不上了,全體曠課。老江的筆友收到七封文采飛揚、胡說八道的情書后,很快就同意在約定的日子與黑黑的他見面了。說來也巧,他們見面那天,竟然風雨交加。我們都以為不成了,天意如此。后來,據他講,他們見了面沒到五分鐘,雨就如傾盆了。他們倆沿著四五里長的老街騎樓,來來回回走了兩趟,事情就成了。至于怎么就成法,我們也懶得問了,成了就好。這對活寶,剛結婚那幾年,為錢,為家事,為賭錢,為跑船十天半個月不回來,隔天就吵架。后來生了一個女孩,又生了一個男孩,慢慢也就懶得吵了。吵架少之后,已辭去小學老師之職的他的老婆就有心情看守他了。他老婆見他打麻將,掃桌子,拉他回家,給他買書,守著他復習考試。考來考去,考了幾年,他今年終于把船長證書考到手了。船長和水手的工資相差五六倍。這樣一來,很多人的老婆就不得不佩服他老婆的長遠眼光了。說他人黑是黑了點,但一個船長黑點有什么關系?船長的臉皮如果白得像個小白臉,反倒不太像話了。
考上了船長的他,干的其實還是大副的活。剛考上船長,不跟班一年半載,誰放心把一艘值一兩千萬的船交給他?而且他這人大大咧咧的,不多歷練,真不行。
他當客船的大副有三年了。當大副這些年,隔天跑海南,在海南呆的時間比在家里呆的還多。有一次,我跟他們船去海南,船上的客人走完后,同船的同學便叫上街走走。三個人剛走到碼頭大門外,同學便把我帶到大門左側的一家擦鞋的小店,說擦了鞋再去喝茶。擦就擦。兩個同學把我壓坐在一張小凳子上,招呼:“大嫂,來,他是老夫,擦擦。”一個三十多歲的海南女人朝他們倆笑笑,一邊擦鞋一邊和站在邊上的他們倆聊天。擦完我的,他們倆的鞋也一一給擦了,臨了同學給了十塊錢一雙。出了門,我問,這里擦鞋這么貴?他們倆樂了,說:“不貴,不貴,她是黑大嫂啊!”原來老黑常在這里擦鞋,擦著擦著,就擦出意思了。老黑于是常常幫襯有四個小孩的她,比如到交學費的時候,擦一雙鞋,給一百兩百的。后來人家那只會喝酒賭錢的老公聽到傳言,不樂意了,跑到船上鬧過兩次,老黑便就不太好意思去店里擦鞋了。他不好意思,兄弟們會做人的啊,就這樣,大嫂便成了大家的大嫂。大嫂是爽快人,兄弟們來擦鞋,一來圖聊得開心,二也有意幫幫她,她感恩,兄弟們到她這擦鞋,碰上沒吃早餐的,她立馬從邊上的早餐店捧一碗回來。
晚上回到船上,我告訴老黑,早上去擦鞋了。
他老兄一臉尷尬,笑相跟哭相差不多,五官都挪動連結到一塊了,只有那牙齒,白亮白亮的,在太陽光下一閃一閃,就像嘴里鑲了很多假瓷牙。
政工人士
1990年盛夏的一個傍晚,他騎在28寸鳳凰牌自行車上,左手握著銹跡斑斑的車把手,右手拿著一個大蘋果,一邊大口地啃一邊費力地踩。車子從當時人跡稀少的北部灣中路飛馳而過,沖到了四川路口,猛然將車把手往右一扭轉向四川南路,沒一分鐘的工夫就消失在夜色中了。
20余年過去,我一直無法將他的這個形象從腦海里抹去。
他平時的模樣、舉止和言談,偏枯寂,甚至迂腐,飆車這種小年輕的行徑很難和他扯到一起。但是他就飆了,確實飆了。
他上世紀50年代,生于一個叫西牛腳村的貧下中農家庭,高中畢業。這個學歷,在他們那個年代,尤其是他們那條村子里,算得上是高級知識分子了。遺憾的是作為高級知識分子的他,生不逢時,高中畢業后,已沒大學可考。那時大家都忙著去游街、批斗、鬧革命,他也只好回到村子里扛把鋤頭跟老父親去插秧、割禾、看牛和砍柴了。1973年航運分司招工時,他那任村支書的三叔公把他推薦上去,被招為水手,農轉非,吃上皇糧。當水手,在海上漂泊,跑遍了中國沿海的港口,一晃十幾年過去,四十出頭的他,腰彎了,手更粗了,風濕病也染上了。后獲單位一個鄉親領導的青睞,調上岸,坐入辦公室,先到政工股抄抄寫寫,春節張羅職工慰問,夏日組織送清補涼,同事婚嫁幫忙收收彩禮,有人死了代表組織寫悼詞。隨著鄉親領導職務的晉升,時至上世紀90年代,他也升任了辦公室主任。當了官的他,不抽煙,但不反對抽煙;喜歡喝茶,貴賤一視同仁,衣著陳舊,頗受非議,有人認為他破壞了單位黨政領導形象,他卻我行我素,“踐行艱苦樸素作風”:胸前背后常打補丁,頗似 “袈裟”,日復一日,聞名遠近,終成公司一景。兄弟單位有人來找他聯系工作,忘記其名字,沒事,“我要找樸素主任”,就可以找到。
衣著雖不在意,坐姿卻絕對屬于正襟危坐,言出頗有偉人遺風。特別是調解家庭問題,碰上有人要離婚,不管是一起生活沒幾年的小兩口還是打了一輩子生死架的老夫老妻,必定先跟人家講政策、倫理、道德,講家不平何以平天下。為讓他快點蓋章開證明去民政局辦手續,雖然心里對平天下沒什么興趣,但一般會強忍著憤怒聽他滔滔不絕。碰到脾氣不好,心情也不好的,人家會拖出一把殺豬刀,按到他脖子上:“口水多過茶,蓋不蓋?!”
他的性格,說好聽是耿直,說不好聽是固執、死腦筋。不管是對上司還是下級,他是一定要堅持己見的,好像天生以說服別人為己任。如果別人拂袖而去,他會緊追不舍,或者在人家背影漸遠中大聲宣布“來日再戰”,得罪人而不自知。單位一個同事,后調房產局任局長的副書記就多次被他這種性格煩不勝煩而生氣至極。后來,他省吃儉用,買了一塊地,準備建房子。被房產局告知,他買的是市政公共用地,屬于亂買,不能建房。他找到局長,即那位前同事,討說法。人家局長一字一句告訴他,自己身為公務人員,不能違法,不能妨礙辦事的人按章辦事。經人點撥,他于是和房產局對簿公堂,官司打了三年,竟然贏了。為打官司,他精研了民法及其他法律,以致官司打到最后,干脆不要律師了,自己上陣。也得益于這場官司,便好學的他頗通民法,退休之后,偶爾有親戚、鄰居請他幫忙寫狀紙、打官司,他欣然前往,聽說雖鮮有勝算,卻樂此不疲。當然,這是后話。還是講他和房產局打官司的事。打贏官司,房產局要賠他一筆錢,這筆錢卻一拖再拖,后來局長成了調研員,又成了退休人士,那筆錢才曲徑通幽地出現在他的賬戶里。那時,距離他打贏官司已過了七年了。七年時間,中國人把抗日戰爭都打完了。
在打官司和追討補償的七年里,他曾從辦主任崗位調到單位培訓中心當語文教員。那時我在那里參加培訓,因為都喜歡看書,沒事便找他“頂嘴”,吵時窩火,吵后卻頗有爽暢之感。當了兩年老師,他又被調回去當主任去了。他人雖固執,卻天性不喜爭權奪利,堅持“原則”,單位班子幾個人各有背景,在“重大事情”上難平衡,但是長期不平衡也不好,不平衡大家都挺累,于是便找他回去給大家當橋板。
2006年7月,好好的公司被打包賣給私人老板,他堅決不與資本家為伍。“我一個堂堂黨員干部,臨退休還要變節?!”在繼續在公司打工還是領補償金走人的道路上,他毫不猶豫選擇了后者。離開公司兩年后,他得以到社保局辦理正式退休手續。辦退休手續時,他病了,是他已退休五年的弟弟到老公司幫他辦的手續,接待的小同事問他弟弟:“××真是你哥哥?你們家弟弟的歲數比哥哥大的?”他弟弟理直氣壯告訴小同事:“那年月,為招工改大改小歲數,有什么奇怪?戶口簿上爺爺和孫子變成兄弟都正常!”
他退休后,消隱于江湖。雖同在一個城市,我卻難聽聞到他的消息。有時聽到有人講他常幫人打官司,有人講他回老家種地,有人講他騎單車游四川,有人講他哪也沒去,天天待在家里研究易經。
老處男
公司有兩個潑辣的女人曾在公開場合罵他是老處男。
那兩個潑辣的女人嚴重影響了我對“老處男”這個評價的判斷,使我至今分不清楚用“老處男”形容男人,到底是表揚還是咒罵。按道理上講,罵別人“老”,形容其年邁、無用,是不好的,但是罵別人是處男,我就有些不懂是褒還是貶了。
進公司,我就認識了老處男。那年他四十一歲,我二十歲。
當時兩千余人的公司,有幾個著名的“處級干部”。所謂“處級干部”,即指男四十以上,女三十五以上,沒有成家和嫁人跡象,甚至沒有處過男、女朋友的公司機關管理人員。其中兩個是男的,兩個是女的,他是最著名的那一個,著名到從來沒有人聽說和傳言過他曾有稍稍接近的女人,著名到公司分房子時,領導們開會討論時都不好意思不把他排在第一順位。領導們都不想擔“某某領導不同意分房給他,所以他找不到老婆”的罪名。
在這家國有企業里,他的處境算是相當不錯的:在人事科做勞資員,人長得不算靚卻稱得上長相端正;單位分有住房,雖然不大,怎么說也是兩室一廳。他性情平和,為人謹慎,談吐斯文中能夾點通俗,做勞資員不喜怒于色的職業習慣雖然成為生活習慣,但下班后和同事吃飯時歡聲淺笑的時候也不少。挺正常的一個男人,憑什么就老處男了呢?
聽同事講,那兩位女同事罵他是老處男時,他低頭順眉,既不辯解,也不生氣,甚至還似乎表現出有些對不起人家的意思。后來我想,為什么那兩位女同事罵得理直氣壯,而他沉默得順理成章,莫不是被那兩位女同事考核過,但是不合格?這事當然不得而知。也或者合格了,但那是天知、地知、他知、她們知的事,旁人無從知曉。反正后來我調到勞資科工作時,他還是老處男。上班的時候,他的電話絕對不是科里最少的一個,聯系工作的,交朋結友的,甚至是閑聊的,都有。他在電話里鮮有生氣的時候,笑聲朗朗之時倒不少。原來我以為他是因為性格怪癖才榮升老處男,共事之后,先入為主的印象完全被覆蓋。他并沒有怪癖。科里大姐龍姨是和他同一年進入公司的,人家都做奶奶了。龍姨善解人意,講話比較委婉。她講他之所以成為老處男,是還沒碰到合適的人,只要碰上了,就不是了。
龍姨真是先知,到了上世紀末,即是報紙上吹噓新舊世紀交會之限,他老處男的身份被破了。經老同學介紹,他和基本同屬于一個年代的一名助產護士相識了,經過兩三個月的接觸,他們決定組成家庭。他決定結婚,在公司范圍內引起了轟動。書記給工會和團委布置任務時說,連他都結婚了,你們工會和團委一定要想方設法而且必須有方法解決公司技術人員老大難問題!他沒有按習慣在酒店置辦結婚禮酒,只是回老家擺了幾桌,請親戚朋友吃頓飯,宣告單身結束。當然,科里這頓是免不了要請的,但不用他花錢,是科長請。多年來,“老處男那個科”的名聲幾乎蓋過了“勞資科”的名頭,如今老處男科室的帽子在他自覺自愿的前提下得以掀掉,不慶賀,實在沒有道理!
破掉處男之身后,他在公司里的顯赫名聲便如王老五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老處男的身份像籠罩在他身上的一層神秘光暈,多年來,使得他在人群里若隱若現。如今光暈褪去,他就是一個普通的、尋常的,走在樓道上可以熟視無睹的人了。他也逐漸得以恢復了身份證上的名字。大家在背后越來越少稱呼他為老處男了,甚至有人恍然大悟,終于知道他原來還有這樣一個名字!
結了婚的他,一到周末,便搭車返離市區三十公里的老婆家去探親。大家都知道他不是要把工資貢獻給汽車總站,而是要把年輕時耽擱的時光搶回來,所以在周末聚餐或者搞什么活動,一般也不預他的份子了。
第二年,他老來得子。好像沒過幾年,他的小孩讀幼兒園了。再后來,他的小孩讀小學了。小孩讀小學那年,他辦理了退休手續。
歡送他退休的那頓飯上,他喝醉了。看著他醉得一塌糊涂的樣子,我不由感慨,時間過得太快。快得好像認識老處男還是昨天的事情,一瞇眼的工夫,二十年就過去了。快得好像一輩子只夠他做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從一個老處男變成一個老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