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 Not Found
404 Not Found
淺談女性都市文本的現(xiàn)代性
楊瑞曉
摘 要:現(xiàn)代性一直以來都是大家爭論的熱點話題,對于現(xiàn)代性的理解各有不同。嚴(yán)家炎和袁進(jìn)對于現(xiàn)代性的描述是:“何謂現(xiàn)代性,就是指傳統(tǒng)社會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代社會過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的知識理念和價值標(biāo)準(zhǔn)。”女性都市文本就體現(xiàn)了這樣的現(xiàn)代性。首先,女性都市文本寫作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現(xiàn)代性,因為它打破了男性話語控制下的城市想象,書寫了城市的另一種面貌,使城市想象更為完整。其次,女性都市文本的寫作方法如用個人感性認(rèn)識代替宏大敘事和身體寫作都是在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過程中由女性所開拓的新的寫作空間,帶有女性色彩和女性個性,因而是具有現(xiàn)代性的。因而我們可以說,女性都市文本從整體寫作到文本內(nèi)部都是具有現(xiàn)代性的。
關(guān)鍵詞:女性;都市文本;現(xiàn)代性;寫作方法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3-0138-02
王光明在《城市與女人》一文中說:“假如沒有城市,不會有女權(quán)主義運動和女性主義寫作,城市與女人,其實在現(xiàn)代社會,歷來就有非常復(fù)雜的關(guān)系,以城市為舞臺的女性文學(xué),不但表現(xiàn)了女性閱讀城市的意識和立場,而且通過女性寫作進(jìn)一步塑造,想象了城市的現(xiàn)狀和個性。”[1]正如王光明所說,城市在女性的筆下有了屬于女性的另一種城市想象,并且展現(xiàn)了城市富有女性色彩的另一面。而這正符合了嚴(yán)家炎和袁進(jìn)對于現(xiàn)代性的描述:“何謂現(xiàn)代性,就是指傳統(tǒng)社會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代社會過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的知識理念和價值標(biāo)準(zhǔn)。”[2]下面我們來具體論述一下女性都市文本所體現(xiàn)的現(xiàn)代性,需要說明的是我們要談的女性都市文本指的是女性作家筆下的都市文本,而不是描寫女性的都市文本。
一、 女性都市文本寫作本身就具有現(xiàn)代性
從開掘山洞到城市建立,男性英雄創(chuàng)建文明的業(yè)績推動了人類現(xiàn)代的進(jìn)程,作為現(xiàn)代文明產(chǎn)物的現(xiàn)代城市,以雄偉挺拔的建筑象征了男性力量的輝煌,于是很多人說:“城市是男性的象征,是男性的城市,是男性完成英雄業(yè)績,實現(xiàn)生命價值的角斗場。”很多年以來,對于城市的想象一直都是以男性話語下的城市為主的,女性話語則處于被忽略的地位,甚至因為時代的原因,女性都市文本本來就很少。然而追溯歷史,事實則正好相反。城市是屬于男人的,更是屬于女人的。甚至可以說,城市與女性更為契合。
首先,在歷史上,在都市的發(fā)展過程中,女性是從來未曾缺席過的。現(xiàn)代都市文明的入侵就是通過女性符號起作用的。女性與城市的糾纏,在中國似乎一開始就觸目驚心。中國最早的城市符號的出現(xiàn)當(dāng)屬上海。而上海的興起卻并不是完全以工業(yè)的發(fā)展、洋樓建筑為標(biāo)志的,從性別角度來說,當(dāng)時展示城市風(fēng)采的則是鄉(xiāng)鎮(zhèn)周圍的妓女,她們源源不斷地進(jìn)入城市展示西方的服裝、化妝品,表現(xiàn)了西洋文明對中國侵入的流變過程。妓女把西洋文明帶入了仍具濃重鄉(xiāng)村色彩的鄉(xiāng)鎮(zhèn)樣子的上海,引來了西方城市符號的文本變種,這些變種依附在服裝、化妝品甚至小洋車的裝飾品上,從而導(dǎo)致了整個上海廣闊生活和閱讀視野的改變。這樣說來,女性符號與城市符號的糾纏正好意味著堅兵利炮不能攻入中國,不能建立現(xiàn)代都市,可是通過女性卻順利地實現(xiàn)了這一目的,進(jìn)一步說明了女性與城市的密切關(guān)系和女性對于城市的特殊意義。我們甚至可以這么說,女性本來就是屬于城市的。城市使女性獲得了屬于自己的獨立空間,使女人擺脫了農(nóng)業(yè)文明時期體力不如男人而被強制規(guī)定了的弱者角色和附庸位置。現(xiàn)代化城市里的工業(yè)文明使人類擺脫了對于體力的依賴,男子可以做的工作,女性照樣可以勝任。這樣,在城市中生活,女性的身體變得伸展自如,可以盡情感受屬于自己的都市生活,擁有了伍爾芙所說的“一間自己的屋”。
女人與城市之間的這種深切的淵源,讓女人天生就喜歡依附城市,對于鄉(xiāng)村并無半點留戀。而男性卻正好相反,他們在走向現(xiàn)代化都市的過程中,往往把自己當(dāng)作一個外來客,身體在城市中,心卻在鄉(xiāng)村。這點在生性敏感的男女作家身上表現(xiàn)得更加明顯。男作家們大多喜歡把更多精力放在農(nóng)業(yè)文明崩潰的痛苦的感受之上。如沈從文,一心向往農(nóng)業(yè)文明的基調(diào),希望它永存不朽,對壓力不勝重荷。郁達(dá)夫早期小說《沉淪》中有許多城市場景,但敘述觀點和感受卻是反城市的或者說充分表現(xiàn)了男主人公對于城市非常不適應(yīng)的感受。相對于男作家,女作家就要輕松自如得多,如冰心在體現(xiàn)母愛、童真和自然的作品中,雖也表現(xiàn)了對鄉(xiāng)村自然的向往,但那已不再是農(nóng)業(yè)文明狀態(tài)下的落后、野蠻、沉重,而是生活在城市中感受回顧美好自然的狀態(tài),反映的是城市女性對自然向往的心態(tài)。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中,城市女人的苦悶呈現(xiàn)為欲望的苦悶,她體驗自身,對男性有距離地觀賞和評判,女性在這樣的狀態(tài)下,具有健全的心理人性,不存在鄉(xiāng)村情結(jié)和城市情結(jié)的對抗。
由此可見女性與城市的天然的契合關(guān)系,但是更重要的是證明了相對于男性,女性似乎更懂城市,女性筆下的城市想象將會使城市呈現(xiàn)得更為完整和獨特,打破了城市為男權(quán)話語所獨霸的局面。在城市民主自由的氛圍中,她們發(fā)現(xiàn)了自己,她們中的許多人還勇于打破“性”的禁區(qū),將都市中的兩性關(guān)系放在大家面前,逼迫著現(xiàn)代人不得不去重新考慮兩性關(guān)系,單就這一點來說,女性都市文本的寫作本身就是具有現(xiàn)代性的。另一方面,在整個中國社會的轉(zhuǎn)型中,女性作家的都市文本不僅是對城市生活的反映,也是對中國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反映,這種反映要比男性作家更加深刻,更具現(xiàn)代性。因為她們對城市的理解更為感性,是精神層面的,她們沒有返回鄉(xiāng)村的可能,她們也不愿意返回,她們只能向前走,而且這種無路可退的感覺會逼迫她們更加努力地去反映城市并企圖改善城市。正因如此,她們的文本對于改進(jìn)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的各種問題也是深具參考價值的,因而她們筆下的都市文本是具有現(xiàn)代性的。
二、女性都市文本的寫作方法是深具現(xiàn)代性的
(一)以個人感性認(rèn)識代替宏大敘事
李歐梵在《當(dāng)代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性和后現(xiàn)代性》中說:“中國的現(xiàn)代性我以為是從20世紀(jì)初期開始的,是一種知識性的理論附加于在其影響下產(chǎn)生的對于民族和國家的想象,然后變成都市文化和對于現(xiàn)代生活的想象。”[3]對于都市的想象,男女作家向來就是有很大不同的,男性作家習(xí)慣于從宏觀的角度來觀看都市,在他們的都市文本中,都市只是一個整體,一個宏觀的背景。如在茅盾的《子夜》中,都市代表了進(jìn)步的力量,作為鄉(xiāng)村的對立面出現(xiàn);在施蟄存、劉吶鷗、穆時英等新感覺派的作家的都市文本中,他們極盡展示都市的繁華,通過展示都市的奢華從而揭示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中國仍然存在的問題和矛盾。但是在女性的都市文本中,她們不再像男作家那樣利用城市來構(gòu)建宏大敘事,利用都市來反映國家歷史民族的發(fā)展進(jìn)程。她們用她們的個人的感性認(rèn)識來代替宏大敘事。女性天生敏感,相對于男性,她們更為感性,因而她們關(guān)注的是都市的內(nèi)部變化對自身感覺的影響,并在其中融入了更多女性對于都市的理解和心理體驗。“作為一個女人的生存是不能被闡述的,它必須去感覺,它必須使自身被感覺到。”[4]因而,女性善于描寫的是她們對于這個城市的感覺,如果說男性描寫的是這個城市的外觀,那么她們則是深入肌理的,她們展示的是這個城市的內(nèi)涵。
最具代表性的當(dāng)屬王安憶的《長恨歌》,作品以一個女人王琦瑤的一生來寫一座城市的歷史變遷,以一個女人對于這個城市的各個時期的心理層面的認(rèn)識來反映這個城市真正的內(nèi)在精神。從王琦瑤的日常生活中提煉出對都市的記憶和女性人生的理解,你了解了這個女人也就跟著了解了這個城市,從上海弄堂中的女性生活的瑣細(xì)之處挖掘出上海市民的生活理想,一個弄堂就是一個上海。“上海弄堂總有股小女兒情態(tài),這情態(tài)的名字就叫做王琦瑤。”同樣的,還有池莉的《煩惱人生》,從城市中鍋碗瓢盆的世俗生活入手,用女性的感性去感覺這平凡生活所蘊涵的獨特的韻味,雖沒有多么宏大的歷史背景,倒也讓你從生活的一隅了解了整個城市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別有一番滋味在其中。
這就是女性都市文本的一個特別之處,用瑣細(xì)生活反映歷史民族的發(fā)展進(jìn)程,用個人感覺來感知城市生活。這種書寫方法相對于之前的宏大敘事,將視角放在平凡生活上,用女性獨有的感性書寫城市的另一種感覺,城市不再是一個整體,變得立體而有血有肉,它偏重于寫個人體驗,用自己的語言建立了一個屬于自己的世界,但是又不狹隘,國家民族的歷史又真實地反映在文本之中,因而是深具現(xiàn)代性的。
(二)身體寫作
在女性都市文本中,有一部分作家的寫作方法是不容忽視的。都市化進(jìn)程帶來了女性都市文學(xué)的新時期,“城市的發(fā)展,意味著都市人獲得了新的生存空間和生存方式,這是中國人在向西方學(xué)習(xí)過程中追尋‘現(xiàn)代性,尋找自己話語的必然結(jié)果。”[5]因而可以這么說,身體寫作向人們開拓了一個新的寫作空間,正是人們追尋“現(xiàn)代性”的結(jié)果,是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結(jié)果。同時因為現(xiàn)代化進(jìn)程加速,女性生存空間擴大,她們的性別意識加強,身體寫作也成為了對抗男權(quán)話語霸權(quán),追求平等的一種手段,而現(xiàn)代性的一個重要特點便是追求現(xiàn)代精神即自由、平等。因而從這兩方面來說,身體寫作本身是具有現(xiàn)代性的。
身體寫作可以成為女性承認(rèn)自己身體的有效手段,在文學(xué)的世界里,她們盡情地表現(xiàn)自己的身體。在陳染、林白等新時期的女作家的都市文本中,欲望書寫包含著美感和追求。在《致命的飛翔》中,林白用審美化的語言將身體的欲望闡釋為一種自由若飛的神奇的感覺,將身體與美感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而衛(wèi)慧、棉棉她們則是試圖通過符號的方式將肉體欲望變成一代人的“形而上學(xué)的表現(xiàn)”。在衛(wèi)慧的《蝴蝶的尖叫》中書寫的都市在解放欲望和坦然地面對欲望層面,解構(gòu)了傳統(tǒng)道德,用性的符號構(gòu)造女性都市,女性性別體驗的快感和都市現(xiàn)代氣息融合在了一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身體寫作追求的不是張揚個性,而是個性書寫本身,一味地展覽身體,表現(xiàn)欲望,不但把女性都市寫作引入了歧途,還從某些方面滿足了男性的窺視欲,這與最初的目的是相反的。如此看來,“身體寫作”反而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細(xì)思一下,我們也可以把它當(dāng)作現(xiàn)代性的一種表現(xiàn)。
綜上所述,女性都市文本的書寫填補了文學(xué)史上許多的空白,讓都市以另一種形象出現(xiàn)在大家面前,而這要將很大一部分功勞歸于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加快,女性獨立空間的獲得。女性只有擁有了自己的自由空間,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新,女性都市文本不僅是對自己和城市的發(fā)現(xiàn),也是對中國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反思,是深具現(xiàn)代性的。
參考文獻(xiàn):
〔1〕荒林.花朵的勇氣——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文化的女性主義批評[M].九州出版社,2004.
〔2〕嚴(yán)家炎,袁進(jìn).現(xiàn)代性:二十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的顯著特征[J].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2005(5).
〔3〕李歐梵.當(dāng)代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性和后現(xiàn)代性[J].文學(xué)評論,1999(9).
〔4〕埃萊娜·西蘇.從潛意識場景到歷史場景[A].張京媛.當(dāng)代女性主義文學(xué)批評[C].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2.
〔5〕胡良桂.都市文學(xué)的現(xiàn)代特征[J].當(dāng)代作家評論,1998(2).
(責(zé)任編輯 張海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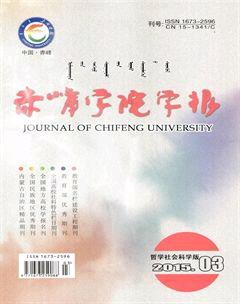 赤峰學(xué)院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5年3期
赤峰學(xué)院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5年3期
- 赤峰學(xué)院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水滸傳》之宋江人物形象研究
- 淺談辛棄疾的悲劇性
- 妝容與服飾在宋詞中的作用
- 從“詩言志”看杜甫對《詩經(jīng)》詩學(xué)精神的繼承與發(fā)展
- 論中外神話中女性形象的差異
- 女性小說到影視生成的性別文化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