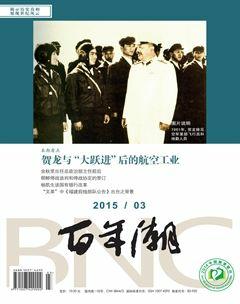江渭清三回故鄉
李炳侯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江渭清擔任南京市委第二副書記。江蘇恢復建省后,他先后擔任中共江蘇省委第二書記、書記、第一書記等職,是江蘇省委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第一書記。“文革”后期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1982年9月任中顧委委員。新中國成立后,江渭清大多時間在江蘇工作和生活,但他曾三次回到故鄉湖南平江,改革開放前后三回平江感受的巨大反差,令江渭清終生難忘。
1950年秋天,新中國成立不到一年,經濟恢復工作正在全國展開。這時,黨中央決定,讓部分幾十年南征北戰、走過萬水千山,與家鄉斷絕音訊的負責干部回鄉探望,尋找親人。這些老戰士回到故鄉后,要把黨對老區人民的懷念帶回去,感謝他們為中國革命做出的貢獻和犧牲,向老區宣傳新中國成立后黨的政策,以擴大黨在老區的影響。紅軍時代參加過平江起義,1930年參加過第一次打長沙,并屢建功勛的江渭清當時擔任南京市委第二副書記,他離開家鄉已經22年,中央決定將他列為第一批回故鄉探望的干部之一。江渭清的故鄉是湖南平江縣時豐村秀水大屯。黨中央通知他回故鄉探親,他心情萬分激動。在回程的路上,少年時代故鄉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不斷在他眼前浮現。平江暴動后離開故鄉時母親牽手送別的情景歷歷在目,眷戀之情沸騰在心,淚水一直在他的眼眶里轉動。如今,不知父母兄妹是否還在人間,還有那些支援平江暴動的鄉親、為革命奔走的同學是否還活著。他又想起當年參加平江暴動的同志都已犧牲在戰場上,今天只有他一個人回來,而且身上掛了八次花,腿部已經傷殘,他是從犧牲的戰友們的尸體里爬出來的人。
江渭清突然回到故鄉,轟動了全屯,許多年紀大的人驚訝地說:是渭清嗎?他活著回來了!一時,全屯的人都來看他。鄉親們對他都很熱情,對共產黨一片稱贊聲。回到家里,他見到離別20多年的母親,母親拉著江渭清的手說:“你總算回來了,和你一起走的都回來了嗎?”為不使母親傷心,江渭清含著淚說:“都回來了。”“那就好!”母親深情地看著江渭清,一直拉著兒子的手。
1950年,湖南剛剛解放不久,群眾生活還很苦,但鄉親們沒有一點兒怨言,因為他們看到了共產黨是為人民的,干部艱苦奮斗,清廉務實。他們感到生活會有希望的,對解放了他們的共產黨充滿了信任,都相信好日子定會
到來。
江渭清在家住了7天,他一面向群眾講解黨的政策,一面慰問為革命獻出親人的鄉親們。當時,江渭清的家鄉已著手進行土地改革。人民真正當家做了主人,這是盼望了多少世代的大事情。人民群眾對黨的熱愛之情,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男女老少都說共產黨好,人民軍隊好!當年跟著共產黨鬧革命的年輕人,沒有白鬧。群眾都說自古以來沒見過毛澤東領導的這樣好的軍隊,紅軍愛民如子、親民如家人。總之,對共產黨歌功頌德、贊聲不斷。因為不論是秋收起義,還是平江起義,都是從湖南發起的,湖南子弟大都跟著共產黨走了,20多年,家鄉人民盼共產黨回來,就像盼星星盼月亮。家鄉群眾對共產黨的擁護是從心里發出的。
1959年,江渭清已擔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南京軍區第三政治委員。這時的形勢和1950年已經完全不同,江渭清所在的江蘇也是政治風云迭起。恰恰就在這年9月底,他接到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三封加急電報,電稱:“你母病危,速歸。”于是江渭清請示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允他回鄉看望母親。假很快批下來了,他立即動身,先乘飛機到武漢,后乘火車到長沙,再坐汽車到平江,于當天晚上趕到家里。他來到母親病榻前時,母親已經處于彌留之際。次日凌晨,老太太摸著江渭清的頭,確信兒子已經回來,之后不到兩個小時就離世了。母親去世后,江渭清將兄弟姐妹等人召集到一起,提出喪事從簡,一不請和尚道士,二不請吹打彈拉,三不請人吃飯,只開個簡樸的追悼會。江渭清親自寫了一副對聯貼在大門口:“勤儉建國,節約治喪。”當時中國經濟面臨極端困難,農村生活異常貧苦,許多人都生了浮腫病。七里八村知道江渭清這個大干部回來都趕來訴苦,詢問為什么辦公共食堂,為什么不許搞副業,為什么要搞“大躍進”。群眾說:搞按勞取酬、多勞多得不是很好嗎?但這時江渭清并不了解鄉間群眾的情況,他還宣傳人民公社好,群眾都用疑惑的眼光看著他,這已經不是江渭清第一次回來時的眼光了。安葬這天,江渭清家請鄉親們吃了一頓飯。在當地政府幫助下,從幾十里外的鄉下買了一口只有40多斤重的小豬殺了。小豬瘦得可憐,沒有多少肉,煮了一鍋湯。后來,江渭清叫秘書想了許多辦法買了100斤大米、幾百斤山芋,買了50斤黃豆做豆腐,沒有幾天就吃光了。江渭清很心酸。他后來心情沉重地說:作為一個省委書記,我當時深感內疚。對不起為革命做出那么大犧牲,革命勝利后又過著這么苦日子的老區人民。江渭清知道,這些都是由于浮夸風、“共產風”等“左”的思潮導致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的結果。但當時廬山會議剛開過,“左”的形勢異常嚴重,他也沒有更好的辦法。江渭清在家只住了三天,將母親提前安葬后,便回到了南京。
江渭清二次回鄉感觸很深。回到南京后,一次毛澤東在浙江要他匯報江蘇情況,他如實匯報了江蘇的情況和回湖南家鄉的情況和感受。并向毛澤東建議:“共產風”要糾正,公共食堂不能再辦下去,浪費太大,家庭副業不能全搞光。第二次回故鄉,由于江渭清看到農村的實際情況,他的腦子不再發熱,實事求是成為他工作遵守的座右銘。
江渭清1959年第二次回故鄉到1984年第三次回故鄉,中間相隔23年。
1982年,江渭清從一線退下來,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84年10月,他第三次回到故鄉。這次回鄉他住的時間較長,還深入到鄉里進行調查研究。這時,他的家鄉簡直是另一番天地。鄉下喜氣洋洋,許多鄉親又來看他。這次不是來討飯吃了,也不是來訴苦,是來告訴江渭清他的家鄉每人每年平均可收獲900斤糧食,年終分紅,每戶還能拿到1000元,甚至更多一點。副業發展也很興旺,98%的農戶殺了過年豬,公社已經蓋起了寬敞的電影院,農民勞動之余可到那里看看電影。群眾不再吃山芋、紅薯,而是吃大米、白面。農村普遍搞起了聯產承包、專業承包。鄉親們關心的主要不是生活問題,而是現行的農村政策會不會變。他曾到蘇州去看鄧小平,說農民擔心政策再變,鄧小平說,不會再變了。江渭清對改革開放僅僅幾年的變化深有感觸,特別是這次回去他的侄兒為他殺了一口近200斤重的大肥豬,江渭清十分感慨。想起他母親去世時,他跑了幾十里才買到一口40斤重小豬,真是今非昔比。江渭清回到南京后,激動中賦詩一首:“誰道平江路不平,乾坤奠定是人民。堅持馬列春常在,遍地黃金遍地銀。”
感觸中,江渭清對他三回故鄉所見到的農村不同時期的變化,作了較為深刻的分析:過去,我們不面對現實,喜歡搞“左”的那一套,不在國家富強、人民富裕上多動腦筋,而是瞎指揮、亂折騰。當時我們有些干部存在著“三個誤解”:把社會主義誤解為共產主義,把集體所有制誤解為全民所有制,把按勞分配誤解為按需分配。看不到現實情況是“三個不相適應”: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不相適應,與群眾思想覺悟不相適應,與干部的管理水平不相適應。幻想一下子就把中國變成共產主義社會,結果欲速則不達,適得其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堅持的是一條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集中力量搞四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時期是我們國家35年來最正確、最充滿希望的時期,這是鄧小平與黨中央的同志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一大特色。
當時,江渭清已74歲,但他對黨的事業和國家的前途充滿信心,要在有生之年繼續發揮余熱,為實現國家“四化”竭盡余力。(編輯 潘 鵬)
(作者是解放日報社退休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