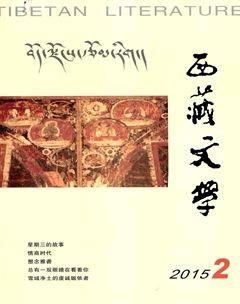“雜草”叢生的圓形跑道
佘學先
因色波遠居成都,一時無法進行實地采訪,故只能通過電子郵件交流,敬請讀者見諒。
問:色波先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你是有名的前衛作家,喜歡你的作品的讀者不少。遺憾的是已經很久沒看過你的小說了,是什么原因促使你長時間輟筆?
答:這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這里,我只能簡單地把這件事情的起因講給你聽,看看是不是能與其他輟筆的所謂前衛作家構成區別。剛開始的時候,我只是覺得自己突然悟到了一個全新的小說領域,它迫使我不得不去對許多已經熟知了的事物和已經成型了的認識重新加以審視。這無疑是一次觀念大遷徙,需要靜下心來廣泛閱讀和認真思考。當然,這對我來講本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可陰錯陽差的是,緊接著我又開始了現實生活中的舉家大遷徙。兩種遷徙疊加在一起,我已經沒有心思和精力寫作了。那是一段精神和肉體均居無定所的時光。盡管如此,每每回憶起來,我卻很少為此感到遺憾,因為正是這種身份的閑置,這種一切從零開始、什么也不是的處境,給我提供了脫胎換骨的條件,使我能夠毫無顧忌地向小說發問。
問:在你的理解中,小說是什么?
答:小說是雜草,其真正價值和獨立存在的理由都產生于它放棄了成為大樹和鮮花的愿望之后。
問:這是否意味著你對寫作的把握更大了?
答:沒有哪種理論或者經驗能夠使寫作變為一項有把握的工作,作家的苦惱是永遠存在的。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將復雜的事物簡單化,而過去、或者說年輕的時候,我總是將簡單的事物復雜化,并且樂此不疲。這是兩種不同的才能。
問:阿來認為他的寫作受益于西藏口傳文化更大,而你們的西藏寫作恐怕更多的是根據想象和對西方的學習。那么你當初寫作時是否了解西藏?
答:如果執意要從口傳文學中汲取營養,那么利用俗麗的辭藻和高昂繁復的敘述激情來吸引聽眾將是至關重要的。至于我們當時的西藏寫作,則一直是朝著兩個方向探索的,一是包括內地漢族和國外發達國家在內的文學思潮,二是西藏本土文化,然后再根據各自的小說稟賦與學養盡情想象。小說本身就是想象的產物,這無可厚非。這是我們從拉美作家那里學到的經驗,是出自寫作本身的需要,而不是要把自己搞成一個遵守“共享文化規范”的西藏文化學者。就我個人而言,我對西藏文化的了解不系統,可一旦某個文化截面進入我的小說視野,我差不多都會努力把它們演繹得盡可能精彩,以便讓它們能夠順暢地進入現代文學的認知系統。
問:那么當初你寫作時,究竟是出于自覺地對西藏文化的追尋,還是出于較為單純的文學沖動。
答:表現自己周圍獨特世界的強烈愿望、難以遏制的審美沖動(也可能是青春期的躁動,這點我不是十分拿得準;或許,兩者壓根兒就是一回事)以及對功名的渴望等等,都有。
問:比如《竹笛,啜泣和夢》,有多少是根據西藏文化的傳說,有多少來自想象,又有多少是對西方文學或拉美文學的模仿?
答:這篇小說的題材是西藏的,甚至還是根據西藏門巴族關于傳統樂器竹笛的起源故事和傳統曲子《抽泣》的音樂結構寫成的。在寫作時,我并不打算要通過這個題材挖掘出更多的、屬于西藏的區域性文化內涵,而是惦記著如何把它放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中重新加以考察。比如我對故事中的孤獨感就進行了一定的加工處理,為的是讓它能夠上升為人類的深層孤獨──原孤獨,并企圖由此完成地域和時代的跨越。另外,由于我幾乎完全采用了這首曲子的音樂結構,甚至在語言的節律上也緊扣著曲調的變化,這篇小說幾乎讓我忘卻了文本的規則和范式,是一次借助素材的力量讓小說走向音樂的實驗,因為在所有的藝術中,音樂在所指與能指之間最為飄忽。這是一樁很有意思的實驗,它帶給我的小說想象也是超乎常規的,只是做得好與不好又另當別論了,畢竟那時我才25歲。還有《星期三的故事》,這篇小說在很大程度上簡直就是對西藏民間故事《倉巴跳崖》的改寫。另外,西藏傳統文化中許多既形象又智慧的東西對我的啟迪也非常大,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
我想,上述解釋已經同時回答了你提到的兩個方面的問題,那就是既有西藏的文化傳說,也有個人的豐富想象,但模仿的卻是音樂而不是文學。至于拉美文學對我的影響,我要說的是,它只是以非常相似的民俗風貌、地理特點以及作家處境等等,印證了我對西藏新小說萌生已久的想法。而作為文學流派的魔幻現實主義,我的興趣不是很大,除博爾赫斯外,我最喜歡的還是美國以及歐洲一些國家的小說,比如意大利、法國、捷克等。但需要說明的是,西方文學作品和文學思潮在影響我的時候,也是要有許多前提條件的,那就是這些東西必須更有利于我對西藏題材的開掘,并且還要跟我自己的文學追求和素質相貼近,等等。
問:是不是說,這種聯系并不是直接的西藏文化材料的移植,而是一種隱含的、背景性的文化底蘊的影響?
答:對,差不多是這樣。
問:在你的小說中,往往隱含著較為深厚的佛教理念。宗教,當然準確說應該叫藏傳佛教,是不是你所有作品的靈魂?
答:實際上我不大把握得住“佛教理念”這個詞匯所能涵蓋的意思層面,但我可以明確地回答后面的問題,那就是任何宗教任何時候都不可能成為我任何一篇作品的靈魂,因為在我看來,圣潔的宗教意識和虔誠的宗教情感必定會拒絕小說的反叛精神和游戲姿態。不過,我完全認同宗教作為一種題材在藏族小說中存在的必然性,特別是已經化為日常的生活行為那一部分。
問:繼《圓形日子》之后,你的許多小說中都存在著明顯的“圓形意識”,能說說這是為什么嗎?
答:因為圓是世界密碼中最高級的符號。
問: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美國文學和拉美文學在中國的影響之大是有目共睹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西藏當代文學也不例外,成功地走出了一批在國內外都叫得響的青年作家。你是怎樣評價那個年代的西藏小說的?
答:一塊提前收割了的文學麥田,西藏小說史上一道耀眼的疤痕。這是我給那個年代的西藏小說下的結語。依我看,由于今天的小說已經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小說形成了一種有機的銜接,即便是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主要小說從西藏現代文學史上刪去,今天和今后的人們也不會從中發現任何問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西藏小說,是一段必須單獨記載的歷史。
問:我還是想再問一下,你那么早就封筆不寫了還有其他原因嗎?
答:有,對自己的寫作過分苛刻也是重要原因。對我來說,每寫一個新的小說,需要重新開始的東西太多了,而不僅僅是故事。正因為如此,雖然我的作品數量很少,卻感覺到已經走了很遠的路。另外,舉家內遷至成都后,我一直就沒找到一個可靠的文化支點,總覺得自己僅僅只是身份證上的一張照片。
問:打個比方,或許不很恰當。我覺得你的小說就有些像漢族作家中的阿城。阿城當年的“三王”,出手不凡,但他對語言的追求過高,這樣的寫作太累、要求太高,不可能持續得很久。在某種程度上,你可能也有點像先鋒作家中的孫甘露,他對語言的追求過于極致。不過我想知道,你在寫《竹笛·啜泣和夢》時,有沒有自覺地想到要去追尋西藏文化?你想,扎西達娃、阿來的小說,都寫到了不少西藏的人或事,難道你不能像他們那樣,去展開寫西藏嗎?你不用你的作品去有意地表現西藏,表現對西藏文化、西藏命運的思考嗎?
答:我后來寫的《星期三的故事》就是在探討這個問題。當然我也承認,小說濃得化不開并不是什么好事。《竹笛,啜泣和夢》是我改變小說觀念后的第一篇小說,后來我一直在努力探索其他表達方法,而且探索的力度還相當大,以至于大家普遍認為我那本叫做《圓形日子》的小說集完全不像是一個人寫的。但由于我是在湘西鳳凰長大的,受漢語文學傳統的影響在同伴當中最深,所以我過去的小說在強調與漢語文學的差別上相對來說也更為決絕,這可能預示著我的改變將是有限的,我的小說觀與國內漢語讀者的審美預設之間的疏離將繼續存在。我之所以只是強調與國內漢語讀者之間的疏離,是因為我發表在《西藏文學》(1985年第6期)上的《幻鳴》后來在意大利就很受歡迎。
問:我讀你們的作品,盡管扎西達娃的作品也有不少抽象性,但還是比較容易把握,而你的作品就很難理解。有一個評論家朋友寫了篇文章,里面將扎西達娃、阿來、范穩的西藏寫作聯系起來進行了比較。但沒有提到你的作品,他后來說是因為沒有辦法把握你的作品。我覺得你的《竹笛,啜泣和夢》,更像是詩,而不像小說。你的敘述過濃,濃得有些化不開,致使故事無法展開。
答:我在寫《竹笛·啜泣和夢》時倒是有過另外一個不是十分清晰的念頭,那就是我所描寫的這個西藏故事,是不是具有哪怕一點點關于藝術起源學上的意義?顯而易見,這種做法要求我對西藏文化和西藏命運的思考必須在寫作之前完成。至于說到為什么我不在小說中展開來寫西藏,這對我來說向來就不是什么重要問題,要緊的是我采用的又會是什么方法。
問:可不可以說,你的寫作,實際上還是有許多寄托的,但你最終要將所想到的東西轉化成特有的語言形式,所以,感到非常累,常常寫不下去。所以寫出的小說,更像是詩。你為什么不寫詩呢?
答:寫作的艱難不在于我不知道下一段將要寫什么,而在于我將采用什么方式做到“不說”,并通過這種“不說”來給出更大的小說張力,以克服“說”的局限性。
問:那你現在好些了嗎?
答:在這類問題上,我不知道什么樣的狀況算是好些了。至今我仍然堅持認為寫作的過程其實就是對靈感的褻瀆過程,只是我現在越來越能容忍這種褻瀆了。另外,我還想就你前面提出的問題強調一下:盡管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對小說中的“無價值時刻”甚至都產生了厭惡情緒,但把小說寫得像詩從來就不是我想要干的事情。我倒是非常想寫詩,但卻死活找不到靈感與成詩之間的現代通道。
問:最后一個問題。上面提到的那個評論家朋友說,在將扎西達娃、阿來、范穩的西藏小說聯系起來進行分析之后,感到扎西達娃的作品有些過于抽象,這種抽象讓他沒有辦法真正貼近他所想表達的西藏;認為阿來的《塵埃落定》將西藏敘事從扎西達娃的抽象半空中降落了下來,使西藏敘事詩意地貼近西藏大地,而且展示了西藏文化的多樣性;這種詩意的多樣性展示到了范穩那里,就更為豐富、精彩了。但是,《西藏文學》又曾經刊登過一篇文章說,將西藏詩意化正是內地人寫作的一種偏見,好像西藏就沒有切切實實的日常生活一樣。你怎么看這些問題?
答:關于文學作品落地的問題,我倒是有著完全相反的看法。文學恰恰需要具備飛離地面的能力,無論你是鴻鵠還是燕雀,總之要有一種翱翔在高天之上的姿態,盡管它們也要落地覓食、棲息,但我們不能因此就管它們叫家禽。當然,我承認能夠在空中翻飛的還有羽毛,可羽毛沒有生命,只能借助風力并追隨風向。至于文學作品中“將西藏詩意化”的傾向,這只是作家個人的寫作特點而已,這種現象的增多,直接與許多詩人轉行寫小說有關。在我的認識中,將西藏符號化和概念化的現象才是需要警惕的,這不僅會影響到西藏小說的多樣化呈現,也會縮短作家個人的寫作生命期限。在共享文化規范與個人的實際行為狀況之間存在著一條鴻溝,小說關注的應該是豐富的、沒有定數的后者。這個問題,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就在一些文學研討會上提出來過,之所以至今沒有解決好,我想,除了作家自身的原因外,還跟包括評論家在內的讀者審美期待有關。要想讓這個問題得到解決,大致需要這樣的前提:作家要了解西藏生活、熟諳寫作技藝、提升理論素養,而讀者也要逐步從符號西藏和概念西藏的閱讀成見中走出來。而這,正是西藏小說的未來。
責任編輯:次仁羅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