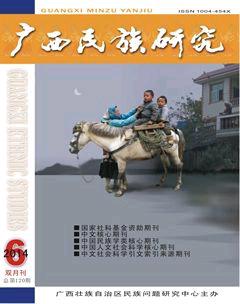金錢、權力與文化:節日現代性的建構與解構
甘代軍 李銀兵
[摘要]我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使傳統節日文化進入現代性的建構歷程之中,節日時空的脫域化、節日內涵的時代化、節日體系的碎片化和節日屬性的異化引發了人們對節日現代性及其金錢、權力運行機制的反抗。人們通過文化鄉愁的排遣、傳統節日保護主義的實踐來解構節日現代性的異化和束縛,在重塑生活世界的努力中逐漸實現節日文化對精神需求的滿足。
[關鍵詞]節日;現代性;建構;解構
[作者]甘代軍,貴州省高校人文醫學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學博士。貴州遵義,560003;李銀兵,玉溪師范學院副教授、西南大學博士后。重慶北碚,400700
[中圖分類號]G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4)06-0106-007
在解釋人類學的框架下,節日無疑是一個蘊含本土知識、本土世界觀與價值觀的符號體系和意義網絡,因而對節日的分析就是對節日文本所潛藏的本土意義的“深描”、揭示。如果說解釋學的節日研究代表著一種關于節日的“本體論”研究范式的話,那么功能主義的節日研究則代表了注重節日現代應用價值的“方法論”研究范式——功能主義通過闡述節日的文化價值、社會功能來確定節日研究的現實意義。基于這兩種研究范式的優勢,本文試圖兼收并蓄,以闡釋學、文化批判理論、功能主義的多重視角對節日文化進行分析,通過闡述節日的現代象征意義和功能價值,實現對節日文化的現代本質和現代功能的深度揭示。
一、金錢與權力——節日現代性的建構
節日是特定族群、民族、國家在長期的歷史積淀中形成、傳承并周期性舉行的祭禮、慶典、娛樂等活動與儀式,它既是傳統文化習俗的集中展示,又是以象征符號形式對集體意識、社會結構的曲折反映、再生產和強化。節日對傳統的展示、傳承和再生產并非僵化、凝固的,而是一個動態地修改、增減和發明傳統的過程。在自然社會環境和社會結構的現代變遷影響下,傳統節日文化也隨之進入現代性的復雜場域中。從此,節日既被現代性所重塑,也對現代性給予強化或抵制,并因此變得日益碎片化和多元性,深刻地表征了現代社會的成就、失落與困惑。
在前現代社會,地理的阻隔、交通工具的落后和生產方式的長期固化導致了不同文化之間交流、互動的遲緩和微弱,節日文化也因處于這樣的環境中而體現出濃厚的地域性、民族性、自足性、穩定性等傳統特質。當人類歷史進入到現代社會階段,節日文化和其他社會系統一樣,也陷入現代性的包圍之中并被深深打上了現代性的烙印。“現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們拋離了所有類型的社會秩序的軌道,從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態。在外延和內涵兩方面,現代性卷入的變革比以往任何時代的絕大多數變遷特性都更加意義深遠。在外延方面,它們確立了跨越全球的社會聯系方式;在內涵方面,它們正在改變我們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帶個人色彩的領域。”…。作為人們日常精神、社會生活重要領域的節日文化,其現代性的生成也就構成人類現代性體系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急速變遷的現代社會中,傳統節日浸染、吸納的現代性因素既全面又深刻,因而傳統節日的系統性瓦解與重構也非常鮮明并影響深遠。
在促成節日文化現代性特征的諸多因素中,金錢、權力無疑是最為直接而有力的影響力量。在傳統社會,節日文化較少受到金錢的困擾和支配,節日依賴地方群眾的信仰、倫理觀念、社會秩序、精神娛樂、社會關系和經濟貿易等自足性需求予以維系、再生產。在此,節日文化更多地表征為特定族群的信仰價值體系、精神文化、社會關系、社會秩序構建的需要,它為地方社會的存續、穩定和精神滿足提供社會舞臺和價值力量。因而,支配節日體系的是傳統的人與神、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和精神文化需求。正是這個緣故,節日的時間、地點和形式都與傳統生活節律高度一致,大多數節日都與人們生活的閑暇時間、作物生長收割的關鍵時期密切相關。在這些時期舉行節日活動,既是對傳統生產方式、生產環境的適應,也是對人們生活節律的及時調適和對精神、價值需求的適時滿足。但是,傳統社會這種自我調適、滿足與分享的節日文化在遭遇現代經濟系統之后,它就被經濟系統中的金錢、資本深深地侵襲和殖民了:節日不再是地方秩序、社會關系的維系力量,不再是地方群眾自我信仰、價值、精神追求的象征符號體系,而是首先淪為金錢追逐、支配的對象和工具。節日為了錢而存在,在金錢的驅使下節日可以脫離傳統的地理空間在任意地點舉行,也可以打破節日傳統時間的固定性而多次、反復地為游客展演,神圣的節日儀式也可以為了金錢而輕易表演,節日的傳統價值和意義就這樣在金錢的作用下開始失落:“人們越來越迅速地同事物中那些經濟上無法表達的特別意義擦肩而過……生活的核心價值和意義總是一再從我們手邊滑落;我們越來越少地獲得確定無疑的滿足。”作為現代經濟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旅游經濟,其無所不在的擴張潮流把傳統節日也卷入其中,使傳統節日日益脫離其原有文化場域、文化特性,節日的精神活動異化為物質銷售和消費方式,節日文化變成了空洞化的表演,節日的神圣信仰被對金錢的膜拜取代,節日的人性化社會關系變成了以金錢為紐帶和軸心的交易關系,節日的傳統秩序再生產功能變成了追求發展指標的經濟政治功能。這一切變化都是傳統節日現代性的總體呈現,并表征著節日的傳統特質和意義在金錢、資本支配下的深深異化。節日現代性的構建起源于兩大力量的相互推動:商品經濟、市場體系的跨界性擴張和政府追求經濟社會效益的權力操控,前者通過金錢、資本、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后者通過政府的政治權威締造成果。
在卷入現代生活體系越深的地方,傳統節日的衰落表現得更為明顯和全面。旅游市場的大力擴展為權力提供了動力和機遇,政府運用所掌握的政治、經濟、人力等資源對傳統節日符號系統進行表面的恢復乃至重構,“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成為節日體系現代性構造的主要方式。在我國廣大地區,節日文化資源豐富的地方往往都是經濟社會發展較為落后的地方,為了追求當地的快速發展,地方的旅游局、文化局等部門聯合打造節日文化旅游、節日消費經濟,大力開發利用傳統節日的象征資本、文化資本。政府通過掌握的行政權力把市場力量、社會力量整合起來,通過形式多樣的節日資源開發模式,實現對傳統節日現代性的建構。在各種自然、人文旅游區,傳統節日文化被嵌入其中,與旅游景區本無關的節日傳統被移植過去,成為景區游客文化消費的對象,在此過程中,被移植節日的傳統時空被任意更改,其為原生地群眾自我詮釋和分享的本土意義也隨之湮滅。在政府傾力打造的主題公園式的民俗村,節日的傳統時空性和本土意義的顛覆尤為明顯。在民俗村舉行的節日,也完全是權力與市場機制運作下的表演化、商品化的符號,它為游客的旅游想象和文化體驗提供價值與意義,為節日產業鏈條上的群體注入經濟效益與生活動力,同時也為政府權力運作的成敗提供文化試驗的注腳和案例。即便在政府打造的更具原生態的民族自然村,其舉辦的節日文化活動也難以擺脫“現代性的斷裂”的困境——“某些現代社會的組織形式并不能簡單地從此前的歷史時期里找得到”。在節日的現代性建構中,村民們往往適應政府、游客和利益的需要把原本退出日常生活的傳統節日習俗又重新恢復過來,恢復的常常是傳統節日的某些符號、形式,而那些深藏于這些表象背后的價值體系和精神意義已經被現代性的功利目的所篡改、遮蔽。
總之,在金錢和權力的作用下,傳統節日的現代性特征逐漸被構建和固化——節日時間虛擬化、節日空間脫域化、節日意義現代化。節日日益脫離其原生的時空序列而存在,其本土意義也隨之發生根本性轉換,因而節日的現代性發展歷程就是其傳統性消退的不可逆過程。節日時間的虛擬化在于,在各種表演化、商品化的節日活動中,節日文化展示的傳統時間不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節點:在各種舞臺和時刻,節日文化都可以適時地、任意地再現和展演,在再現和展演中,節日的時間已經被虛擬為一個符號、一個概念供人們記憶、認知和把握——而在傳統性節日中,節日時間與節日活動、節日儀式是唯一對應的關系(特定的節日內容只與特定的節日時間相對應)。節日空間的脫域化在于,節日不再依賴于某個固定的傳統地點(這個地方是歷史性、沿襲性的),也不再受原生地力量的支配,節日可以在權力、金錢的支配下在任意地域被建構,節日像一個可以隨地移動的文化櫥窗被巡回展示。因而,在被建構的現代性節日中,傳統的節日地點可以不在場,原生地的節日主人可以不在場,政府的權力和市場的資本也可以通過某種“缺席”把遙遠異地的節日搬演到某個預定的地方,“建構場所的不單是在場發生的東西,場所的‘可見形式掩藏著那些遠距離關系,而正是這些關系決定著場所的性質”,傳統節日的現代性就這樣被金錢、權力關系所建構。
二、文化鄉愁——節日現代性的解構
由于傳統節日現代性的建構導致了節日形式與價值意義的根本轉向,人們在節日的現代性情景中產生了不適、異化乃至焦慮感,于是人們對節日的傳統性進行想象、懷念和向往,這種文化鄉愁的彌散引發了人們對現代性節日的反思、批評和對節日傳統性的重建努力。
文化鄉愁是對現代文化的消極拒斥,是對傳統文化母體的深情呼喚和象征性回歸,它以懷舊的方式訴說著文化心理的不適和現代文化的危機,“懷舊是現代性的一個特征;它同時為確定性和解構提供肥沃的土壤,它是對現代性中的文化沖突的一種反應。”傳統的節日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確定而穩定的文化空間和文化母體,在其中人們感受到節日文化提供的持續性、傳統性、熟悉感和溫馨感,進而體會到自我文化生命的延續性和安全感。而被現代性所浸染的節日已無法為人們提供熟悉的文化圖式和文化體驗,現代節日對節日傳統時空的抽離、對節日傳統文化價值與文化體驗的消解引發了人們的節日文化失序感和焦慮感,因此人們的節日文化鄉愁孕育而生。人們懷念舊有的節日文化習俗,倡導通過傳統節日文化的傳承、保護來重建節日的合理價值體系和文化心理調適功能。
人們走出被現代性包圍的喧囂都市,走進偏遠的集鎮和鄉村去尋找消解文化鄉愁的傳統文化,人們想象那里的傳統文化、傳統節日還保留著城市中難以找尋的文化記憶。由于我國現代化、城鎮化進程的快速發展,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部分鄉村都在加快社會轉型、改善交通條件、促進文化交流的浪潮中使傳統生活方式和文化習俗被洗刷一新。這些地區再也難以為文化鄉愁提供相應的節日符號和象征體系。遠離都市的文化“朝圣者”到達那些已基本被現代文化同質化的村野,看到的往往是傳統節日文化的凋敝和現代性節日文化的繁榮——專為游客們精心準備的充斥了現代文化元素和文化觀念的被新發明的傳統:節日地點被轉移到交通更為方便、游客更為集中的集鎮或景區,節日的一些標志性象征符號也從無到有地被發明、展示,節日服飾的顏色、款式、材料也更具現代化風格,節日的舞蹈、歌謠、樂曲也融入了現代藝術的表現手段和元素,節日中的習俗活動也變成了非生活性的舞臺表演。因此,游客看到的只是碎片化的傳統節日文化,是一場失真的偽節俗表演,這與他們想象、期待的傳統節日文化存在很大差異,他們往往對此感到深深的失望乃至厭惡,因而難以真正排解文化鄉愁。對很多游客而言,古樸、純真的節日傳統才是其文化鄉愁的釋放劑,只有置身于傳統的熟悉感、純粹感中,他們被現代性侵蝕得失衡、麻木、焦慮的心靈才能得到傳統文化母體的溫暖和撫慰。因此,游客對節日文化本真性的追求和期待反映了他們對節日現代性的某種消極反抗。在城市中,快速的生活節奏、同質化的消費文化、沉重的工作壓力、喧囂擁擠的城市環境等現代文明病壓抑得人們難以承受;同時,現代都市浮華的風氣、象征性社會身份、眾多的發展機會、完備的交通設施等優越性又使人們難以割舍都市的生活工作方式。因而,它們對現代性的反抗只能采取消極的形式,暫時擺脫都市現代文化帶來的疲憊和厭倦,他們相信,只有回歸到遙遠而熟悉的鄉野,從傳統節日文化的本真性和質樸性中,他們的身心才能得到安寧和放松。
因此,一旦他們發現自己千里迢迢到達的卻是一個個充斥著現代都市文化元素和特質,并被高度舞臺化、偽裝化的所謂節日傳統文化時,他們就充滿了失望乃至進行深刻批評。節日偽文化對本真文化的遮蔽根源于節日文化的商品化、物質化。本真的節日文化是生活態的文化,是地方民眾日常生活習俗的自然流露和自發展示,是自足的文化自娛而非他者化的文化銷售,是審美化的過程而非商業化的表演。因此,一旦節日成為商家賺錢謀利的工具,節日文化的本真性、傳統性必然變味和變異,因而游客看到的只能是打下了現代性烙印的異化了的節日文化,它無法給人們提供鄉愁的精神歸宿,“節日文化的審美情感和趣味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可以使休閑生活更加愜意。但是,隨著全球化、現代化對節日傳統文化的沖擊,節日傳統文化在年輕人心目中逐漸淡漠,甚至變得庸俗化、物質化。節日被異化成為物質消費和享樂的借口,也就消解了節日的神圣性和文化性。”因而,商人對傳統節日文化的商業化解讀、建構和供給只是對節日現代性的復制和再生產,這反而激起游客的拒斥和批評。
節日文化的表演化、偽俗化和異化激起了人們恢復、保護節日傳統性的努力。傳統節日的生命扎根于特定的文化空間之中,因此,消解節日現代性的弊端、壯大節日傳統性的活力就需要維護好節日的傳統文化空間。節日文化空間是歷史延續下來定期舉行節日的物理場所和固定時間,是節日文化傳統性的構成要素之一。保護節日文化就需要把節日置于傳統的時空之中,以確保節日的歷史感、熟悉感和文化根基。只有這樣,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抵制、消解節日現代性造成的脫域化傾向——節日的脫域化為金錢與權力機制對節日時空的任意遷移、復制和解構奠定基礎。在更深層次上,保護傳統節日文化傳統性往往就是破除節日現代性的生成機制,把節日重新植入其原生的文化土壤和文化機制之中,這是一場艱巨的斗爭,是對抗現代性的一場艱苦狙擊戰。因為,在社會生活整體性被現代性包圍的環境下,節日文化的生產與走向已經深深地被作為現代社會支柱的金錢和權力所支配,“官商主宰或官商合謀以左右傳統節日走勢的趨勢,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愈來愈明顯了”,節日的活動、內涵和形式基本被政府、市場力量所控制——民眾從傳統節日的主人地位消退,變成節日的觀眾、看客;政府成為節日總體設計師和策劃者,掌控著“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節日權力和節日模式;而市場力量成為節日的真正幕后主體,它們讓傳統節日碎片化、商品化,其唯一的目的就是以讓人眼花繚亂的節日符號、產品使民眾成為節日的消費者。所以,人們看到的節日基本上都是只有節日的一些傳統符號、儀式,而缺乏文化內涵和完整的節日傳統形態。正是這樣的節日運行機制才導致了節日文化的異化。因此,要保護好節日的傳統意義和完整形態,必須要重構節日文化的生成機制,讓節日真正成為以普通民眾為主體和主人的節日盛典,使節日不再是政府權力構筑的政績工程,不再是金錢和資本編織的消費陷阱和物欲化泥淖;只有讓節日變成群眾自我舉辦、自我娛樂、自我分享和自我發展的文化體系,才能真正消除節日現代性的桎梏,“讓傳統節日回歸民眾,由民眾自主組織、自愿參加、自己管理,把傳承和延續中國傳統節日文化的文化權利,放回到節日文化的主體——老百姓手中”,“改變目前很多地方由政府包辦和官商共謀主導過節的格局,回歸到‘民間的事情民間辦的傳統上來,已經是勢在必行的了。”
三、生活世界——節日文化重構與多向度的人
在金錢、權力機制作用下的現代性節日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世界物質化、商品化的溫床,人們在節日中獲得的不是精神文化的盛宴和愉悅,而是物欲主義、消費主義和拜金主義的膨脹,由此導致的是節日活動的空洞化、偽造化和人們精神世界的荒漠化、人格發展的片面化——人變成了單向度的人。人們因在市場提供的豐富節日商品中獲得某種虛假的消費自由和幸福而喪失了對市場壟斷的反抗意識,市場的需求壓制了個體的真正需求,金錢、商品所構造的生活方式變成了最“合理”、最“舒適”的生活模式,“更多的社會階級中的更多的個人能夠得到這些給人以好處的產品,因而它們所進行的思想灌輸便不再是宣傳,而是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這是一種好的生活方式,一種比以前好得多的生活方式;但作為一種好的生活方式,它阻礙著質的變化。由此便出現了一種單向度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單向度思想和行為模式也為自己播下了反抗的種子,文化鄉愁的生成和引發的傳統節日文化保護在深層次上就是一種設法阻止人們走向單向度化的努力。
人們試圖消除現代性節日文化所代表的現代文化對其傳統生活世界的侵蝕,并設法重構其日常生活世界的結構。生活世界是依靠歷史沿襲下來的習俗、慣例、傳統等規范而運轉的社會生活狀態,“它是一個可信、熟識和慣常行為的世界”,傳統性節日文化依靠相對封閉、穩定的生活世界環境而存在。當現代性生活方式形成后,它與現代社會的金錢和權力共同發揮作用,使生活世界淪為被它們共同支配的現代性世界,進而其中的傳統性節日文化也受到沖擊并被改造為現代性節日系統。但是,“生活世界并不只是聽憑經濟和行政上所采取措施擺布。在極端的情況下,則會出現被壓制的生活世界的反抗,出現社會運動、革命。”文化鄉愁的彌散逐漸催生了人們對節日現代性的解構實踐,人們試圖通過傳統文化保護來恢復節日的傳統性特質,因此積極主張使傳統節日融入并逐步成為人們現代的日常生活方式。在當今時代,人們的生活世界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尤其是日常生活領域,經濟化、消費化等現代性元素對人們的生活產生重要影響,這些元素甚至侵入作為人們重要生活領域的節日文化場域之中,使節日這一原本充滿傳統文化特質和人文精神的系統日益物質化,由此造成人們在節日期間缺乏真正的精神性享受。人們紛紛感嘆現代節日的同質化、物欲化,人們在市場提供的吃喝玩樂等現代性消費中深深感受到節日傳統精神的衰落。因此,人們不斷產生對消費性節日的拒斥和疏遠,人們開始逃避現代性節日并呼喚充滿人文精神的傳統節日文化的回歸。傳統節日文化回歸人們的日常生活世界是一個系統的過程,既要使節日的文化內涵、文化精神回歸到人們的心間,讓傳統時代對自然、家園、家族、生產生活信念和精神信仰的熱愛和憧憬重新融入節日活動之中,也要使節日活動回歸到人們自我組織、自我娛樂和文化傳承的軌道上,避免節日完全成為金錢和資本支配的、追逐利益的空間。同時,節日向人們生活世界的回歸還需要重構系統的節日文化符號,使被現代性肢解的碎片化的傳統節日符號以完整的形態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節日的歷史淵源、發展歷程、價值內涵、象征符號、主題活動、參與模式等節日元素都應在節日期間予以完整呈現和強化,任何對節日元素的片面化恢復和展示都無法還原節日文化的整體精神價值。在節日傳統體系的重建過程中,需要尋找與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緊密結合的切入點,以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調動節日參與熱情和積極性,只有這樣才能使節日真正融人人們的日常生活,從而確保節日文化的群眾基礎和生命力。
在融匯傳統節日文化與現代生活方式的積極實踐中,一種無效乃至虛假的文化復興傾向需要克服——一些地方政府把節日復興工具化為謀取經濟社會發展的手段,而忽視或消弭了節日的真正歷史文化內涵,“每到節日,‘假日辦、經濟管理部門和商家總是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導到旅游和商品消費上。有些政府主管部門幾乎忘掉了文化,也許他們壓根兒不懂文化。”在當今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物質生活條件的大大改善使人們的真正生活需求已經從物質性轉向精神性,因此,如果造成節日的片面物欲化,就會使人們無法獲得真正需要的豐富化、個性化精神滿足。對政府主導的節日經濟應該進行根本性轉向,必須把群眾生活世界迫切的精神文化需求作為節日文化的主流和重點,使群眾通過節日文化活動把生活世界重新改造為充滿文化內涵和人性精神的世界。為此,政府需要擺脫把節日文化過度工具化、商業化的取向,使節日文化的主體性真正回歸民眾,滿足民眾的精神性需求,從而在根本性上改善民眾的生活世界結構。
此外,民間社會需要重新發展、壯大自己的節日組織和團體,增強文化自覺意識和文化自主能力,把被權力和金錢異化的節日文化重新扭轉過來,使節日真正回歸到精神性文化傳統之中。人口老齡化的現狀為民間節日組織的發展提供了人力資源,大量老年人口、大量空閑時間和人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民間組織發展的重要動力。因此,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城鎮,民間的文化藝人可以在社區組織起來,把恢復傳統節日文化的內涵和特色作為其文化需求和生活世界自足化的重要依托。為此,政府應該發揮好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功能,為民眾自主組織節日活動創造條件,通過提供政策、技術、場地乃至資金等方式促進民間傳統節日文化的恢復和重建,以保障民間節日文化活動真正成為精神性、自主性的文化盛宴。
生活世界的重塑還須克服民眾缺乏文化自覺意識的障礙,民眾在生活世界中對文化自主權的忽視、放棄則是生活世界被金錢和權力控制的一個重要原因。對普通民眾來說,生活世界是其依賴傳統、慣習和世俗力量運轉的領域,人們的思想習慣和行為方式往往缺乏洞穿事物本質的批判性、反思性,人們對于給其帶來物質性滿足的社會系統的異化、控制本質缺乏深刻認識,反而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因此,人們要找回被權力和金錢篡奪的主體地位,必須要依賴于具有反思精神的文化精英的啟蒙和培育,培養起民眾的文化自覺意識和文化批評精神,在文化批評和文化自覺狀態中認識、建構和維護自己的文化主體地位。文化精英對民眾文化反思精神的培育是一項艱巨、長期的任務,需要精英們以實際行動構建起文化內涵豐富、形式多樣、貼近群眾日常精神需要的節日活動體系,使民眾在這樣的節日生活中獲得精神的滿足和自主能力的發展,從而克服被市場體系異化、單向度化的傾向。
總之,民眾要把自己從“商品拜物教”、消費主義、權力壟斷等異化中解放出來,找回自己真正需要的精神文化活動,實現在節日文化活動中的自主、自治、自由等主體地位,需要不斷提升自我個性、文化自覺意識、文化批判能力;還需要與政府、社會團體、知識精英等力量聯合起來,通過對權力、金錢主宰地位的解構,通過對民眾文化自主能力的培育,使群眾從單向度的人走向“總體的人”、“全面的人”,“人是自由集體中自由的個人。它是在差別無窮的各種可能的個性中充分發展的個性”,“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
四、結語
從解釋學的角度看,節日現代性的形成有其內在機制與意義根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傳統節日文化在金錢和權力雙重力量的作用下,被重構為過度物質化、消費化的經濟場域,并被賦予了經濟化、金錢化的現代功能與目的。隨著現代性對人們文化心理平衡的打破,文化懷舊的節日鄉愁使人們對傳統的節日文化充滿了渴望,人們逃避現代化大都市,走向鄉野,去尋找昔日節日文化的舊影和溫情,以拒斥節日文化現代性的束縛。那些鄉野“朝圣者”在賦予其文化旅程以精神意義的現實,表明了節日現代性與人們心靈需求的某種疏離。從功能主義的視角看,遏制節日現代性過度蔓延的現代價值在于:過于現代性的節日與人們的文化鄉愁和多向度人格需求相背離,因而只有努力探索祛除節日現代性對人們日常生活深度侵蝕的途徑,抑制金錢、權力機制的雙重束縛,在一定范圍內系統地重建傳統節日文化,重構民眾自主自足的生活世界,才能塑造全面發展的人格和完美的現代生活。
[責任編輯:羅柳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