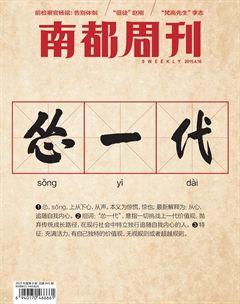在臺灣遙祭一位叫姚貝娜的大陸歌手
駱以軍
在這個清明時節,我想起來年前逝世的大陸歌手姚貝娜。
姚貝娜病逝的新聞,在臺灣肯定沒受到如大陸那樣的關注。在臺灣,可能除了《中國好聲音》的觀眾,一般人恐怕對姚貝娜都不熟悉。或許媒體寫“《后宮甄嬛傳》片頭曲演唱者”時,大家會哦地一聲恍然過來。
在姚貝娜剛去世那些天,我上YOUTUBE搜尋第二季《中國好聲音》:從第一輪盲選,讓導師為她發生哄搶;到她飆高難度高音的幾場;連能唱惠妮·修斯頓的臺灣小胖(這位在臺灣可是家喻戶曉),都被她PK掉。我熬夜把每一集都看過,像瘋魔一樣,反復聽著她唱過的歌;被這女孩的堅毅、認真打動。準確地說,某些遠距的、非貼近人類短暫時空所經驗的什么感受打動了我。
怎么說呢?在選秀節目舞臺上,你知道那些殘酷設定的淘汰賽,正是一個超現實夢境的現代資本主義祭壇。舞臺上那些年輕歌者的勝利或輸了之瞬的哭泣、擁抱、導師每每陷入淘汰誰的兩難,那多少都有扮戲成分。但姚貝娜一直以王者之姿,優雅謙遜,在倒數第二輪意外敗給一位小姑娘;那近乎驚呆、淚崩、哭著離場的模樣讓人深深著迷。
我還看了她在春晚上演唱跨年曲的影像,還有她唱《冰雪奇緣》中文版主題曲的MV。很奇怪的,我用YOUTUBE的不同鏡像,拼組出來一個讓計算機前的我著迷、卻連名字都陌生的女孩。其實她已經不在這世上了。在看到她過世的新聞傳來臺灣之前,我(或大部分臺灣哥們)根本不知道大陸有這么一位女歌手。網絡上有許多她仍那么清晰活著的影像,讓你覺得她在那發著光的演唱比賽的框格里,持續活著。
我想我腦海中的那個“姚貝娜”,定然和任何一位大陸哥們記憶里的姚貝娜不是同一個人。那似乎是她死去之后,才像遙遠外層空間漂流飛行體傳回地球的信號,由于時間差被延后接收,在我的視網膜、腦額葉重構了另一個栩栩如生的她。她在那款款微光的視頻小格里,巧笑倩兮活著。譬如看到在春晚上演唱的她,或在另一些表演場合演唱《甄嬛》的她,我覺得和在《中國好聲音》里飆歌爆發,像要把自己胸腔都唱綻裂的她,常唱至熱淚滿面的她,不是同一個人,似乎連臉妝都不很像。對我而言,她變成時間之外的拼貼、組裝、填色,其實缺乏真實的姚貝娜那細細瑣瑣累積在中國大陸人記憶里的脈絡。
這后頭其實有一種“臺灣閱讀大陸”,或之前“大陸閱讀臺灣”的科幻電影式隱喻,似乎拿到你手中的那個魔術方塊,左旋右轉翻面觀察,其實它可能是一個組裝過的模型。這不小心會變廢話;哪個傳奇明星不正是脫離了真實生命本身才得以在時光中傳遞,變成一個發光的圖像?瑪麗蓮·夢露、黛安娜王妃、鄧麗君……哪一個明星的故事交到一代一代人手上,不是一枚已被刨模打光過的可旋轉排列組合的模型?
現在臺灣人拿到手上的這枚魔術方塊,已經跟以前不一樣。上世紀最后十來年,臺灣“解嚴”后出版爆炸的黃金時光,“漂洋過海來看你”的是莫言、余華、蘇童這些人的小說,是心靈史的傳遞。現在你看到的是大陸新一代的年輕人,他們以舞臺為夢想,他們或是卡車司機、銀行柜員、鄉村教師、餐廳駐唱,或是離開故鄉的浪子,但他們的歌喉在某些時刻,宛如神跡。你不知道怎么有這么多年輕人,吃過難以言喻的辛苦,當他們將自己變成一架宇宙發聲器時,可以發出那讓人流淚的天籟。
我想起來了,我前面說的“某些遠距的、非貼近人類短暫時空所經驗的什么感受”是什么了,在這次的“姚貝娜”經驗之前,是幾年前,某次我曾聽臺灣音樂創作人雷光夏說起,她曾認識兩個不知道是比利時還是奧地利的玩音樂的哥們,他們架設了一種收音很靈敏的儀器,在山里或海邊截收那些我們肉眼看不到、太空中人造衛星的聲響。我問那是什么樣的聲音。她說:很有意思,很像深海中的鯨,寂寞的哀鳴。其實噗嚕噗嚕的,是某些老舊人造衛星的類似扇葉的零件,已那樣空轉幾十年的聲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