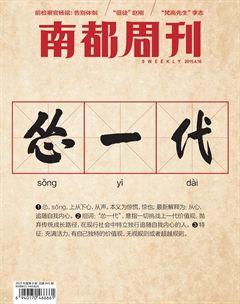自由亦有價
張海律
“慫”方式:背包旅行
居無定所,是已深度走訪60國的環球旅行者,是國際電影節采訪者及國內各大報章影評人。對他來說,在路上就是在上班,抓緊時間深啃世界。
最近通過一家英超俱樂部邀請,我在倫敦短暫跟了幾天媒體團。行程結束后,回國的回國,逗留的逗留。我屬于抓住一切機會玩個夠那種,原定只有5天的跟團考察行,早早被我拉長為可能大于58天的不列顛自由行,之所以說可能,是因為怕自己玩不夠,而將回程機票定為改簽成本最低的類型。新朋友們的微信群里開始直播各種最新采購信息,“攝政街的旗艦店得去看看,多買返稅高”,“Chole、Prada這些還是得去牛津旁邊的奧特萊斯Bicester”。看著他們圖片里滿大箱的圍巾、大衣和奶粉等戰利品,在布里斯托爾搖滾現場無所事事的我,插不上任何一句嘴。
這種不合群的自由自在,正是由于自己連續四年馬不停蹄獨行所致。它在把我的足跡帶到60多個國家,讓我的眼界極度開闊,閱歷和知識迅速豐富的同時,也制造著自私自我、物欲喪盡和審美疲勞等不可小覷的問題。
“好山好水好寂寞,好臟好亂好好玩”,如今,人們用這句調侃形容著國外和國內生活的巨大差異。就連我這樣只是走過而非經歷國外生活的旅行者,都覺得這句話非常準確、沒有夸張,更何況那些整日與綠草、奶牛為伴,并小心翼翼下載盜版電影的移民。
作為從來耐不住寂寞的多動癥患者,我絕對無法在一個與世隔絕的俊俏小村或波濤拍岸的壯闊海邊呆過三天以上,反而喜歡看到窮街陋巷里的婦女撕逼,聽到俱樂部現場的金屬咆哮、球場內外的球迷對罵、沒心沒肺的八卦葷段子,甚至更多“刺激的壞消息”。也因為沒心沒肺沒信仰,人生最不想去的旅游名勝包括:恒河邊的瑜伽圣地瓦拉納西、緬甸深山里的靈修道場,以及那個所謂幸福指數最高的國度—不丹,當那么多自覺不幸的癡男怨婦和被功名所困的人生贏家,鉚足勁想往仁波切那拱時,實在想不通這個規定游客每日最低消費的國家能有什么幸福可言。
讓內心聲音見鬼去吧,我需要熱鬧和躁動。可熱鬧源自集體,對于獨來獨往慣了的人,集體就只能是短暫存在的。于是,出乎身邊人預料的是,可能占我旅行總時間1%的跟團游,反倒成了記憶最深刻也最爽的旅行。其中既包括從國內一道出發逛上短暫一周的同業考察團,也包括路上萍水相逢并越發拉大的國際背包團。建個微信群,加幾個非死不可,唱一首披頭士的“I say Hello, You say Goodbye”,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是多么美好的人際距離啊,沒誰會跟你稱兄道弟,沒誰會找你借錢買房。
不過,我卻同時早早就懷念起上學時的集體主義。記憶中,那種榮辱與共的精神其實挺美好的。4X100米接力,因為自己失誤全盤皆輸時,我會號啕大哭;下廠學工,不顧午飯時間已到,非要搬完最后一堆材料,即便那也沒有額外獎勵。我知道這種美好感覺其實挺虛幻,可當意識到自由主義已經在自己身上取得壓倒性勝利時,就會變得非常懷念甚至美化過去的集體。
或許大學時應該把我丟到軍校,去學習紀律和自律?那樣的話,我肯定就不會這么瘋狂地看世界吧,應該對一份工作有點長性,對一家企業有點責任感吧。至于通過獨自旅行見到的世面,還遠不如一個終日需要與各種人際關系和政府部門打交道的老百姓豐富,而且,后面那類世面才是真實的。
微信群里說著的Chole、Prada、Burberry......我當然也都知道,甚至還曾深度探訪過安特衛普皇家藝術學院大名鼎鼎的時裝系、好萊塢明星在頒獎禮前選擇晚裝的圖書館,以及佛羅倫薩與鞋王菲拉格慕的關系史,卻從來沒激起我一丁點的購買欲。
物欲即便不來自形象或財富上的攀比心理,也或多或少與興趣愛好緊密相關。幸好,我喜歡任何事情都不會太投入,可以想見的最多一塊興趣投資,也就是被文藝“所害”后,一度撐滿屋子的DVD,即使是盜版,其價值也等于一輛便宜汽車了吧。不過,隨著越來越依賴網絡下載,這一塊的消費欲被迅速終結。
以往每到一個新的地方,我還曾會到售賣當地民族音樂的商鋪,買上十來張。四年前,成為旅行記者后,由于出國頻率越來越強,自覺沒時間在家添置設備好好欣賞后,就漸漸轉為無所謂多高音質要求的MP3聆聽者。隨著越走越上癮,以及大量出現遠超單位所能提供的出境機會,一走就三四個月不歸的我,就越發覺得實在沒必要往自己都很少住的那套出租屋里搬進什么東西,反正又不需要拿冰箱貼和特色工藝品,來向誰證明都到過些什么地方。加上從一開始就明確表態,絕不愿在漫漫長路上為自己增加負重,也就幾乎沒朋友跟我求代購了。
從巴黎到柏林,從薩格勒布到危地馬拉,那些個著名的城市市集我也會逛,也會特別喜歡那些漂亮而聰明的小玩意,但一點都不想將它們買斷、打包、海運后占有。吃點街邊特色的小吃就好,便宜又不用給小費。因此,當然也就有同學“恨鐵不成鋼”,認為我抓著那么一大把好機會不用,會做代購的話,早就財務自由了,不用像如今這般以失業狀態,到處求包養蹭吃蹭住,還同時自嘲又炫耀的叫嚷“沒尊嚴”。
總之,我在國人強大的海外購物消費力中,成了為數不多拖后腿的。其實,無論是物欲還是旅行欲,都一樣得花錢。這么四年的旅行下來,我有3/5的時間在路上,雖然沒記過賬,但除去各類工作或活動邀請外,自己花費的估計也得15萬左右,聽起來,應該也遠不如常規購物者們的消費力吧。
不過我相信,如若哪天我真跑煩跑膩,想要安居樂業(真希望我還能具備職業工作能力)了,就真會借著大幅減少的出國機會,去把以前喜歡的市集上那些漂亮東西搬回來。前提當然還有一個,得有錢!
昨天,在英格蘭西南部海港城市,一艘叫做皇家不列顛號(SS Great Britain)的19世紀汽船,在這個國家難得的晴空下,牢牢吸引住了我。我上上下下走遍金色的甲板、豪奢的餐廳、逼仄的三等艙、昏暗的機房,反復看著仿制的渦槳發動機和它行遍四大洋的歷史故事,并操弄著電影特效開發商打造的造船游戲。
而早前一天,剛離開牛津和巴斯的我,還不斷抱怨煩透了博物館、美術館、教堂以及任何一切的文化知識。參觀簡·奧斯汀那幢故居,也僅僅是因為這女作家和我同一天生日,而我還能電話里假借報道名義,免了門票,才進去聽著講解便昏昏睡去。至于圍成圈的喬治亞式建筑、景點前穿著維多利亞年代臃腫華服的職員、水果要分類擺放的精致下午茶、古羅馬浴池一淌不能玩的冷水,沿著大坡鋪開遠去的碧綠草地,都成了我這見多識廣雙眼里,“也就那么回事”的東西。
外人聽上去或許顯得有些嘚瑟,但這種“也就如此”的感覺,實在是因為走太多,看太多,又沒能就此將興趣集中到某一領域而造成的審美疲勞。從花兩個整天逛遍圣彼得堡冬宮,到一小時競走完成巴黎盧浮宮并拍下拍蒙娜麗莎的人海;從在土耳其帕姆卡萊初見古羅馬城池的“哇塞”,到走在古羅馬帝國核心斗獸場的煩躁;從雅典衛城看日落的愜意,到危地馬拉瑪雅金字塔前質問“這破積木算高度文明?”;從在科索沃和波黑抓緊機會挖掘當地人內戰和屠殺記憶,到美加灰狗大巴上戴起耳機低頭手機的不與人交流……我確實已經從饑渴求知,變得有些許反智和吝于交流。記得去年12月底,在凍雨不絕的德國北部地區,連續四天,我所居住的客棧都僅我一人,街上也連個鬼都見不到,那一刻,我真想立即改簽,飛回熱騰騰的火鍋里。
這么看來,不成為馬不停蹄的旅行者,也并非什么壞事。它確會留下很多遺憾,畢竟好多你覺得“以后有時間再去的地方”,會真的再沒時間去,但更會讓你變得珍惜每一處壯麗景致、每一個票價不菲的名人故居,會讓人覺得這世界真正好美!
確實,我經常被問你就這么玩一輩子嗎?就不想成家立業嗎?
立業確實不想,很早之前我就會在書店最顯眼的成功學柜架前納悶,人干嗎非得有一番事業啊?成家還是挺想,只不過當被提出“你總不能這么長時間沒個人影”時,就會開始在內心權衡利弊,想著還剩南美、大洋洲、西非沒去過,又不能只去個把星期,于是又不了了之了。其實,在路上玩個不停歇的中國姑娘,數量上遠比社會壓力大的男人多得多,她們中又不少竟出乎我意料的,有著幸福穩定的家庭,獲頒個什么年度旅行家獎時,老公會替其出面,“我老婆在伊朗玩著,這是她發來的感謝視頻。”
即便最終不能兩全其美如那些女玩家,估計也就偶爾在又一個空無人煙的異鄉憂傷一會兒,然后告訴關心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人一輩子就這么短,活自私點也沒什么。”

攝影_劉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