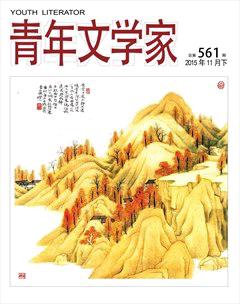試以巴赫金的復調理論解讀《罪與罰》
劉譯涵
摘 ?要:20世紀著名文論家巴赫金提出了復調小說的理論,指出復調小說的含義是“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真正的復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中,就鮮明地表現出了不論從結構還是人物形象以及人物語言之間的復調性。本文試圖以巴赫金的復調理論來解讀《罪與罰》,并且分別從歷時性和共時性兩個方面來探究作者是如何巧妙地安排這種復調式的情節和人物的。
關鍵詞:復調小說;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對位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33-0-02
20世紀蘇聯文論家巴赫金,在其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中,提出了復調理論,深受學術界贊譽。由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藝術也被定義為具有復調結構的小說。復調,在音樂上是指不同聲部的互相獨立而又互相應和,共同表現一個主題。不論有多少旋律,總能在每個階段保持完美的和聲而又同時各自獨立發展。巴赫金借用音樂中的術語,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命名為復調小說[1]。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每個人物都在思想觀點上自成權威,卓然獨立,同時又與其他人物的思想形成對比和共鳴。主人公的語言不再是傳統的獨白型小說中的代表作者觀點的聲音,而成為了一個個具有完整自足性的個體。這種美學觀尤其體現在小說《罪與罰》中。
一、主要人物形象的共時性分析
小說中的主要人物是拉斯科爾尼科夫、馬爾美拉多夫和索尼婭。這三個主要人物就像賦格曲的三個旋律主線,缺一不可。在拉斯科爾尼科夫,其特點是一種帶著青年大學生的思考、懷疑、沖動而又單純的主線,他始終遵循這個特點,從頭到尾都像一個中提琴一般時而高亢時而低沉,時而激越時而滯鈍,但這種基本色彩沒有變化,他的行動貫穿了整部作品,給整部作品定調。馬爾美拉多夫就像低聲部的旋律,他的家庭的衰敗、他的酗酒、他女兒的不幸經歷使得這個人物始終是憂郁、悲憤、痛苦、低沉,這個人物時而在情節線中占主導地位,如開頭第一章他在酒館里半醉時痛斥自己的大段獨白;時而又沉入主要情節之下,給整部作品帶來一種濃郁的低沉氛圍,而不論他是在明線還是暗線,他的聲音始終是在獨立地演奏著的,甚至到他死后,也是在以一種回蕩著的悲劇氣氛影響著主題的發展。索尼婭是高聲部,她的美德、基督教犧牲精神超乎世俗,身世的凄慘與信念的高昂是她的主要音型,她就像是高聲部的小提琴,在必要時刻、情節發展到高潮時高亢而激越地奏出主題,此時她在三個聲部中占據了最明顯、最主要的地位,她的光輝照徹了其他一切因素,使得其他旋律都在她的這個旋律之下形成輔助。這三個聲音是這部小說的主要內容,他們就構成了整部小說的主要旋律。其余的人物,是推動主旋律前進的不同的刺激性因素。拉斯科爾尼科夫在面對這些人物時的態度和感情,都是受來自這兩個低音和高音旋律的影響。當他受到來自馬爾美拉多夫的影響時,他是憤世嫉俗的,仇恨丑惡現實的;當他受到來自索尼婭的向善的影響時,他內心中向善的一面又被激發,整個作品的旋律也開始向善了。這三個人物不論在共時的空間對比上還是歷時的情節發展上都是以復調音樂般的精準對位來互相對話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一切莫不歸結于對話,歸結于對話式的對立,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對話才是目的[2]。
二、歷時性復調的情節的織體
“織體”一詞是指音樂作品中各音縱向結合和橫向進行的結構形式。20世紀之后,織體一詞被廣泛地引進入文學解讀中來,羅蘭-巴爾特在他的文本理論中,把文本稱為“能指的織體”[3]。下文試圖以文本構成的織體的形式解析《罪與罰》的情節結構。
2.1 激怒地開端
當主要人物的行動開始行進時,是怎樣互相應和而又互相影響呢?在賦格曲中,一般會有一個音型先行奏出主題,其次,第二個旋律線出現,與之應和或模仿它行進,繼而,第三個,第四個。這部小說最先出現的旋律線,自然是拉斯科爾尼科夫。他的出現,一開頭就先定下了整部作品的調子,這是一個窮困潦倒的大學生,為了交不起學費已經輟學兩個月,他的衣衫襤褸,對整個世界產生了懷疑,看到的一切無不是敗壞與墮落;但是他在要實行自己的殺人計劃,準備沖破這個世俗社會的規則時,還是猶豫的,自我懷疑的,這就形成了他的形象的內在對話性:一方面是幾乎難以忍受的赤貧與生存的壓力迫使他要去搶劫,另一方面是他的天然存在的良心與道德感,使得他難以為了一種尼采哲學而打破社會規范。所以,這個人物在出場時就一直在自我對話,而這種自我對話造成了一種平衡,即雖然想犯罪,但又在自我勸說的兩個力量互相制約的平衡,但這只是暫時的、帶著巨大不安的表面上的平衡。這個人物的設置正好像是一個賦格曲的主題,雖然是自足的、但也帶著不穩定性,只有這種不穩定性才是巨大的前進、演變的潛能,這樣才能使旋律在得到其他的動機的出發之后繼續前進并不斷變化。拉斯科爾尼科夫在這種自我懷疑的不穩定的平衡中去找了放高利貸的老太婆,之后似乎要對自己準備進行的犯罪感到后悔并準備停止這個計劃;但是這時,第二個旋律出現了,這就是馬爾美拉多夫。在酒館中喝醉后對拉傾訴的馬爾美拉多夫,帶著重大的痛苦而徹底的沉淪,以不同的方式但是遵守同樣的主題,重復了拉斯科爾尼科夫的內心中開場就存在的懷疑與沖動,仇恨與傾向于破壞的一方面,強烈刺激了第一個旋律,使得他在暫時的從屬位置之后,再回到主要線索時,變成了有著更堅定的想要突破這個悲慘社會的意志的個體。而馬爾美在進行自己的陳述時,已經帶出了第三個旋律的影子,這就是索尼婭。但是這個旋律在此時還是隱藏的,是通過他人視角交代的,是模糊的回響,這種模糊的回響,直到索尼婭真正出場,才變成堅定的切實的旋律,影響著主要情節的發展前進。
如此,在全書第一章中,三個旋律都已出現,并且以第一個旋律為主線,第二個旋律經過短暫獨白,在形式上對第一旋律進行模仿并加深后,成為進入輔線,并出現第三個旋律的模糊回響,為互相刺激、互相模仿的情節方式,構成了這部作品中的主題陳述。從第二章開始,三個旋律就在主題動機之上,互相影響,互相作用,不斷發展演進,直到最后得到最終的平衡。
2.2 回旋地演進
在第二章中,出現了第一和第二旋律的奇妙的對稱:當拉斯科爾尼科夫為自己的罪行感到后悔,想要去警察局自首時,就好像一個旋律在觸到底部之后緩慢地上升;而這時第二旋律重又出現,并重重地下降到底——這就是馬爾美拉多夫的死,對第一旋律的上升起到了一種往回拉的力,使得這個旋律繼續保持在既要上升又遲滯的地步,一種新的內在對話出現:拉斯科爾尼科夫內心感到痛苦,本能的道德感使他驚慌失措,不由自主地要去做些事情來彌補這種過失,去犯罪現場跟人糾纏,只是一種方式。但是即使去懺悔,又有誰能有這個能力去赦免他呢?這個世界都是一片悲慘渾濁,他應該向誰懺悔?誰有這個至高的道德評判的權力?但這個他內心的聲音被另一個鮮明的聲音打斷了,精彩的地方正是在馬爾美拉多夫不幸遭遇車禍的時候,第三個旋律以奇異的高亢的凄慘音調的正式出現,瞬間與其他兩個旋律形成對照,并與其他所有內容之間形成一種張力。這個精彩的對位就是索尼婭的出現。當兩個主旋律,一個在上升,一個在下降,一個在內心懺悔,一個遇到了車禍快要死的時候,第三個精彩的、閃亮的旋律出現,它的出場瞬間撮住了所有的旋律,并如畫龍點睛一般以最鮮明地方式點出了整部書中的悲哀、凄慘的主題,帶著最輝煌的音響,和最明亮的色彩,以至于索尼婭的出場簡直是一種經典的戲劇場景。這個時候,第一旋律,拉斯科爾尼科夫的懺悔和恐慌被壓抑了,出現了第二和第三旋律的對照,一個是痛苦復雜的、自甘沉淪的,一個是內心凄哀的、尖銳悲厲的;這兩個旋律的合奏形成了一種新的效果,當作父親的在瀕死時刻看到那個不得不去出賣自身的女兒的樣子時,所有的痛苦都在瞬間爆發,他痛苦地喊了一聲,“索尼婭,女兒!原諒我!”就死去,死在了這個命運凄涼的女子懷中,這種人間慘景,使得拉斯科爾尼科夫對現實的一切壓迫和剝削仇恨到了極點,他用自己的錢給這家人作喪葬費之后,內心感到一陣輕松和堅定,因為他目睹這一目慘景之后,已經不再為殺死那些剝削人的高利貸者感到后悔,相反,他更加肯定了這個世界上,沒有什么人能夠有權評判他的行為,因為在他看來統治者和有錢人是造成這種悲劇的根源。此時他對社會的不公已經憤怒到了極點,對被殺死高利貸者也不再憐憫;此后他這條線中,是一種反抗社會一切規范、并在與調查他的人斗智過程中享受一種樂趣的傾向。
2.3 平靜地結束
在此之后,第三章至第七章,有斯維德里蓋洛夫的享樂主義生活觀,有盧任的自私自利的獨白,還有拉祖米欣對他妹妹的真誠追求,還有盧任為了陷害索尼婭在葬禮之后的戲劇化的沖突;在這紛繁的眾聲雜語中,占據主要地位的還是拉斯科爾尼科夫的尼采主義,超凡脫俗的自我定義,他在與這三個人對話時,都不改他本身那種內心中對外界的反抗,所以在他這個旋律與其他旋律相互作用時,都是一種類似他們在獨白而其實是第一旋律作輔助而其他旋律的半獨白。這些輔線之上,主要的第一旋律沒有什么變化,直到第三個旋律,即索尼婭又一次出現,并開始陳述它的基督教救贖思想,才對第一旋律造成影響,而這種懺悔、贖罪與寬容他人的意識,又在索尼婭當眾受到盧任的栽贓陷害,被誣陷和侮辱之后,所以這種情境之下,索尼婭本質中的善的因素被格外地凸現出來,形成一種奇異的至高的精神力量,這種力量震撼讀著的心靈,似乎在閱讀中感受到了凈化。在索尼婭為拉斯科爾尼科夫朗誦圣經的場景中,“一個殺人犯和一個妓女,在燭光下讀著這樣一本書,”[4]似乎有著某種神秘的象征意義。在基督教中,有著深厚的原罪、救贖意識,圣經上記載著這樣的故事:抹大拉的瑪麗亞是一個懺悔的妓女,她見到耶穌時,用自己的眼淚為耶穌洗腳,用黑而密的頭發為耶穌擦干。眾圣徒都斥責她,唯有耶穌說,她的罪已免了,因為她內心的愛多。這個場景,似乎就是在為這個故事做出一種情景的復現與呼應。它暗示著作者的思想:只要潛心贖罪,在內心有贖罪悔過的意識,就會被赦免,而這個能夠赦免他們的機構,不是世俗的警察局或者流放的刑罰,而是內心對宗教的虔誠。在此場景之后,整部作品的旋律開始轉向上升,是走向最后和諧與平衡的起點,并最終以拉和索尼婭一起流放并開始在流放地形成新的、向善的生活狀態結束。
綜上,就是這部作品的共時性與歷時性復調分析。巴赫金認為,在復調小說中,多重聲音的聚合與對話本身就是目的。如果說這本書的中心思想始終是潛藏在文本之下,似乎若隱若現,那就是作者刻意為之,他的小說只服從藝術結構的統一性,而不是思想觀點的一致性,這種藝術結構揭示的又恰恰是不同意識的對話性和矛盾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構造的精彩絕倫的復調織體中,讀者不由地參與進了一場悲喜交織的大型對話,我們既是看客又猶然已經置身在戲臺之上;這就已經達到了復調小說的預想的審美境界。
參考文獻:
[1]楊春時,簡圣宇:巴赫金復調小說的主體間性世界,東南學術, 2011,2.
[2]巴赫金 著,白春仁,顧亞玲譯: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北京:三聯書店,1988,344.
[3]張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創作藝術的“聚合性”,外國文學研究,2010,5.
[4]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譯:罪與罰,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