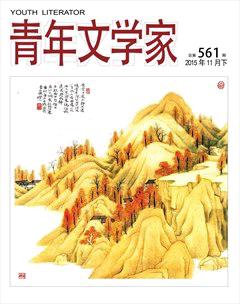淺談施特勞斯的“審美烏托邦”的意義
摘 ?要:列奧·施特勞斯在20世紀重提古典政治哲學“古今之爭”,認為當下時代,真正的政治哲學已經不復存在——政治哲學被科學實證主義以及歷史相對主義心照不宣地謀殺了。他倡導應重新回到以“自然正當”為價值準則的古希臘哲學之中。那么,科學主義和歷史主義真的如施特勞斯所言,將我們帶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了嗎?以“自然正當”為基礎的古典政治哲學真如施氏所言能夠拯救現代性嗎?施特勞斯所構建的“審美烏托邦”對當下中國的發展有沒有,或者有怎樣的借鑒意義呢?這就是本文要探討的內容。
關鍵詞:列奧·施特勞斯;自然正當;歷史主義;科學主義;審美烏托邦
作者簡介:李曉瓊(1990-),女,漢族,山西陽泉人,四川大學工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中圖分類號]:B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33--02
無論從思想學術的意義還是社會政治的影響來看,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 1899-1973)及其創立的政治哲學學派都是當代西方最獨特的一個現象。施特勞斯是在20世紀重提“古今之爭”的以為重要代表,正如邁爾所說,在20世紀的這人當中,“沒有誰像他那樣全身心地投入這一問題。”[1]在施特勞斯看來,“現代性的危機原本是現代政治哲學的危機,而現代政治哲學的危機則源于自然正當觀念的轉變”,也就是說,正是因為natural right由古典自然正當蛻變為現代自然權利(天賦人權)后,現代性的危機才得以從西方文化的最深處向外逐漸爆發,虛無主義也才得以徹底沖破現代西方社會的最后防線,導致了“現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夠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 [2]的結局。
一、科學主義和歷史主義——“自然正當”的謀害者
施特勞斯提出,正是“科學和歷史,現代世界的兩大力量,最終成功地毀滅了政治哲學存在的可能性本身。”[3]
《什么是政治哲學》中提到,科學的社會科學是不能夠做出價值判斷的,因而必須徹底避免價值判斷,對于科學家來說,他們所從事的學科的唯一職能,也唯有他們能夠提供的只能就是對任何社會目標的可行手段提供恰切的知識,施特勞斯諷刺這種“價值無涉的、倫理中立的”科學主義為“道德遲鈍是科學分析的必要條件”,對于任何目標無動于衷、漫無目的、隨波逐流必然導致虛無主義。
而歷史主義認為,所有的人類思想都是歷史性的,所有的普遍性努力都將歸于徒勞,人類對于任何永恒性失誤的把握都是無能為力的;某一社會科學的各種價值,取決于學科所從屬的社會,也就是取決于活的歷史,而這樣最終也必然會導致一般意義上的現代科學的相對化。所以,“歷史主義的頂峰就是虛無主義”。
科學實證主義及其轉化后的歷史相對主義以其“價值無涉”的中立姿態來輕視永久的、整全的、終極的價值,最終引致始于了1933年的人類的浩劫。“1933年最重大的事件不如說似乎已經證明——人無法拋開好社會的問題,人無法通過聽從歷史或任何其他不同于其他自身的理性的力量來擺脫回答這一問題的責任。”[4]
二、幾點有關“自然正當”的悖論
施特勞斯的思想,尤其是現代性批判思想的緣由,很大程度上來自于魏瑪民主及兩次世界大戰的直接經驗。他親眼見證了魏瑪民國的自由民主政制從繁榮到覆滅,親眼目睹了可以不問好壞、為任何政制服務的價值中立的科學主義,和蛻化為狹隘民族主義的歷史相對主義共同鑄就的納粹,給整個文明帶來的血腥和浩劫。鑒于其特殊的身份和生活背景,對其理論思想做仔細的探究,筆者認為,施特勞斯思想中有部分思考仍值得商榷。
(一)歷史主義究竟是相對主義還是絕對主義?
施特勞斯力證“頂峰即是虛無”的歷史主義乃完全的相對主義。而波普爾在《歷史主義的貧困》中卻稱歷史主義存在一種非相對性的傾向,特別是表現在歷史主義的專斷論上:這種專斷論認為“歷史的意義一般是可以或者應該以某種法則或規律加以解釋的;同時,每一種世界觀也都是歷史地被限定的和制約的。”[5]也就是說,在波普爾那里,歷史主義首先意味著一種歷史決定論,其根本的內涵在于強調歷史的發展本身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歷史演進過程本身存在著一種自身發展的舊在規律。所以說,在波普爾看來,歷史主義不是相對的而恰恰是絕對的。事實上,人類社會的發展是由諸多偶然性構成的,歷史的發展具有強烈的不確定性,因而歷史的發展形態也可能是多元的,不存在任何歷史規律,也不存在任何歷史規律所制約的終極性的理想圖景。
而且,在歐洲思想史中,正是早期的歷史主義糾正了啟蒙運動中的重視普世理性而忽視不同民族文化獨特性的偏頗,為人類普世理想的實現奠定了多樣性的民族文化之根。伯林在談到歐洲早期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維柯和赫爾德時指出,他們并非時人所誤解的文化相對主義者,而是真正的文化多元主義者。只是到了費希特之后,歷史主義開始保守化,逐漸與國家權力聯手。
(二)重回古典“自然正當”——這一“審美烏托邦”能否證成?
在施特勞斯的視域中,柏拉圖所構建的“理想國”中五種制度之首的“哲人王”式的君主制度無疑是最符合“自然正當”也是最為完善的政治制度,然而,這一看似美好的制度卻僅僅是只能存在于理想之中的“審美烏托邦”:哲人何以成為統治者以及如何保全其統治地位的延續性(也就是如何避免哲人的腐化墮落的問題)?護衛者又怎樣能夠不崇尚武力和榮譽而“改旗易幟”,將制度顛覆為尚武的榮譽制度或僭主制度(希特勒帝國為這一江山的易主提供了最佳范例)?怎樣防止被統治者向往所謂的民主和自由而使整個社會淪為一種“暴民的統治”?這些都是這個“審美烏托邦”所無法解決的癥結。
此外,哲人因為意識到,“達到政治生活的終極目的不可能通過政治生活,而只能通過一種獻身于沉思和哲學的生活”[6]而不愿意下降到洞穴中去,那其成為哲人王參與統治就往往是被迫的,哲人自身成為哲人王的可能性極小。可是,要想實現那種“各盡所能、各司其職”的政治局面又必須要哲人分配什么樣的人適合何種位置,“智者”的缺席必然無法實現人盡其才,真正的正義也就無法,在城邦中實現。
因此,蘇格拉底才會說是要“用詞句創造一個善的國家。”也就是說,理想城邦總是言辭性的而非現實中的:政治哲學的理論探究不一定導致現實中出現理想形態的政治架構。
三、施特勞斯學說在中國究竟應該被怎樣看待
嚴格來講,施特勞斯的“復古”傾向正是著意于古典“自然正當”理論的引入,通過對古典政治理性主義的重新審視,而為現代性進程中的虛無主義問題的化解提供一定的思路,也就是說,施特勞斯引入古典政治哲學并不是試圖要否定現代性,而是試圖要改良現代性、拯救現代性。
施特勞斯的古典政治哲學自1985年進入中國,已整整二十年。作為中國引入的解救現代中國危機的“良藥”之一,施特勞斯對西方傳統中啟示與理性沖突的解釋,也確實讓我們認識到現代理性主義的問題。哈佛大學政府系哈維·曼斯菲爾德教授在2008年訪問上海時驚異于中國對施特勞斯如此感興趣,他對此的解釋是:中國的民族主義使得施特勞斯思想的影響如此巨大。這種說法很顯然是有失公允的。理論構建的積極意義固然存在,但作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眾多西方“主義”話語之一,施特勞斯思想在解決中國問題時也并非那樣有效。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文化”與“文明”之間的沖突?
在近代德語中,文明(Zivilisation)意味著屬于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或本質文化,而文化(Kultur)則強調民族之間的差異性和族群特征。文明的表現可以是全方位的,可以是物質、技術、制度,也可以是宗教或哲學,而文化一定是精神形態的,文化指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存在價值,而是某些特定的民族或族群創造的價值。施特勞斯從其古典主義的視野出發,將古典文化特別是以“自然正當”為基礎的希臘文明作為人類的普世文明,那么,推行古希臘“自然正當”理念或多或少都會把中國文化或文明視為一個單一共同體內的特殊“文化”:文明擁有永恒的原則,屬于全人類,放之四海而皆準;而文化卻是歷史主義的,僅僅屬于特定的民族或族群,因時代的變遷而異。而施特勞斯所欲的,即使不是普世文明代替特殊文化,也是要對特殊文化進行改良而臻于至善。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化保守主義雖然試圖追求中國特色的現代性,卻預設了“西方等于普遍,中國等于特殊”的二元對立立場,試圖以中華文化對抗普世文明。以上觀點,筆者認為即使沒有墜入文化保守主義立場之嫌,至少也給我們以警戒:若不加思考地照搬施氏學說,只學皮毛不見其里,盲目“復古”而不懂其良苦用心的道路是絕對行不通的。
(二)“自然正當”的古典城邦與儒家文化的多民族國家之間的差異
古典政治哲學的主題是城邦,城邦中的兩個最重要的原則是自由(公共精神)和文明(藝術和科學的高度發展)。施特勞斯認為,直至18世紀,一些最杰出的政治哲人仍然及其正當地偏愛城邦,而非16世紀就已經出現的現代國家。將適用于建立寥寥數千人的城邦的規則,安置于建構幅員遼闊的多民族國家的難度可想而知。而且,如果說“好”的標準等同于“古老”的,那么“古”的就是“好”的,而“最古”(上古、太古)就是“最好”的,那么,儒家孔子以周代禮樂文明/政教為藍本而創制的儒家理想的政治秩序是不是也是最好的秩序呢?這是值得懷疑的。縱然儒家思想體現出超前智慧與高明氣象,仍有其內在的機構性的思想癥結,比如說,儒家企圖把美學、政治、文化問題一并解決的“大局觀”勢必忽視細節,最終也必然導致儒家失去活力;再像儒家學說中的“圣王”理念蘊含的“王者應有圣德”與“圣人應為王者”的崇高期許又與柏拉圖憧憬的“哲人王”政制何其類似。簡言之,古代儒家的“圣王”政制與柏拉圖的“哲人王”政制都是構想的“審美烏托邦”而鮮有實際操作價值。
劉小楓在《施特勞斯與中國:古典心性的相逢》中提出的觀點無疑更具有參考價值:我們可以借施特勞斯的古典學問學會重新珍視中國傳統。確實是這樣。在經歷長達一個半世紀的開放之后,西方的各種文明傳統,從資本主義制度的理性化、自由主義的理念與價值,乃至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都已經緩慢地內化為中國自身的現代話語和歷史實踐,中國早已風化為有待激活的思想碎片,施氏理論的進入,恰好可以作為這種激活手段。
注釋:
[1]邁爾. 古今之爭中的核心問題——施米特學說與施特勞斯的論題[M]. 林國基等譯. 北京: 華夏出版社,2004:198.
[2]施特勞斯. 現代性的三次浪潮[A]. 劉小楓編. 蘇格拉底問題與現代性——施特勞斯演講與論文集:卷二[C]. 北京: 華夏出版社, 2008:32.
[3]施特勞斯. 什么是政治哲學[M]. 李世祥等譯. 北京: 華夏出版社, 2014.9.
[4]施特勞斯.什么是政治哲學[M]. 李世祥等譯. 北京: 華夏出版社, 2014.19.
[5]何兆武. 評波普爾和他的貧困[A]. 見:波普爾.歷史主義貧困[C]. 何林, 趙平譯.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87:2.
[6]施特勞斯. 什么是政治哲學[M]. 李世祥等譯. 北京: 華夏出版社, 2014.78.
參考文獻:
[1]施特勞斯. 什么是政治哲學[M]. 李世祥等譯. 北京: 華夏出版社, 2014.9.
[2]伯林. 自由論[M]. 胡傳勝譯. 南京: 譯林出版社,2010.58.
[3]邁爾. 古今之爭中的核心問題——施米特學說與施特勞斯的論題[M]. 林國基等譯. 北京: 華夏出版社,2004: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