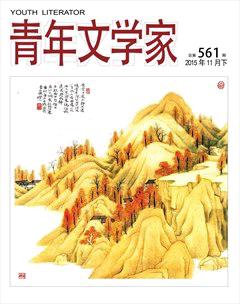康有為書學思想的心理史學解讀
魏愛平
摘 ?要:根據心理史學相關理論證明,一個人的思想傾向可以由他扮演的社會角色、社會行為、個性特點等一些外部和內部的特征顯現。而且這些外部和內部的特征需要在行為主體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中才能顯示出更深層的意義。
關鍵詞:康有為;書學思想;社會意識;行為目的
[中圖分類號]:B8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33--02
書學即包含了形與質的自然意識,也蘊含了書家社會意識的心靈體悟。在中國近代史上,康有為是一位彪炳史冊、成就矚目的重要人物。他不但是近代中國著名的政治家、杰出的啟蒙思想家,也是聲名顯赫的書學理論家。康有為的書學思想體現了遠見卓識的政治眼光和獨特的藝術品質。他在“尊碑”口號下發展了中國書學的雄強之風,開啟了書學理論的新格局。
心理史學是將心理學和歷史學結合起來的一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是利用現代西方心理學理論、方法、手段對各種歷史人物和歷史現象做出解釋的一種新史學方法。心理史學的研究特點是借助心理分析方法從內部研究歷史人物的社會心理和行為特點,從而了解歷史人物的行為目的和行為結果。
根據心理史學的相關理論介紹,在社會歷史文化變遷的過程中存在“邊際人”的現象。所謂“邊際人”是指處于兩種以上文化或群體之間,其個性具有中間性和邊際性的人們。“邊際人”在時空上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共時態邊際人和歷時態邊際人。共時態邊際人指的是由于出訪、留學、國際聯姻、移民等原因,具有兩種不同文化、制度、生活經歷的人。歷時態邊際人是指經歷社會動蕩或大變革時期的人,具有這樣經歷的人一部分會成為時代前進的弄潮兒,成為推動歷史的先驅人物。雖然這些人內心存有現在價值和原有價值觀念的沖突,但他們往往能更加清楚、客觀、理智的認識和對待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差異,因為他們基本超越了本土文化,能站在更高的視角看問題。康有為就屬于中國變革時期的歷時態邊際人,而且是時代浪尖上的弄潮兒;又因為他海外16年逃亡游歷的生活經歷,使他具備了共時態邊際人的特點。同時根據心理史學相關理論證明,一個人的思想傾向可以由他的社會角色、社會行為、個性特點等一些外部和內部的特征顯現。而且這些外部和內部的特征需要在行為主體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中才能顯示出更深層的意義。所以用心理史學的相關理論研究康有為的書學思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中國儒家思想為中國讀書人的人生構建了“士人——君子——圣賢——仁(道)”的修養之路,這也正是中國讀書人自我超越、自我實現的理想之路。根植于傳統文化,飽讀儒家經典的康有為,其自我意識的形成和人生目標的確立都離不開儒家“經世致用”的終極目標。“內圣外王、經營天下”的自我實現必將是康有為的生命意義和人格理想的最高境界。所以康有為確立了以經營天下為己任的行為動機、 “思以易天下”的行為方向。這樣的行為動機和行為方向時刻提醒著康有為應擔負起天下興亡的責任和使命,成為他一生行追求的內部驅動力,尤其是在他的書學思想中得到充分體現。
早年的康有為在形成經世致用自我意識之后,確立了入仕為官的行為動機,在這一行為動機的影響下,康有為只將書法作為入仕為官的“敲門磚”,所以他早年的書學思想是順應時風的帖學思想。在維新變法時期,康有為確立了維新變法的行為動機之后,他的書學思想轉變為尊碑抑帖求變尚雄的書學觀。海外游歷期間,康有為的行為動機是參照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特長之處,彌補和變革晚清社會制度的不足和弊端,這時他的書學思想表現為融碑入帖的書學觀點。天游化人時期康有為的自我意識表現為脫離凡塵的理想狀態,而他此時的書學思想同樣表現為一種“兼容并包、眾美皆備”的理想狀態。由此可見。康有為一生書學觀點的變化完全依附于其政治思想的行為方向和行為動機,所以康有為的書學觀點其實是都帶有未影射時政的歷史痕跡。
1888年,中法戰爭爆發,清政府竟然不敗而言敗,列強競相瓜分我國領土。康有為警覺中國若不維新圖強,即將面臨亡國之危,于是不顧自己身份懸殊,毅然寫下了《為國事危蹙祖陵奇變請下詔罪已及時圖治折》,也就是《上清帝第一書》。他指出了當時中國所處的危機形勢,給清政府提出了要“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張,并要求清政府通過采用他的方法以達到變法圖強的目的。也就是從這件事開始,康有為正式以一個政治家的身份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臺。但是由于頑固勢力的阻撓,這封“布衣上書”并未能使光緒皇帝得見。康有為第一次上書的失敗,使他清楚地認識到在祖宗之法不可違的環境下,變法時機還未成熟。他作為一介布衣,人微言輕,直接上書皇帝,本身就是一件驚世駭俗的事情,要想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成功實現自己變法的理想,必須要從長計議。所以此時的康有為在好友的勸說下隱居在北京宣武門外南海會館之“七樹堂”汗漫舫中,閉門謝客,潛心寫作《廣藝舟雙楫》這本使他蜚聲書壇的理論著作。
康有為在書論中寫道:“詩以言志,何事律則欲諧?文以載道,胡為辭則欲巧?蓋凡立一意,必有精粗,凡營一室,必有深淺。此天理之自然,匪人為之好事。楊子云日:‘斷木為綦,抗革為鞠,皆有法焉。而況書乎……吾既不為時用,其他非所宜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因搜書論,略為引申。蒙子臨池,或為識途之助;若告達識,則吾豈敢?”。
既然詩可以言志、文可以載道,那么書學為什么不能表達變法思想呢?由此幾段話可以看到康有為此時寫書論的行為動機之所在了。因為無論是康有為的自我意識和行為動機還是他的性格特點,詩書畫印都不會是他的志趣所歸。“治安一事知難上,只是江湖心未灰”退而研究書學理論,并非是其苦悶無事消遣時光。雖然書畫金石類的“雕蟲小技”完全不是康有為的旨趣所在,但是書學恰是一種不遭文人忌諱卻又會被文人關注的一門“小技”,利用這一 “小技”思考和闡述他的政治大道,不僅可以委婉的申訴自己的政治意圖,還可以引起文人權貴的注意起到嘩眾取寵的作用。
康有為總結的關于碑的優點絕大部分都與雄強有力、氣勢壯闊有關,碑的這些特點剛好和清代的帖學書風軟滑無力、柔媚艷俗形成鮮明對比。我們來想一下,當初促使康有為維新變法這一社會動機的根本原因是他看到清政府積弱積貧的弊政致使中國任人宰割。正是這種“弱極”的現狀,使康有為樹立了“立國自強,維新變法”的社會意識。所以他提倡“雄強茂密”鄙視“纖巧柔弱”的弦外之音就不言自明了。康有為明顯把書法與振奮民族精神、變法自強、救國救民的政治理想聯系在了一起。康有為在書論中攻擊帖學的頹靡書風暗射當時腐朽沒落的官僚統治。
康有為傾其一生的精力在尋找和研究一個能使體系即將崩潰,面臨存續危機的封建王朝順利平穩地轉換為一個富強、文明的國度的絕世妙方。這也是他經世致用自我意識的最終歸宿。所以康有為的書學理論注定會帶著一種“自我實現”的愿望和動機。熊秉明先生曾說,書法具有一種純美的魔力和號召力,它具有煽動性和振聾發聵的鞭策作用。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書學思想其實是一種曲折隱晦的反抗呼號。康有為清楚地知道書風背后的強大支撐物是什么,書學有著其他藝術形式所不具備的非凡能力,因為書法自誕生之時起就與政治文化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那么康有為為什么選擇以書學思想為媒介來闡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呢?
首先,康有為雖有滿腹經綸,但是因為他自小不喜歡八股文,所以在求仕的過程中屢試不中。康有為十四、十五歲,兩次應童子試,都落榜了,并且一直都沒有得到應鄉試的資格。直到其祖父康贊修在連州抗治水災遇難后,朝廷才因其祖父賑災有功,而破格給了康有為鄉試的資格,但這次康有為仍是以落地告終。“十九歲……是年應鄉試不售,憤學業無成。”再到后來上書不達,變法失敗的種種政治受挫經歷使康有為始終沒找到一個“圣人”與仕途之間的平衡點。這種矛盾的心態使康有為很難完成理想的“自我同一感”。這給康有為的心理帶來極度焦慮的情感體驗,而且這些焦慮又無法直接發泄。這些受抑制的情感既然存在,就必然要通過一種自認為合理的方式發泄出去。恰在此時他卻在書風變換的空氣里找到了自己政治抱負的方向感,所以及時地抓住這一契機舒展自己的政治大道便順理成章。
其次,書學理論是康有為所熟悉并頗有心得的藝術形式。因為他從11歲就開始在祖父的嚴格要求下,遍臨法帖,臨池之功頗為深厚。再到后來拜入朱九江門下,為了應考求仕,更是苦練書法。尤其是朱九江先生是當時嶺南有名的書家,對康有為耳提面命,從執筆教起,康有為在他的指導下耳濡目染,心摹手追,刻苦練習。所以康有為的書學功底不是一日之功可達的。有這樣的經歷和心得,康有為自然可以游刃有余的運書學理論于其思想之中。
第三,康有為認為藝術應該“上感國變,中傷種族,下哀民生”,藝術的發展與文化和時代的發展是休戚相關的。所以,以書法言時政,容易為世人接受且順理成章。這一行為方式正好秉承了中國 “文以載道”的儒家思想傳統。所以康有為設計了以書學的力量來感化和改變國民性情的藝術功能模式,以此來達到變革社會政治的目的。
基于以上三個原因,康有為導演以書學“微言”政治變革的歷史劇就不足為奇了。
既然書法思想只是康有為政治抱負的工具,那么,他又怎么會成為一代書法大家的呢?其實康有為之所以能成為書學大家是有其特定原因的:首先康有為具有扎實的帖學基礎;其次康有為是一位學富五車的大學問家,具有一流的融匯貫通能力;第三是康有為是在順應了書學發展的歷史潮流基礎上,以他遠見卓識的政治氣魄和非凡能力使碑學發展點石成金的。
所以當代的書家要理智的對待康有為的書論和書法審美觀點。有所選擇的借鑒和利用康有為的書學觀點和書法技法。不要良莠不分的一概拿來,或者盲目信奉,以防在學書道路上走入極端或白費精力。比如現在書壇上的一些學碑人士,盲目崇拜康有為的“尊碑抑帖”觀點,認為帖學浮漂,沒有力度,缺乏陽剛之氣。在學書過程中杜絕歐、顏、柳、趙甚至羲、獻的書體,只以碑版書體為審美標準,哪怕是窮鄉女兒造像的碑刻也奉為圭皋。這就是走入了極端,失去了學書的根本。再比如康有為的書論里力求出新,就有一些書家為了追求個性而故意筆畫歪斜、夸張字體間的疏密層次,甚至以丑、怪為出新標準。這就脫離了書學大道,而陷入了過于張揚自己的小道。清代文學家楊軍曾說“小道數載可成,大道千古無一”。所以對書法審美的追求應以中國的文化大背景為前提,不管寫碑還是寫帖都要以體現出中國五千年文明的大氣息為實踐和欣賞的最高境界。
參考文獻:
[1]沙蓮香.社會心理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2]章志光.社會心理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3]周光慶.中國讀書人的理想人格[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4][美]馬斯洛著,許金聲等譯. 動機與人格[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5]馬洪林.康有為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6]康有為著,崔爾平校注.廣藝舟雙楫注[M].上海 :上海書畫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