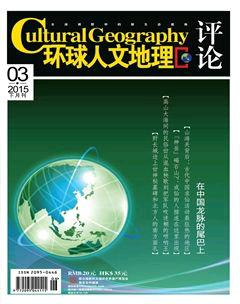德國設計之旅
湯博深
2014年夏末,我有幸參加歐洲景觀設計聯盟的暑期課程——一次以“Running out of land”為主題的workshop。這次課程把重點放在了解決德國北部Middle Ammerland地區的土地問題。
Middle Ammerland位于Lower Saxony州,人口約70500,面積422.5平方公里。這里的主要產業大部分為第一產業,種植業,苗圃,養殖業和采掘業,旅游業和其他投資有很多都是基于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公園式景觀”。這樣的產業結構意味著這個地區要發展,土地是最珍貴的資源。經過專業的測算,截止2030年,如果各個產業都經歷持續發展,整個區域的土地豁口將達到550公頃。
在村莊和城鎮騎行走訪了兩天,展現給我們的是大片的草甸,玉米地和苗圃,湖水蕩漾,街道愜意,園藝更是當地人的驕傲。和居民接觸之后我們了解到這里的人普遍受教育水平較高,歐洲的資本經濟下農場主、苗圃主以及泥炭開發業主充斥這個地區。五名中國同學一致認為就這種風景田園式的歐洲鄉鎮生活正式許許多多國人夢寐以求的定居地;這樣的美好正是我們所以為的景觀設計的最終目標。
然而當我們越來越多地和當地的利益相關者接觸之后,問題漸漸浮現。各行各業都有發展的優勢和瓶頸,他們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我們的第二個任務就是把自己當作一類利益相關者,站在他們的角度弄明白他在地區中的“power”,他們自己在地區中的份額,和其他利益相關者活著其他類型土地的關系,未來的機遇和挑戰等。以苗圃主為例,Middle Ammerland苗圃行業規模很大,苗木產量占整個Lower Saxony州的50%,本地苗木公司Bruns更是整個歐洲最大的苗圃,為這個地區贏來了不少殊榮。但苗圃主們并不是這個地區的多數派,他們認為他們目前正處于一種微妙的處境。首先,苗圃需要土地,而且苗圃生產具有時間長,不易遷移的特點;但是就目前來說,由于歐盟對可再生能源的提倡,種植玉米的農民可以得到可觀的補貼,因此他們更容易從地主手中爭奪土地,損失巨大。第二,這個地區之所以能夠形成“公園式景觀”,和這里世代相傳的苗圃業有很大關系。正是由于這種“公園式景觀”,Ammerland的旅游業也因此發展起來。第三,上個世紀之前用于劃分界限的樹籬占用大量土地,但是限于相關生態法令,他們只能忍受土地空間的浪費。苗圃業主認為他們的行業應該會保持平穩發展;除了農民,他們和其他行業沒有沖突。其他利益相關者在該地區的角色也類似地表達出來,整個區域的人地關系也漸漸明晰。
建立在對人地關系相對了解的基礎上,項目進入最后設計階段。與以往的規劃項目不同,這次workshop并沒有使用傳統的用地分類方法,而是從土地上具體的利益相關者以及具體的活動為入手點,進而形成概念,提出利于所有人利益的解決辦法。景觀設計師的任務也不再局限于我們熟知的“空間規劃”層面,而成為了某種程度上的原則制定者。比如其中一組同學的概念就是首先從大眾利益入手,保護一定數量的生態保護和生態補償用地,形成綠色基礎設施的格局網絡,在此基礎上結合現有的用地進行遠景規劃,產生矛盾的時候,進行討論聽證;還有一組同學則從開發強度的角度出發,從生態,地理以及土地使用現狀角度出發,將土地劃分為高密度使用,中密度使用和低密度使用三類,對三類用地賦予相應的使用原則,發生用地沖突的時候進行利益相關者的博弈和民主決策。這樣的規劃概念直接體現出景觀設計學對人地關系的解讀,在法定規劃之外形成了具有相當執行彈性和發展彈性的發展規劃。
從這次德國的workshop來看,歐洲國家和我國面臨的景觀設計學挑戰有一定差異。我國尚處于城鎮化高速發展的階段,生態債務到處可見,因此許多項目針對于生態恢復;新城建設也此起彼伏,規劃的思路基本上是不同程度的新建,很少側重于更新。歐洲國家則已具備高度城鎮化水平和相對完善的生態補償機制,大部分項目為改造項目,因此規劃中涉及到土地上發生的復雜的社會關系。但是隨著我國政府對地方財政赤字的控制進一步加強,規劃建設的主題必將轉型。
無論在中國還是德國,都有法定的城鄉規劃編制;但是從景觀規劃角度而言,尚未形成相應法規,因此在方法上更加自由,可以采取較為特殊的方式以便更加貼近場地情況。本次workshop緊扣“running out of land” 這一主題,將需要使用土地,規劃土地的人提取出來,從社會問題上升到土地空間問題進而尋求解決辦法,切實地尋找人地關系中的矛盾點。之后的概念方案也盡可能地土地社會兩手抓,并不單純地提出空間解決方案,而是在此基礎上提倡居民共同解決社會問題,從而達到人地關系的協調,這正是景觀設計學所關注的(俞孔堅,李迪華,2007)。
這次workshop從場地真實的情況出發,采用角色帶入的方式進行使用者感知調查。研究表明,設計師和使用者的感知存在差異(Yu,1995; Hofmann etc.,2014),而設計師的作品是為使用者設計的。這樣的過程難免會和場地的真實人地關系有出入,從利益相關者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則有效地避免了這樣的問題。綜合分析各個利益相關者的交互關系,這樣的成果相對完善地表達出了場地的真實現狀;而且從真實的人的角度來分析未來的發展,比起設置計劃目標,對于高度發展的城鄉基底來說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和現實實現性。同時,這種方法將當地人融入到規劃的過程和體系中來,增加了公眾參與的可能,也給規劃賦予了新的意義。
德國《建設法典》明確規定,公民有權了解規劃目標,有權參與方案編制,有權參與規劃方案的討論,并提出相關想法或建議。從第一天到達Ammerland,無論是利益相關者意愿調查,還是項目匯報,從市長到農民,大家都熱情地參與到討論中去。一位泥炭采掘業主聽了設計概念之后十分激動地贊同,并從他的經驗中分析了如何克服土地決策上的不公平。參與者們表示這種各行各業的人相聚的機會很好,希望可以多進行類似活動。Middle Ammerland人們的這種熱情處處體現著他們對生活,對未來的認真和細致,他們的經驗也值得我們借鑒。
本次暑期課程最大的收獲就是將所學的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開始真正理解景觀設計的終極目標是解決場地上存在的問題,而不僅僅局限于堆山造型。原本看不到摸不著的“以人為本”也植根于此,讓我理解了“人本主義”——它不只是對個人利益的支持和最大化,還包括平等自由的參與權欲決策權——它出于對人的尊重。
參考文獻
[1]Hofmann, Mathias. Westermann, J.R. Kowarik, I. Meer,E.Perceptions of parks and urban derelict land by landscape planners and residents[J]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2014,11:303–312.
[2]任國巖.論公眾參與城市規劃[J]規劃師.2000,16(5):73-75.
[3]Yu, K.Cultural variations in landscape preference: comparisons among Chinese sub-groups and Western design experts[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1995,32(2):107–126.
[4]俞孔堅,李迪華.可持續景觀[J]城市環境設計.2007(1):7-12.
——《勢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