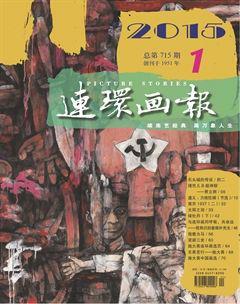無畏苦行——施大畏
耿劍


施大畏,1950年生,浙江湖州人。有人說施大畏畫畫如同拼命三郎,只要一拿起畫筆便不知累、不知苦、不知煩,勇往直前。施大畏給自己的座右銘是“畫我喜歡的畫”,幾十年來不論他畫連環(huán)畫,還是畫中國畫,始終有著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他要用繪畫觀照生活、觀照社會、觀照人性,“他用他的作品來思考自己對社會,對民族乃至對人本身的責任;闡釋自己對歷史、對現(xiàn)在乃至未來的理解”。
施大畏自幼喜愛畫畫,那個年代普通百姓人家能夠接觸到最多的“畫冊”,恐怕就要數(shù)“小人書”了,他還記得,幼時從母親那里拿到了零用錢,要么就買來幾只粉筆,在家門口的水泥地上涂畫腦海中的幻想;要么就跑去書攤上看書,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本價值幾毛錢,不知看了多少次的《三打祝家莊》。十三四歲時,施大畏跟著母親的學生毛國倫先生臨摹門采爾、尼古拉、菲欽等大師的素描,一周二十張的練習量,讓他打下了堅實的童子功。1964年,從敬業(yè)中學畢業(yè)的施大畏,由于時局問題,無法繼續(xù)求學,只得去市建二公司當起了油漆工。他說:“當油漆工,經(jīng)常需要調(diào)整漆的顏色,我最在行了!”很快他就找到了工作的樂趣。那時的施大畏,跟著建筑工程隊一起到安徽某個山溝里搭建戰(zhàn)備所需的房子。白天干了一整天的體力活兒,晚上師傅們都光著膀子喝酒、打牌,只有施大畏一人不言不語,在睡覺的床上碼個小桌子,趴在上面畫畫,畫的就是這些活生生的師傅們。三年后,領(lǐng)導調(diào)他去機關(guān)搞宣傳,好讓他發(fā)揮專長。1974年,經(jīng)過工人生活洗禮的施大畏創(chuàng)作了《祖國處處是我家》,使得他在美術(shù)界嶄露頭角。他回憶道:“這就是我的生活,我在藝術(shù)上的起點,便是我與底層人民群眾建立起來的感情。”
也是在那一時期,施大畏開始創(chuàng)作連環(huán)畫,他的第一本連環(huán)畫《難忘的友誼》(合作),畫得極其認真。雖然只有四十幾頁,可萬事開頭難,最初畫起來并不易,只能照著前輩的路子走,一點一點鉆研進去。第一本連環(huán)畫的出版,帶給施大畏的喜悅無以言表,看著書擺放在新華書店貨架上就很歡喜。后來,從施大畏早期的連環(huán)畫《三棵棗樹》《恩瑪?shù)倌棠獭贰杜实恰贰督鹄C娘》中就可見其扎實的素描功底,他的作品造型準確,筆力雄勁,嚴謹扎實的畫風是他一貫的作風。1978年,施大畏進入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室,任創(chuàng)作員,專職創(chuàng)作連環(huán)畫。那會兒,在出版社繪畫,不但畫畫有稿費,外出寫生每天還有兩角的餐補費,半年下來就能攢個十幾元,這筆“豐厚”的收入,的確讓人喜出望外,那種工作和生活完美結(jié)合的日子,給他留下了難忘的記憶。施大畏提到:“那時,出版社畫連環(huán)畫有規(guī)定,拿到題材必須到相應的地方體驗生活一個月,否則不許回來。”施大畏接到《朱德同志在井岡山》的腳本,一個人打了背包就去了南昌,碰上江西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的丘瑋,幫忙開了介紹信,這才到了井岡山。他在井岡山到處找老鄉(xiāng)、老紅軍,還去當?shù)氐木蠢显赫业搅速R子珍的戰(zhàn)友,聽她講當年的故事。施大畏在山上待了一個多月,積累了大量的速寫,回來之后交給領(lǐng)導審核。正是有了這樣的積累,才創(chuàng)作出了這部人物造型精準的水墨淡彩連環(huán)畫,成功塑造了朱老總的光輝形象。
施大畏總說:“沒有生活積累、對生活認識不夠的畫家,何談創(chuàng)作?他畫不好連環(huán)畫!賀友直先生,為了畫《山鄉(xiāng)巨變》,三次下鄉(xiāng)體驗生活。他在生活中發(fā)現(xiàn)‘四小——小動作、小道具、小孩子、小動物,用它們把故事畫生動了。這種東西不到生活中體會,不向生活中的人們學習,僅憑看幾本書,是體會不到的。”正是靠著對生活的感悟,施大畏創(chuàng)作了一部部經(jīng)典連環(huán)畫。20世紀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他的連環(huán)畫《清兵入塞》《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都是這樣創(chuàng)作出來的。他畫《清兵入塞》,與羅希賢、崔君沛、徐有武、王亦秋五人組成創(chuàng)作小組,從上海乘火車北上,先后到了天津、山海關(guān)、北京故宮、長城、洛陽、西安、潼關(guān)等地采風。有一天,他們在洛陽龍門石窟,剛好吃過午飯準備休息,施大畏發(fā)現(xiàn)遠處有一群農(nóng)民,躺在地上小憩,他馬上湊過去,把這個場面畫了下來,后來就畫到李白成慘敗,在路上打尖時的情景中,他利用這個速寫并經(jīng)過加工,融化到創(chuàng)作中去。他畫《暴風驟雨》,在拿到腳本的第二天,就和搭檔韓碩(封面為兩人合繪)一同坐火車、趕汽車去了東北元茂屯。兩人到了那里,白天寫生,晚上記筆記,還時常到老鄉(xiāng)家里,和老鄉(xiāng)嘮嗑。那里十分偏僻,條件簡陋,晚上住的地方挨著公路,門又鎖不上,兩人只好用毛巾捆上鎖,再把水壺、臉盆放在門口,以防有人半夜闖入。就是在這種條件下堅持了一個多月,在創(chuàng)作中,他以激情飽滿的筆觸,用中國傳統(tǒng)的線描將東北解放運動波瀾壯闊的過程生動地描繪了出來。后來,施大畏畫《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特意到桑干河畔走了一圈,還特意找到作者丁玲,了解創(chuàng)作故事及人物性格發(fā)展線索等,畫了一百多幅的素描速寫,如今看來仍帶有生活的味道。就是憑著這種踏踏實實的創(chuàng)作道路,讓施大畏的連環(huán)畫一部部均可堪稱經(jīng)典,他的《清兵入塞》《暴風驟雨》《望夫石》接連入選全國第二、第三、第四屆連環(huán)畫評獎并獲得創(chuàng)作二等獎和兩次三等獎。這段創(chuàng)作經(jīng)歷不僅給他留下了一生難忘的經(jīng)驗,更為他日后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積淀了豐厚的素材。
有人說施大畏的連環(huán)畫給人的第一印象便是準確的人物造型和個性化的筆墨線條。無論是《李白成》中用線之灑脫還是《暴風驟雨》中用線之張弛有度、豪邁奔放,他的線描技法始終不斷地創(chuàng)新并精進。而到1991年他的獲獎作品《望夫石》,他更是把自身的彩墨技法激發(fā)出了新的藝術(shù)內(nèi)涵和更豐富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
1986年,施大畏調(diào)入上海中國畫院,五年后逐漸走上了領(lǐng)導崗位。無論是操持畫院大樓的建造、還是推進單位的體制改革,他都親力親為,這些工作擠占了他的創(chuàng)作時間,也讓他進入了另一個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階段,他繪制了大量的中國畫。也許是受到年少時對英雄的崇拜之情的影響,他的《1941.1.14·皖南事變》《歸途——西路軍婦女團紀實》《國殤》《不滅的記憶——南京·1937》等都是表現(xiàn)中國歷史悲劇的宏大敘事。他曾說過:“中國畫的偉大的包容性不只體現(xiàn)在文人畫,它更具有大江東去的豪邁氣概。我迷戀恢宏的、有崇高感的畫面。歷史有這個能量,歷史是人類活動積壓濃縮之后的體現(xiàn),我相信它可以支撐我的畫面,將如此跌宕起伏的戲劇簡化為線條、塊面的結(jié)構(gòu)……我想精選歷史的切面,以悲壯為伏線,連成一部史詩。”這就是施大畏獨特的中國畫創(chuàng)作道路。即使是在創(chuàng)作中國畫,施大畏也堅守著藝術(shù)源于生活的宗旨,他說:“1996年,我沿著黃河走,到榆林高家坡,我在那里畫農(nóng)家的速寫,碰到一位七十多歲戴白羊肚手巾的老漢,我給他拍了一張照片;2007年,我又到高家坡,老漢已經(jīng)八十多歲了,我又給他拍了一張照片。當我把兩張照片放在一起,就會心生感慨:這個村子走不出多遠就是高速公路,但這里十年都沒有變化,所以我畫了《高原的云》,來表達這個感覺。”神話故事也是令施大畏癡迷的題材,近年來他也創(chuàng)作了不少此類題材作品,如《開天》《后羿的故事》《夸父族的故事》等,他說“這些神話積淀了雄厚的中華民族的力量,可以讓當下的人們從歷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中國的神話是民族靈魂所在,是可與世界文明進行對話的文化元素。”
談到當下美術(shù)界無法回避的問題——精品力作的匱乏,施大畏講道,現(xiàn)在的青年畫家,太過急功近利,忙于應酬畫,而沒有靜下心來進行創(chuàng)作。“做文化不能靠價格,要靠藝術(shù)家的執(zhí)著。”連環(huán)畫家的創(chuàng)作也是如此,20世紀80年代,連環(huán)畫的發(fā)展達到了一個樣式上的頂峰階段,然而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沖擊、日韓動漫的影響,畫家精神的衰落,連環(huán)畫走入了低谷期。“首先,要有好的創(chuàng)作題材,要研究當下年輕人喜聞樂見的東西;其次,畫家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要端正,藝術(shù)不分大小,連環(huán)畫不是單純的‘小人書,畫家對藝術(shù)要有信念的追求,要有敬業(yè)精神,才能畫出好的東西。”或許只有這樣,才能讓連環(huán)畫走出低谷,重新走入輝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