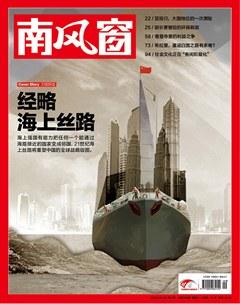城市也是受害者
唐小兵
讀《南風窗》上一期封面策劃“我們的精神史”較受觸動,春節過去不久,《平凡的世界》還在熱播,平時被冷落的鄉村生活或者說鄉愁突然被給予了高度的關注。這一期專題從多個層面展現了城鄉流動這個歷史過程造成的多重因果關聯,從鄉村到城市的人員流動從晚清就已開始,這其中既有自然的選擇,也有戰爭、政治等多種外部因素的影響,而從城市到鄉村的“返流”,在20世紀到如今,可能只有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等。兩者之間呈現出來的自然是一種不對等的病態關系,簡言之,從鄉村到城市的流動被認為是正常的階層上升流動,而從城市到鄉村的流動,則往往會被認為是非常態的社會選擇,意味著被城市淘汰了之后的別無選擇。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所謂“鄉愁”?它究竟是對鄉村生活一種內在的關切,還是一種追逐潮流的“矯情”?或者是進入城市之后長久無法安頓身心之后的一種心靈病癥?
如果是內在的關切,那就是無法割舍的,就像這一期報道中有些在城市里已經變成所謂“成功人士”的選擇那樣,千方百計也要回歸鄉村,反哺鄉村,不將鄉村作為一個包袱而渲染悲情,而是切實地從日常生活出發,為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這在前些年一些鄉村讀書計劃以及其他致力于鄉村文化與社會建設的公益組織中都可以印證。若是一種追逐潮流,則是一種虛假甚至病態的鄉村意識,其骨子里其實是高度認可城市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但似乎對鄉村有一點點愧疚感,而談論鄉愁又顯得特別“高大上”或者說有“人文情懷”,于是就人云亦云地鸚鵡學舌,這種所謂鄉愁不足道也。當然,還有第三種,就是一些在城市里長久無法尋找到內心寄托的人,這些人既有失意者,也有成功者(從物質生活來看),他們的鄉愁更多的是在對城市痛斥之后的一種心靈自我補償,是尋找一種替代性的精神安慰。
這最后一種折射出來的就是我們的城市文化、社會和意義建設的高度單一化,無論是城市的物理空間還是精神生活空間,都收到擠壓,這正如《南風窗》記者何蘊琪的報道所顯現,這些人即使到了大理等地方,其實仍舊是在精確地復制在廣州、上海或北京等地的家庭生活模式,對于日常生活世界的自我更新和想象力,其實最大程度地限制了無論是城里人還是鄉下人的美學趣味。而沒有審美趣味和多元化的自覺意識,一種表面上追逐時尚的生活,卻可能是一種無意義的生活。在這一組報道中,我覺得特別有價值的是關于城市的敘述和分析,在此前二元對立的敘述框架之中,鄉村總是受害者,城市總是施害者。可是,如果我們認真地對待我們的生活空間,就會發現伴隨鄉村在消逝的同時,一個更為多樣化和原生態的城市,同樣在消逝,城市同樣也是受害者,這也許才是同樣值得我們關切的問題。城市為什么成了讓我們厭煩卻無法擺脫的夢魘?它為什么不能像卡夫卡筆下的布拉格或者波德萊爾筆下的巴黎,或者民國時期如張愛玲筆下的上海那樣,充滿了日常生活的傳奇感,以及魚龍混雜的多樣性,或者說一種將“都市里的鄉村”和“鄉村里的都市”融合起來的空間?城市為何無法將我們凝聚起來成為一個共同體,這也許是同樣值得思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