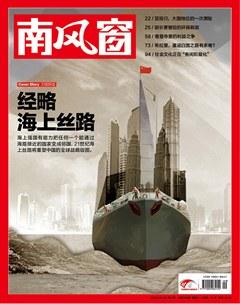亞投行,大國地位的一次測驗
唐昊


截至4月15日,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最終達到57個。
據財政部網站消息,截至4月15日,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增至57個。
關于中國倡議的亞投行,美國一開始是拒絕的,但架不住中國一直告訴世界這個銀行會有“特效”。隨著相信“特效”的英國的加入,抵制亞投行的美國聯盟“DUANG”的一聲垮塌了。最終,圍繞著亞投行的國家間博弈,以美國的盟國紛紛加入亞投行而告一段落。這普遍被認為是中國的勝利和美國的失敗。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單純。
創建一個金融組織相對來說是容易的—只要有錢就行了。要讓這個金融組織持續地發展,則是另外一回事—它還得不斷地賺錢。特別是亞投行這種發展銀行與一般的銀行不同,其目的是要對貧困國家進行援助,同時保障投資者的利益。而這兩個目標并不那么容易實現。在這個意義上,關于亞投行的真正考驗還沒有來臨。如果亞投行的規程設定不滿足相關國家的要求,或投資運作得不盡如人意,那么這些當初蜂擁而至的國家也更有可能會一哄而散。中國將57個國家拉到亞投行這條船上,贏得了尊嚴,但隨之而來的國際壓力也是前所未有的。這些國家之所以上船,可不是因為喜歡中國當“老大”,而是為分一杯羹而來。
過去的12年間(從2002年到2014年),在中國對外投資高速增長,吸引外資增長速度卻放緩的背景下,中國逐漸成為凈對外投資國。有統計表明,這12年里中國境外投資猛增50倍之多,直接投資存量超過6600億美元。僅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就達到1400億美元左右。由于這一年的中國對外投資比中國利用外資超出約200億美元,表明中國已正式成為資本凈輸出國。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2014年中國100大跨國公司的海外資產和海外員工無論是規模還是占比都比上年有所上升,然而海外營業收入的平均占比卻由22.25%降至20.86%,下降了1.39個百分點。這直接反映了中國公司海外業務投資回報率不理想。
其中最令人難以釋懷的案例是在2008年,中鋼不顧澳大利亞本土的反對聲音收購中西部礦產公司,結果在收購成功后周邊的港口、鐵路均被拍賣給日本三菱公司并隨后停止建設,導致中鋼收購的礦產無法利用。這家巨型國企以虧損嚴重、退出國企100強、決策者被調查而慘淡收場。類似的情況在對外投資的中國企業身上經常發生。商務部研究中心顧問吳東華教授直言中國“海外礦產能源、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70%是失敗的,充分說明了中國以往海外投資的風險和效益相當不成比例。
基于這樣的歷史記錄,很多學者認為由中國主導的亞投行未來的風險在于投資效益如何保障。因為在亞洲,雖然因基礎設施短缺而制約了經濟發展的國家有很多,但也正是這些投資需求國的國內政局極度不穩定,是世界上最無法保障投資者利益的國家。此前中國在這些國家多有投資,但經常血本無歸。特別是在亞洲的基礎設施投資,如泰國的大米換高鐵項目、柬埔寨的水利項目、斯里蘭卡的港口項目近年來都遭遇過叫停,中資企業損失嚴重。
當然,對于一心謀求大國地位的中國來說,其創設亞投行的目的當然有著政治上的戰略考量,為“一帶一路”的戰略和中國金融地位進行鋪墊,至于賺不賺錢尚在其次。不過,即使是基于這種考慮將投資回報放在第二位,亞投行所面臨的政治和外交上的風險仍不可低估,甚至其影響有可能超過單純的經濟風險。筆者將它命名為“模式風險”。
對外資本輸出的“模式風險”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內部管理模式,二是對外投資模式。在內部管理方面,英、法、德、意等歐洲國家的加入,一定是以謀求董事席位為目標。而在中國不具有否決權的情況下,亞投行內部的管理將呈現典型的多頭協商局面。中國必須學會在金融多邊組織中發揮協調作用,否則亞投行將在董事分歧的情況下失去能力。迄今為止中國仍未明確亞投行的基本章程原則。國務院臺辦發言人馬曉光4月15日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目前意向創始會員國正就亞投行的章程進行談判,適用于新成員加入的相關程序和規則尚在磋商之中。
關于對外投資模式,最重要的不是投資回報,而是處理好投資和治理之間的關系。在某種意義上,這是真正實現多邊開發銀行目標的生命線。世界銀行和亞洲銀行以往在進行投資時的核心議題正在于此。當然,許多得不到投資的發展中國家對于兩大銀行的批判也正在于兩者所堅持的投資與治理掛鉤原則。
曾在世界銀行擔任顧問的魯特教授,也是亞洲開發銀行的總裁顧問。他的成名作《聯盟的詛咒》,描寫的正是美國和世行冷戰期間所進行的對外援助和投資,很多情況下帶來的是嚴重的問題而不是進步,甚至制造出美國至今仍很頭痛的敵人。在聽到亞投行的消息后,他曾表示過擔憂,即中國有可能會步美國的后塵,在那些國家進行無效投資,甚至有可能催生壞的發展模式。經驗表明,缺乏治理前提的投資經常會引發投資對象國更嚴重的國內問題。
確實,只問投資而忽視治理,在世行和亞行以往的經歷中有著特別慘痛的教訓。對于一個治理結構不良的國家來說,大筆資金的涌入有可能對投資者和投資對象國帶來雙重的消極后果。
消極后果之一是刺激腐敗。過去數十年時間里,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援助機構,世界銀行扮演了對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凈水系統、教育機構、通信設施等進行投資建設的角色,很多人因此受益。但問題是,相關的項目資金卻難以監管,非生產型公共消費大增,讓這些國家的腐敗情況更加嚴重。世行2014年的報告顯示,有高達85%的援助資金被挪用,而非按照原計劃發揮作用。
消極后果之二是加速貧富分化。本來亞行和世行的貸款是為了提升窮人的競爭力。但由于不少受貸國家本身的制度設計是排斥窮人的,所以從項目中受益的往往是精英階層。援助之下,貧富鴻溝進一步拉大,社會矛盾更加突出。有數據顯示,從1970年到1998年,經過28年的不斷援助,非洲的貧困率竟然從11%迅速飆升到66%。
消極后果之三是造成“援助依賴癥”、“世行依賴癥”,即治理水平過低的國家會因過度依賴援助而自身造血機能退化,經濟發展無力。上世紀80年代以來,最依賴援助的非洲國家的經濟增長率為負數。離開國際社會的援助,這些國家可能一夕之間就會垮下來。這可能是國際援助史上最大的教訓了。
事實證明,那些接受世界銀行貸款而運作良好、回報率高的國家,如中國、博茨瓦納等,本身擁有足夠的治理能力,因此才能將外來資金真正化為發展的動力。也許有些中國人認為本國的治理水平很一般,但實際上就目前的治理水平來說,中國已經被認為是世界銀行最大和信譽最好的客戶了。到2003年上半年之前,世界銀行已經為中國245個項目提供貸款大約366億美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貢獻巨大。而中國的發展也成為世界銀行在過去主要的“政績”之一,雙方皆大歡喜。
相比較而言,比中國的治理水平更差的國家有的是,很多事情是我們難以想象的。有曾在世行工作的朋友就抱怨說,在印度連買張火車票這樣的小事都要向基層官員行賄,雖然印度的火車票價很低,但幾乎每走一步都要涉及賄賂的問題。他認為,還是中國的火車站服務好,按價交錢就能買到票!也有在非洲投資的企業,中方經理與本地員工奮斗了一年,最終連員工上班遲到的問題都無法解決。在這樣連最基本的治理能力都缺乏的投資環境里,資金最終會去向何方,究竟能不能起到幫助發展的作用,那不是想當然的事情。這也是世界銀行和亞行一直將投資對象國的治理水平作為投放貸款前提條件的原因。當然,這樣做是不是剝奪了這些國家發展的機會,則是另外一個被熱衷討論的問題。但畢竟,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Kenneth Rogoff所言,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稀缺的不是現金,而是有能力的政府。
而這個環節正是亞投行可能面臨的問題和風險所在。以往中國自己的對外援助向以“絕不附帶任何條件”、“不干涉內政”而著稱。經濟學家費恩波姆發文稱,中國的貸款從不過分關心減少貪污,提高透明度,或者提高私營公司的條件;它通常要求受援國家,購買中國產品或者雇傭中國工人。確實,只提經濟條件、不設治理前提的投資,有可能摧毀世行在過去幾十年里用慘痛教訓所構建起來的投資防火墻,甚至讓這些國家敗壞的治理水準雪上加霜。這正是外界對于亞投行的投資模式最為擔心的地方,決策者不可不察。
中國在以往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積累了足堪世界各國借鑒的經驗,當然也強化了亟待解決的嚴重問題:收入分配體制不公而致貧富兩極分化,企業與政府關系過于密切易催生腐敗,片面強調經濟發展帶來環境惡化,等等。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些問題都是中國的國內問題,由中國人自己來承受。但隨著中國經濟逐漸走向世界,這種發展模式中的問題也會隨之“行銷”世界。
中國經濟走向世界可分為三個階段:產品、公司和國家。在中國經濟以“產品”走向世界的階段,歐美國家由于貿易體制成熟,“中國制造”的情況還好。但在俄羅斯、東歐等市場經濟不健全的地方,“中國制造”幾乎成了“問題產品”、“質量差”的代名詞,對這些國家與中國的長期合作帶來惡劣影響。
在中國經濟以“公司”走向世界的階段,對外投資主體以大型國有企業為主。如前所述,有的對投資的管理不善,虧損嚴重;有的過度追求資源占有,連累中國在所在國飽受“新殖民主義”的指責。有時還兩者都沾邊—像中鋼集團在澳的“敵意收購”,既虧了錢,又背負了惡名;而中資企業在東南亞的熱帶雨林開發,也飽受不小爭議。
而今,中國經濟開始以“國家”走向世界。關于“中國模式”會否影響其他國家的發展模式問題隨之被世界各國重視。美國、日本對亞投行的謹慎態度,歐洲國家一再強調亞投行規則的制定程序,如果拋除形式上的正義,其實質是表明了發達國家對于既有模式中負面問題的憂慮。從這個角度來看,亞投行雖然是一個聰明而大膽的嘗試,意在整合世界金融資源助推亞洲發展。但就以往的投資和援助方式來看,這一嘗試客觀上與上述風險是高度耦合的。除非我們能夠創新和改變現有的投資模式,否則很容易被自己的強大投資能力所累。
不過,好消息是,2014年習近平在參加布里斯班G20峰會上明確提出,中國支持加強全球制度,而非弱化全球制度;中國也支持世界銀行搞的全球基礎設施投資基金,愿意把自己的“一帶一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納入全球計劃中。這個表態意味著,在以“國家”走向世界的階段,中國也在試圖讓世界走向中國,用成熟的全球經濟制度來改善中國的制度短板。如若這些提議得以實踐,就不僅是一個亞投行的項目的成功,中國對外經濟模式的制度性進步對中國、亞洲和世界的發展貢獻將不可限量。
因此,我們不能停留于目前的成功而沾沾自喜。因為亞投行所可能帶給中國的,除了表面的榮耀外,更是一次站在大國地位邊緣的測驗。當中國已經被默認為是一個有資格引領世界的角色,被全世界期待發揮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特效”時,就更需要在一片贊譽聲中清醒地認識到可能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