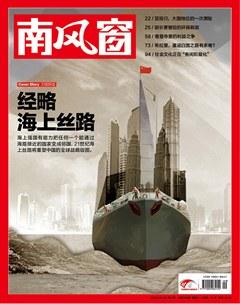虛幻與真實的中國:從魯濱遜到安森
張國剛
18世紀歐洲的中國形象,在不同的國度、不同的學者,或者同一個學者的不同時期,都會有所不同。大體說來,狄德羅前期贊揚多,后期批評多。伏爾泰正面評價比較多,孟德斯鳩負面看法比較多。其中一個原因是資訊來源不同,伏爾泰更相信耶穌會士的材料,孟德斯鳩卻親自訪問了一些遠東歸來的船長和商人。
18世紀對中國最負面的評價還是來自英國。
英國在18世紀已經進入工業革命階段,自信滿滿。英國著名現實主義作家笛福(1660~1731)的第一部小說《魯濱遜漂流記》,講述了英國冒險家開拓“新世界”的殖民者魯濱遜,獨自在荒島上創造新生活的故事,使他聲譽鵲起。他還創造了《魯濱遜二次漂流記》,這次的旅行來到了中國的南京和北京。10天的南京行,使魯濱遜覺得,盡管這個城市人口繁盛,但是同英國相比,則毫無可稱道之處:當我把這些國家的可憐的人民同我們國家的相比時,他們的衣著、生活方式,他們的政府、宗教,他們的財產和榮耀,幾乎不值一提:
“他們的建筑,拿什么同歐洲宮殿和皇家建筑相比?他們拿什么同英國、荷蘭、法國和西班牙進行普遍貿易?他們的城市在財富、堅固、外觀的艷麗、富足的設施和無窮的樣式上,有什么可與我們的城市相比?他們那停泊了幾艘帆船和小艇的港口,如何同我們的航運、我們的商船、我們巨大而有力的海軍相比?”“我們的倫敦的貿易量就超過他們全國一半的貿易量;一艘配備80架槍炮的英國、荷蘭或法國軍艦就能摧毀所有中國船只。”“中國沒有一個設防的城鎮能夠抵擋歐洲軍隊一個月的炮轟和攻打。”“當我回到家鄉,聽到我們的人民在談論中國人的力量、光榮、輝煌和貿易這類美好事情時,我感到很奇怪;因為就我所見,他們顯然是不值一提的一群人或無知群氓、卑賤的奴隸,臣服于一個只配統治這種人的政府。”
笛福還借魯濱遜的北京之行,貶低中國人的道德。他們進京跟在一位總督的隨從隊伍中,每天有充足供給,但要按市面價格付賬。還有另外30個人,也以同樣的方式隨隊旅行。總督借此大賺一筆,因為國家無償供給他旅行用品,他則有償提供給旅行者。中國人除了像這位總督這般的貪婪,也很傲慢,富人喜歡擺架子,蓄養眾多奴仆來賣弄;普通平民也很傲慢無禮。
笛福沒有到過東方,他的魯濱遜在華游歷是編纂加創作而成,但早在馬嘎爾尼來華前半個世紀,一位叫安森(Baron George Anson)的英國船長,在其環球航行途中,有過在澳門和廣州(1742~1743年間)停留的經歷。1748年出版的《環球航行記》(A Voyage round the World,in the years 1740~1944),根據安森及其下屬的航海日志編纂而成。其中對中國的描述,來自他們的親身見聞,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18世紀后半葉歐洲人打量中國的眼神。
1742年11月至1743年4月,安森在澳門停靠了半年,因為船只損壞和需要補給,向廣州官員申請雇人修船并購買補給品。起先,安森沒有獲得中國官方的許可證,因此被嚴格禁止購買任何貨物或請中國人來工作。英國人為此評論說,中國地方官特別喜歡頒布各種禁令,用觸犯刑法的辦法收取罰金,是中國官員常見的生財之道。
中國官員欺軟怕硬,甚至官賊勾結,這也是英國人從親身經歷得出的印象。艦隊在澳門時,一位因生病而乘小船上岸活動的英國官員遭到毆打和搶劫,安森立刻知會中國官員,地方官態度冷淡地表示若查獲這些賊,將懲罰他們,但他根本就沒有行動。后來英國人從一群來賣供應品的中國人中,認出了那天的一名首犯,于是安森將他扣留。當中國地方官前來交涉時,安森態度強硬地威脅說可以將這名罪犯擊斃,于是地方官立刻從高高在上變成卑躬屈膝地懇求安森放人,甚至很快又來了好幾位地方官,許諾一大筆贖金請求放人。安森揣測,這些地方官吏與竊賊之間肯定互通情報,狼狽為奸,怕事情鬧大,廣州知府拿他們問罪,故而苦苦哀求安森放人。
但這種官民同盟也有因分贓不勻導致破裂的情況。安森的旗艦丟失一根中桅,打聽不到下落,只好以重金懸賞,結果很快就有地方官通報說他手下有人找到這根中桅,安森派船取回中桅并如約付給這些人酬金。安森許諾這位地方官一份單獨的酬勞,并托一名牙人轉交,不料牙人將錢私吞。于是一天早上,那位地方官找借口登船,于談話間問起安森是否再次丟失中桅,安森明白該官吏是為錢而來,就問他是否從牙人那里收到錢。雙方都明白牙人做手腳之后,安森答應再付一筆,地方官卻回答不必,因為第二天他派人把那位牙人搶劫一空。
安森也一口咬定欺詐和自私是中國人的習慣或天性。安森1743年7月自澳門駛往廣州并一直停泊在廣州河口,這時終于獲得總督許可能夠自由購買日常消費品,但還需為返回英國的航程準備充足給養。中國人賣給安森供應品時,在增加分量方面所耍的花招令人難以置信,比如給雞鴨填喂石塊和沙礫,給豬肉注水,給活豬喂許多鹽迫使它們因口渴而大量喝水。安森買上船的禽畜因中國人做手腳而很快死亡,當它們被船員扔下船時,尾隨船后的中國人就會搶為己有,尋機再次出售,因為中國人不避諱吃自然死亡的動物。凡此種種,足見中國人的性格并非天主教傳教士們神話般描述的那樣,他們顯然與耶穌會士所說的一切美好品質的模范相去甚遠。
《環球航行記》的編者根據安森等人的描述評論說,中國人所自命的文雅道德其實只是外表舉止有度,而非內心誠實和仁慈。中國人一貫注意壓制所有激情和暴力的征兆,這算是一種道德,但中國人所不加克制的偽善與欺詐,對人類普遍利益的傷害常常大于魯莽粗暴的性情所造成的傷害,因為魯莽與粗暴并不排斥忠誠、仁慈、果斷,也不排斥其他許多值得贊揚的品質。一個人在抑制較為粗野和狂暴的激情時,往往導致自私性格膨脹,所以中國人的怯懦、矯飾和不誠實,或許多少應歸罪于該國如此盛行的沉著鎮靜和外表得體。
安森認為,在中國無論是帝國憲法還是政府的一般命令都不易貫徹。中國雖然人口眾多、富饒遼闊,自詡其文明智慧,卻還是被“一撮韃靼人”用10年左右就征服了。而且清帝國仍在不斷遭受各種反叛暴動和邊境騷亂,這正是由于居民的膽小懦弱和缺乏適當的軍事管理。安森曾經因為遲遲不能被廣州總督接見而在10月13日勇闖廣州河,徑入廣州城,并未遭到中國軍隊的有力抵抗。英國人由此得出結論,僅安森這一艘旗艦的軍力就勝過中國整個海軍力量。廣州是中國的主要海軍力量駐防地,但這里的戰船載重僅約300噸,船上最多4個人,裝備8~10門炮,其中最大的一門只能發射不超過4磅重的炮彈。而中國商船也無法抵擋任何歐洲武裝船只的進攻,它們從整體到部件都不結實,船上不配加農炮(cannon),這就是說,政府既不為商船配備可觀的火力,也不提供較好的造船法以保護它們,此亦中國政府不健全的又一證據。
總之,這篇《環球航行記》一出,立時成為暢銷書,并大大改繪了歐洲人對中國的印象。比如1748年12月刊的《環球雜志》立刻有人對游記做出反應,稱贊安森船長做得好,迫使整個中華帝國對英國國旗表示尊敬,這是一件莫大的快事。
安森的游記影響到著名哲學家休謨對中國的評價。安森對中國人道德的看法也影響了法國的孟德斯鳩,他在《論法的精神》中將西班牙人和中國人的性格對比,說西班牙人以信實著稱,而中國人的性格恰恰相反。
當然,魯濱遜的虛幻游記,安森的真實感受,都還不及后來馬嘎爾尼陛見乾隆時的傲慢。但是,他們打量中國的目光背后,分明流露出經歷著資產階級革命的大英帝國,對于沉浸在落日余暉中的天朝上國的睥睨和輕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