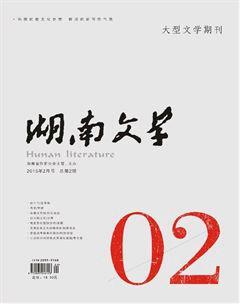沈從文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李佳懌
一九八二年初,湖北江陵發掘馬山一號楚墓,沈從文受荊州博物館邀請前往鑒賞出土的極品絲綢。到了荊州,耄耊老人在那批無價的戰國瑰寶面前下跪了。前一年,先生歷時十五年完成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出版。
關于沈從文的轉業,汪曾祺的《沈從文轉業之謎》和張新穎的《沈從文精讀》末一章已經講得很好。但我還是想趁此書再版之際,把自己的感受記下,保存切已真實的感動,哪怕只是細微暫時的。這也是沈從文一直在做的。
一、曲折十七年
沈從文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后記開頭寫道:“本書的成稿、付印到和讀者見面,經過許許多多曲折過程,前后拖延了約十七年。”我們現在讀到的這篇后記,是由原先的一篇依據多種不完全手稿片斷整理而成的文章壓縮而來。張新穎指出,“《曲折十七年》和《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后記主要不同在于,前者較為詳細地敘述了作者從編著這部書到這部書最終出版這十七年的經歷,特別是下放階段和回京之后的遭遇。”沈從文對這幾段經歷的記述仿佛家信般樸實生動,在此僅抄其中幾節,一是下放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干校的一段:
因為人已年近七十,心臟病早嚴重到隨時可出問題程度,雨雪中山路極滑,看牛放羊都無資格,就讓我帶個小板凳,到后山坡看守菜園,專職是驅趕村前趁隙來偷菜吃的大小豬。手腳凍得發木時,就到附近工具棚干草堆上躺一會會,活活血脈,避避風寒。夜里吃過飯后,就和同住的三個老工人,在一個煤油燈黃黯黯光影下輪流讀報,明白全國“形勢大好”。
后來轉到雙溪,這是沈從文在湖北待得最久的地方,約一年。沈先生的記述有些“黑色幽默”:
人事方面盡管十分融洽,可唯一不相熟的,是分配棺材那個小樓房,有點天然排斥因子。我即或血壓最高時有二百五十,還只想盡我做公民的責任,從不擔心會忽然間死去。
一九七二來請病假回到北京故居,先生馬上投入到書稿的修改中,全然不顧條件艱苦處境為難:
為了工作便利,我拆散許多較貴的圖錄,盡可能把它分門別類釘貼到四壁上去,還另外在小臥房中,縱橫牽了五條細鐵線,把擬作的圖像,分別夾掛到上面。……不到兩個月,房中墻上就幾乎全被一些奇奇怪怪圖像占據了。
即使刪去這些細節,單看成書簡歷,仍舊十分曲折。一九四九年八月,沈從文由北大國文系轉到歷史博物館,此后多年,他的工作只是為博物館的陳列品貼標簽,參預部分陳列,收集購買文物,而其實最主要的工作,是后記從《曲折十七年》中刪去的一句,“在陳列室里,不折不扣作了十年說明員”。一九六四年春夏間(沈從文調入歷史博物館工作已十五年),周恩來總理提出可編撰一部我國的歷代服飾史,以作為出國訪問的文化贈禮。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齊燕銘推薦沈從文來負責,歷史博物館從美術組調出李之檀、陳大章、范曾協助沈從文展開工作。工作方法由沈從文提供圖像和實物資料,按時代排列先后秩序,分別加以摹繪。并就每一圖試用不同方式,不同體例,適當引申文獻,進行分析比證,各寫出千百字說明。“進展格外迅速,由一九六四年初夏開始,前后不到八個月時間,本書主圖二百幅,附圖約百種,及說明文字二十余萬,樣稿就已基本完成。”(《后記》)本可望于當年冬季出版,但由于政治大動蕩已經出現先兆,出版拖延。“文革”開始,這書被認為是鼓吹“帝王將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書毒草,相關負責人受到沖擊,出版更是無望。一九六九年,沈從文下放湖北,在手邊無書又無其他資料的情況下,“只能就記憶所及,把圖稿中疏忽遺漏或多余處一一用簽條記下來,準備日后有機會時補改”。
上面提到歷博派作沈從文助手的三人,“文革”之后因為種種主客觀因由都各自離去了。幫助他完成《服飾研究》的兩位主要助手,一位叫王序,金介甫是這么介紹他的:“一九五三年有一位參加抗美援朝的軍人王序來參觀后,從此就留下來,成了沈的長期助手。”(金介甫:《沈從文傳》)沈從文臨去世幾年,王序常去看老先生,從來不敢進屋,就站在門外看著。因為沈先生一見了他就會哭。另一位叫王亞蓉,最早是學繪畫出身。沈從文想把她調到自己身邊工作,在征得歷博默許后,王亞蓉想盡辦法得到了原單位的調動批準,不想歷博領導不讓她與沈一起工作,而讓她到館里摹古畫。王亞蓉不愿讓老人寒心,選擇了拒絕。因為原單位已停薪留職,歷博又不肯接收,王亞蓉有半年時間只能依靠沈先生每月個人資助的二十元解決生活問題。
一九七八年,在胡喬木關注下,沈從文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關于工作、生活條件,他只提出:一、調王序、王亞蓉做助手;二、有個大些的工作室攤開工作。經過一年的努力,一九七九年初,《中國古代服飾資料》整理完成,更名為《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完稿后交北京輕工業出版社,該社擬與日本講談社合作,沈從文不同意。后轉至人民美術出版社,該社也計劃與日方合作,沈先生撤回書稿。后來由社科院領導向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推薦,后者決定從速出版。一九八一年二月,沈從文訪美歸國后赴廣州校對清樣。同年九月,此書正式在香港出版。同年底,臺灣出版盜版,因沈從文、郭沫若在臺灣屬被禁作者,盜印本沒有作者姓名,序言亦被刪掉。一九九二年,沈從文去世四年之后,本書由王序執筆增訂補正再版。
兩天前正好看到一段資料,可資補充。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的《新民晚報》在黃裳《沈從文的信》中附發沈從文一九八三年四月致黃的一信:
出版原定六四年試印,不意“文化革命”一來,忽成為“毒草”,支持此書編印的齊燕銘先生,被綁起來“歷博”斗了一整天,我則本為陪斗人物,但心臟病已明確,恐在斗中倒下,所以一會即放至隔室坐聽各種丑惡兇狠辱罵,計上下午七小時。事實上卻無什么人看得懂書中內容。甚至于根本還不曾看過此稿。最有趣處,即好幾位首長(包括文化部某某副部長)審看此圖稿時,曾在稿上另紙寫有贊賞眉批的,到批斗時,亦早已將眉批撤去,免遭連累,真是絕頂聰明。還有一位,后來斷定此書無事,擱于其手邊,待付印送審時,卻忽然發生興趣,意以為將我姓名去掉,用彼姓名。照當時情形甚合理,所謂“首長出思想”,十分重要。以“文物”和“人美”均不同意而擱下。到書印出時,卻又不高興,以不曾提及他的“熱情支持”一番美意,而大大不快。真十分有趣。不久又有聰明人出主意,以為應將一切文字說明刪除,只印圖像的,亦未能取得出版方面同意而擱置,一直擱下十七年,才有機會付印。
二、無從馴服的斑馬
《無從馴服的斑馬》是沈從文寫于一九八三年春的一篇未完成的作品。在這篇文章里,沈從文這樣總結自己的性格:“就我性格的必然,應付任何困難,一貫是沉默接受,既不灰心喪氣,也不呻吟哀嘆,只是因此,真像奇跡一樣,還是仍然活下來了。體質上雖然相當脆弱,性情上卻隨和中見板質,近于‘頑固不化的無從馴服的斑馬。”反觀親友懷念晚年沈從文的文章,多偏重言其溫厚、平易,而常忽略其性情中強烈以至極端的“板質”一面。我更為認同的是張新穎的評論,他這樣評價沈從文轉業后的人生階段:“一個知識分子實踐的階段,一個知識分子怎么在一個變動的時代過程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這個位置上安身立命。……是在精神的嚴酷磨礪過程中去追求意義和價值,苦難和整個創造事業的主動追求是緊密相連的。”強調“主動”而非“被動”,對于理解沈從文的最后生命階段十分關鍵。
張新穎把沈的轉業比作“鳳凰涅槃”。沈從文確實“死”過一次。據沈虎雛編撰的《沈從文年表簡編》所記,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旬,北京大學貼出一批聲討他的大標語和壁報,同時用壁報轉抄郭沫若《斥反動文藝》全文;時隔不久又收到恐嚇信,他預感到即使停筆,也必將受到無法忍受的清算。在強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一月中旬,發展成精神失常。”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上午,沈從文“用剃刀把自己頸子劃破,兩腕脈管也割傷,又喝了一些煤油”(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張兆和致田真逸、沈岳錕等),試圖自殺,幸被家人發現救下。四月六日,他在精神病院寫下了長長的日記,“在晨光中,世界或社會,必然從一個‘常而有繼續性中動著,發展著。我卻依然如游離于這個之外,而游離的延續,也就必然會帶來更多的纏縛。可我始終不明白我應擱在什么位置上為合適。”
在此之前,沈從文其實已逐漸明確自己與時代主流意識的分歧根源所在。“人近中年,情結凝固,又或因情結內向,缺少社交適應能力,用筆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時卻必須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這一代若干人必然結果。”(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七日,沈從文致吉六)據巴金回憶,沈從文說過巴金的“信念是空的”。(李輝:《與巴金談沈從文》,一九九○年五期《隨筆》)沈從文說過自己不懂政治,這或許可以解釋他在特殊時代環境下的失據,但其精神上淪入瘋毀的原由,根本應是:他無法去信一個“空”的東西。無法在時代洪流中找到一已立足之地,而又無法與之隨波同流,使他驚惶失措,“為什么一個人那么熱愛生命,恰恰就不能使生命用到一個與世諧同各遂其生的愿望下,將生命重作合理安排?”(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日記)
一九四九年八月,沈從文調入歷史博物館。“為補救改正,或放棄文學,來用史部雜知識和對于工藝美術的熱忱與理解,使之好好結合,來研究古代工藝美術史。”(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沈致丁玲)雖然面對的仍是艱苦的條件和動蕩的環境,但沈從文總算是找到了重新支撐起生命的東西。“我似乎第一次新發現了自己。”“我溫習到十六年來我們的過去,以及這半年中的自毀,與由瘋狂失常得來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樣,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預許的一樣,在把一只大而且舊的船作調頭努力,扭過來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致張兆和)“我愛這個國家,要努力把工作和歷史發展好好結合起來。”(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致張兆和)
自此,盡管外界干擾不斷,沈從文始終堅持自己的工作和抱負。一九五三年上海開明書店寫信通知沈,因為沈的作品已經陳舊過時,所以已將他的一切著作的紙型完全銷毀。與此同時,臺灣也查禁了沈的作品。沈的名字在大陸的文學史著作中實際上完全消失。到八十年代初也是如此。一九五六年,歷史博物館在內部舉行“反浪費展覽”,其中沈從文為公家廉價收購的一些文物被作為“廢品”展出。至一九五八年寫作《我為什么始終離不開歷史博物館》的時候,他在歷博約十八年作過“大小六十多次的檢討”。
下面這段引文常被用來說明沈從文的甘于平淡,但是恰恰相反,由這段文字可看出他內心究竟難平的波瀾,但也正因如此,三十余年的堅守和付出尤為可貴:
從生活表面來看,我可以說“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說不上了。不僅過去老友如丁玲,簡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鄭振鐸、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有名,十分活躍,出國飛來飛去,當成大賓。當時的我,天不亮即出門,在北新橋買個烤白薯暖手,坐電車到天安門時,門還不來,即坐下來看天空星月,開了門再進去。晚上回家,有時大雨,即披個破麻袋。我既從來不找他們,也無羨慕或自覺委屈處……
這些處境他都能平靜面對,王序說,沈從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權利。有一次,通知他去辦理從歷史博物館調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手續時,他誤以為是辦理退休手續,走進有關部門辦公室的門,他緊張得幾乎無所措手足,只是囁嚅著說:“我還能做點事,請不要讓我退休。”(凌宇:《沈從文傳》引子)王序又說,沈先生有時固執得讓人擔心。歷史博物館打算把他的書刪去文章單出圖,有人說建議沈去找江青姚文元,因為江青曾自稱是沈從文的學生,沈從文說寧愿不出書,也不找他們。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至今讀來從主題構想到語言風格上都很少沾染彼一時代的色彩。我原來視作尋常,直到讀到這一段,才知道并非容易。沈從文由“思”字出發的用筆方式,從文學寫作轉移到了文史研究中:
近人編《長沙出土楚漆器圖錄》,有摹繪展開復原圖。序言第五頁以為本圖內容反映的是當時仕女風俗畫,還近情理。又以為“反映出戰國時代貴族宮闈陰暗的一角”,因為“女子多細腰欲折,和古諺‘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的宮廷殘酷情況相適應”,意見實可商討。圖中有好幾位近似男性,不像女人。又因為畫面有一婦女,雙手分張,有一線橫貫兩手間,近似執鞭作嗔怒狀,即以為系教舞時虐待舞女情形,說明證據不足。就原物仔細分析,所謂鞭子,只是漆器上一道破裂痕跡。
與此相一致的是這部書“札記”式的結構,這不是一本結構完整的“中國歷代服裝史”,不是先有一個嚴密的理論體系精細的大綱,再來搜集資料,論證成書的。它是從大量的具體的歷史實物出發,進行先是個別的、然后是比較的研究,終于得到了某些帶有規律性的認識。正如黃裳所言,“完整的、嚴密的體系的形成也許還是將來的事。但現已露出地表的林立的樁腳都是結實的,多數是經得起考驗的,而且也已初步顯示出宏偉建筑的規模”。(黃裳:《沈從文和他的新書———讀〈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九八二年《讀書》)錢鐘書說過,古往今來,多少哲人建筑的理論大廈都傾塌了,只有瓦礫堆里的零星材料還可以供人使用。《管錐編》也是由零星材料組成的。一定程度上,“札記”也是文體中“無從馴服的斑馬”。那個時代“札記”式的寫作,似可看作某類思想方式和精神原則的隱喻。
寫到這,想起郭沫若為《服飾研究》作的序。在書未成稿之前,有次宴會沈先生與郭沫若鄰座,談到這本書,郭主動說:“我給你寫個序吧!”并很快就送來了。序成于書稿之前,郭未看過,故與內容不符。
三、抒情考古學
孫機先生稱此書為“中國服飾史的第一部通史”;沈從文卻這樣評價自己的著作:“內容材料雖有連續性,解釋說明卻缺少統一性。給人印象,總的看來雖具有一個長篇小說的規模,內容卻近似風格不一、分章敘事的散文。”(《服飾研究》引言)沈從文的弟子汪曾祺應是理解乃師的,“沈從文后來‘改行搞文物研究,樂此不疲,每日孜孜,一坐下去就是十幾個小時,也跟這點詩人氣質有關。他搞的那些東西,陶瓷、漆器、絲綢、服飾,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聰明,人的創造,人的藝術愛美心和堅持不懈的勞動。他說起這些東西時那樣興奮激動,贊嘆不已。樣子真是非常天真。他搞的文物工作,我真想給它起一個名字,叫做‘抒情考古學。”(汪曾祺:《沈從文的寂寞》)沈從文“能把抒情氣質和科學條理完美地結合起來”(汪曾祺:《沈從文轉業之謎》),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體現得最為明顯。
王序指出,沈從文做服飾研究,首要的工作就是為文物斷定時代,“先替后人把這個東西的時代準確性弄清”,“考察這個資料的可靠性”。(一九八五年王序王亞蓉答《光明日報》記者問)我們可以從書中看出沈從文為此做了大量工作。對許多為專家所不易判斷時代的畫幅,特別是人物故事畫,或有車乘馬匹日用家具的山水卷畫,沈從文從衣服制度和身旁攜帶日用家什等文物常識,得到許多有力旁證,從而幫助判斷出相對年代。沈先生說:“我始終留在博物館不動的原因,不是為了名、利、權、位……而是要解決一系列的所謂重要文物時代真偽問題。不是想做專家權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歷史上一切專家‘權威,破除對他們千年來造成的積習迷信。”(《我為什么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
有學者指出,沈先生利用出土文物等資料還解決了一些古代名物訓詁方面的難題,如衽、小山、便面、步障、捉鷹等。茲舉一例。《禮記·玉藻》中的“深衣三袪,……衽當旁”的“衽”,因鄭玄注過簡,成為古深衣制度中百注未解的問題。《服飾研究》中介紹江陵馬山戰國楚墓里發現的一件小菱紋絳地錦綿衣時,仔細說明了“縫于腋下的‘嵌片”就是“衽”,這恰可以解釋當時“衽”亦被用來稱綴合棺板的木榫。(董志翹:《〈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在名物訓詁方面的價值》)黃裳評論此書亦說,“如試將每章的研究內容各擬一題,那就將有《半臂考》《幞頭考》《關于‘啼妝》《哈巴狗的起源》《足球古史征》《唐代時妝的衍變》等許多小論文。”
沈生先的研究,不僅重實證,而且還重“常理”。古如書中常提到的“布障”,《世說新語·汰侈》:“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里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晉書·石崇傳》亦載:“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布障五十里以敵之”,對此歷來各家均無異議。沈從文在“南北朝寧懋石棺線刻各階層人物”一節中指出,所謂“步障”,實一重重用整幅絲綢做成,長約三五尺,應用方法,多是隨車乘行進,或在路旁交叉處阻擋行人。主要是遮隔路人窺視,或避風日沙塵,作用和掌扇差不多。《世說新語》記西晉豪富王愷、石崇斗富,一用紫絲步,一用錦步障,數目到三四十里,歷來不知步障形象,卻少有人懷疑這個延長三四十里的手執障子得用多少人來掌握,平常時候又得用多大倉庫來貯藏。如據畫刻所見,則“里”字當是“連”或“重”字誤寫。在另外同時關于步障記載,和《唐六典》關于帷賬記載,也可知當時必是若干“連”或“重”。
沈從文轉業雖然在許多人看起來像是“逼上梁山”,但對他來說卻并非全然沒有準備。早在一九三二年寫作的《從文自傳》時,他記述自己的童年,就已在追問:“為什么雕佛像會把木頭雕成人形。所貼的金那么薄又用什么方法作成?為什么小銅匠會在一塊銅板上鉆那么一個圓眼,刻花時刻得整整齊齊?”他在一九六一年的一篇未完稿中說道:
我從這方面對這個民族在長長的年份中,用一片顏色,一把線,一塊青銅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各種藝術,皆得了一個初步普遍的認識。由于這點初步知識,使一個以鑒賞人類生活與自然現象為生的鄉下人,進而對人類智慧光輝的領會,發生了極寬泛而深切的興味。(《抽象的抒情》)
他轉業前對文物的興趣,許多親友的回憶文章中都有記錄,以張充和的記敘最富生趣:
沈二哥最初由于廣泛地看文物字畫,以后漸漸轉向專門路子。在云南專收耿馬漆盒,在蘇州北平專收瓷器,他收集青花,遠在外國人注意之前。他雖喜歡收集,卻不據為己有,往往是送了人;送了,再買。后來又收集錦鍛絲綢,也無處不鉆,從正統《大藏經》的封面到三姐唯一的收藏宋拓集王圣教序的封面。他把一切圖案顏色及其相關處印在腦子里,卻不像守財者一樣,守住古董不放。大批大批的文物,如漆盒舊紙,都送給博物館,因為真正的財富是在他腦子里。
沈從文是個對一切留下生活印記的事物都有興趣,都會執著地進行觀察、思索、記錄的人。在西南聯大的時候,沈從文曾在昆明滇池邊鄉下住過很久,他就趁機會在那些來自四鄉裝備不同的馬背上,仔細觀察探索究竟,“結果明白不僅有犀皮漆云斑,還有五色相雜牛毛紋,正是宋代‘綺紋刷絲漆的作法。至于宋明鐵錯銀馬鐙,更是隨處可見。這些小發現,對我來說意義深長,因為明白‘由物證史的方法。此后應用到研究物質文化史和工藝圖案發展史,都可得到不少新發現。”(《記憶中的云南跑馬節》)
他欣賞的是工藝品中的“匠心”。“不同的為材料,一是石頭,頑固而堅硬的石頭,一是人生,復雜萬狀充滿可塑性的人生。可是不拘是石頭還是人生,若缺少那點創造者的‘匠心獨運,是不會成為特出藝術品的。(一九四一年《創作雜談》)
沈先生提及某種文物時常是贊嘆不已。馬王堆那副不到一兩重的紗衣,他不知說了多少次。刺繡用的金線原來是盲人用一把刀,全憑手感,就金箔上切割出來的。他說起時非常感動。有一個木偶(大概是楚俑)一尺多高,衣服非常特別:上衣的一半(連同袖子)是黑色,一半是紅的;下裝正好相反,一半是紅的,一半是黑的。沈先生說:“這真是現代派!”如果照這樣式(一點不用修改)做一件時裝,拿到巴黎去,由一個長身細腰的模特兒穿起來,到表演臺上轉那么一轉,準能把全巴黎都“鎮”了!(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董志翹先生曾去拜訪沈從文,沈先生在談話中“多次流露出對江青一伙的不滿,特別是對江青設計的所謂連衣裙,更斥之為‘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倫不類。”之所以有這樣的評價,正因為沈從文心中美的標準,是創作者的“心”。
沈從文文物研究的“詩性”或“抒情性”,最主要體現在他對“人”的關心。“有一點還想特別指出,即愛好的不僅僅是美術,還更愛那個產生動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種真正‘人的素樸的心。”(《關于云南漆器及其他》)還是張新穎說得好:
他的文物研究關注的是那些普通的東西,他從這些普通的東西上能夠看到普通人的生活,體會到普通人的情感。他對這個一往情深的。他看到銀瑣銀魚,會想到小銀匠一邊因事流淚,一面用小銅模敲擊花紋;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婦作手藝,能發現手藝人的情結和手藝之間的緊貼或者游離。他用心于工藝美術,用心于物質文化史,對普通人的哀樂和智慧“有情”,和一般的關注文人字畫什么的有很大距離。根本上看,這個文物研究的著眼點,其實也是他的文學的著眼點。
讀《服飾研究》也能感受到沈從文的“有情”,《敦煌壁畫唐代船夫摹本》一節中,他極自然便談到黃河三門峽地區船夫沉重而危險的負擔,“據《新唐書·食貨志》關于漕運部分記載,更遠比一般水邊驛運船夫慘劇。每天有成百上千船夫背牽上行,兩旁崖石鋒利如刀,每遇崖石割斷竹纜,船夫必隨同墜崖,斷頸折臂,死亡相繼。近年發現洛陽含喜倉遺跡,也多只知贊賞當時儲糧豐富,地下倉庫制度組織嚴密,卻少有人注意到年以數百萬石計的糧食轉運過程中,船夫的勞役是什么情形。”
這讓我想起一九三四年,沈從文回家鄉鳳凰途中寫給新婚不久的妻子的信:
我們平時不是讀歷史嗎?一本歷史書除了告我們些另一時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殺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歷史是一條河。從那日夜長流千古不變的水里石頭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爛的船板,使我觸著平時我們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類的哀樂!
“沈從文的物質文化史研究,是用自己的生命和情感來‘還原各種存留形式的生命和情感,‘恢復它們生動活潑的氣息和承啟流轉的性質,匯入歷史文化的長河。”(張新穎:《沈從文精讀》代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沈從文的文學創作與文史研究實是一回事,是一條長河的上下游。沈從文自己的生命也是一條河。他在三十歲的時候追溯自己的過去,寫下《從文自傳》,滿以為可為后半生準備好一個“自己”,卻不料走向了從未想過的道路。然而他卻讓這條生命之河在急轉之后流出了別樣的宏闊,從他的一生,讀者可知“生命流轉如水的可愛處”(《抽象的抒情》),及在特殊環境下個人重塑自身存在意義的可能。
自然既極博大,也極殘忍,戰勝一切,孕育人生。螻蟻昆蜉,偉大巨匠,一樣在它懷抱中,和光同塵。因新陳代謝,有華屋山丘。智者明白“現象”,不為困縛,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陸續失去意義,本身亦因死亡毫無意義時,使生命之火,煜煜照人,如燭如金。(《燭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