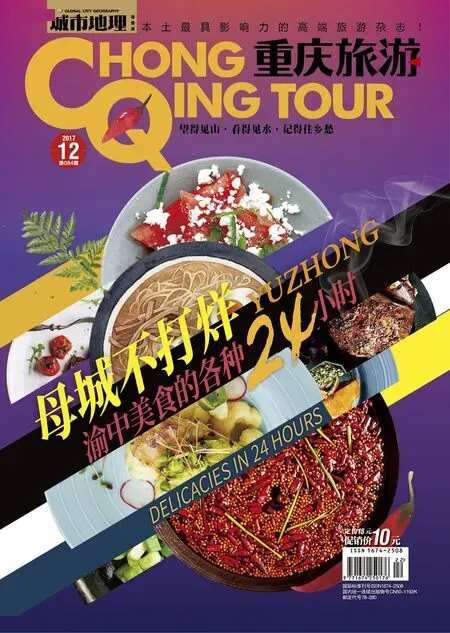鄂西土家族傳統(tǒng)民居建筑特色與保護(hù)研究初探
陳 鵬
(重慶大學(xué)建筑城規(guī)學(xué)院,重慶 400044)
傳統(tǒng)建筑是一個(gè)民族地域文化與社會(huì)生活的物質(zhì)載體,是記錄一個(gè)民族歷史發(fā)展的永恒記憶。研究傳統(tǒng)建筑是為了全面深入地探究傳統(tǒng)建筑所具備的地域文化特征,更清楚地了解建筑與民族地域性文化之間所蘊(yùn)含的深刻聯(lián)系,從而思索傳統(tǒng)建筑如何在社會(huì)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得到有效地保護(hù)與傳承。
鄂西土家族是一個(gè)有著悠久歷史的少數(shù)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中形成了自身獨(dú)特的地域文化與民族特色。土家族傳統(tǒng)民居具有其獨(dú)特的吊腳樓建筑形式,是其地理環(huán)境、功能結(jié)構(gòu)、建造技術(shù)、生活需求、宗教信仰和文化傳統(tǒng)等因素的綜合表達(dá),體現(xiàn)了其民族特有的精神內(nèi)涵與民族特質(zhì)。
1.選址與聚落結(jié)構(gòu)特征
鄂西土家族長期生活在中國湖北省西南部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處于湘、鄂、渝三省 (市)交界處的武陵山區(qū),這里山巒起伏,溝壑縱橫,形成極具特色的山地地形。鄂西土家族主要以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為主,同時(shí)兼顧上山伐木以及采藥,臨水又可漁獵,為生活提供便利。因此背山面水是土家族村寨選址的理想條件,基地背后的山巒可作冬季西北風(fēng)來時(shí)的屏障,面水則可迎接夏季南來的涼風(fēng)。為了節(jié)約更多可耕作的平坦空間,建筑依山而架在半山腰形成吊腳樓形式,或建造在壘筑的土臺(tái)上。同時(shí)擇坡而居,也是避免洪澇,保證良好日照的理想方式。
鄂西土家族一般以聚族而居為基礎(chǔ),整個(gè)村寨就是一個(gè)姓氏的大家族組成。因此土家族村寨多以十幾戶,幾十戶的組團(tuán)為主,每個(gè)組團(tuán)相對(duì)獨(dú)立,而組團(tuán)間彼此又有聯(lián)系。宗族關(guān)系影響著鄂西土家族的社會(huì)組織及等級(jí)制度,隨著私有制及財(cái)產(chǎn)繼承關(guān)系的出現(xiàn)而得到進(jìn)一步發(fā)展。在聚落形態(tài)上往往出現(xiàn)了宗祠為核心而形成的節(jié)點(diǎn)式的公共活動(dòng)中心。尤其是一些歷史較為悠久的大型聚落,這種結(jié)構(gòu)更為復(fù)雜而具有層次。例如利川大水井古建筑群,以李氏祠堂為中心,李氏莊園為副中心而形成具有秩序性,中心性的聚落結(jié)構(gòu),反映出不同層次的宗族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1]。
因?yàn)樯降氐匦蔚膹?fù)雜性,鄂西土家族聚落形態(tài)靈活多變,依山就勢(shì),往往形成自由的線狀布局。建筑平行于等高線連續(xù)布置,道路順應(yīng)地形以幾戶、十幾戶為單位串聯(lián)成線,戶與戶之間有間隙,形成各自的領(lǐng)域界限,不同高程之間各自形成群組,但又聯(lián)系緊密。每隔一段距離便設(shè)置垂直于等高線的道路,以連接不同高程,同時(shí)在兩側(cè)設(shè)明溝排水。聚落結(jié)構(gòu)連續(xù)明確而有方向性,同時(shí)曲折蜿蜒,起伏而有韻律感,體現(xiàn)出一直樸實(shí)的原始美感。
2.建筑空間特征
鄂西土家族吊腳樓的傳統(tǒng)特征之一是以堂屋與火塘間為核心的空間組織形式。堂屋既為人用,也為神居,是居住者的公共活動(dòng)空間,一般供敬神、祭祖、舉行婚喪、壽慶、宴請(qǐng)賓客及平時(shí)接待賓客好友等活動(dòng)之用,是人神對(duì)話的空間媒介[2]。堂屋一般是開放的半室外空間,兩層通高顯得開敞而高大,以一種歡迎的姿態(tài)位于建筑的中軸線上,各個(gè)空間圍繞其展開。土家族民居一般都設(shè)有火塘間,位于堂屋一側(cè)。火塘間一般大概9米見方,主要有取暖御寒、烘干衣物、家庭娛樂聚會(huì)等功能,現(xiàn)在許多土家族居民把電視等設(shè)施放置于火塘間,使之用途更為豐富。
土家族吊腳樓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一般分上中下三層,坡地處吊腳形成為飼養(yǎng)牲畜或者放置雜物的下層空間,中間平層為居住空間,第三層用于儲(chǔ)存谷物農(nóng)具等,各層之間以木梯連接。根據(jù)地形、功能需求、經(jīng)濟(jì)情況以及審美意識(shí)的不同,每個(gè)吊腳樓會(huì)呈現(xiàn)出不同的形式。但是總的來說,在實(shí)際建造中,往往以幾種基本形式為摹本,衍生出其他相似的類型。
“一”字型:“一”字型為土家族最基本的吊腳樓形式,開間按一字形橫向排列,一般為3至5開間,每棟房屋的開間基本是單數(shù)。堂屋位于正中間,兩側(cè)為“人間” (或稱“房屋”、“人住間”)。“人間”常用板壁隔為前后兩間,前一間為火塘間,后一間則是臥房,為休息及儲(chǔ)物用。若為5開間及以上房屋,緊接著人間一側(cè)則會(huì)設(shè)置具有廚房、貯物及用餐房間。民居正屋兩端或背后常搭有坡屋,作為飼養(yǎng)牲口堆放雜物或廁所之用。
“L”型或“鑰匙頭”型:這種吊腳樓在“一”字型基礎(chǔ)上,在某一端向前加設(shè)一兩間“人間”,被稱作“龕子”,根據(jù)地形或形成吊腳。吊腳樓上層為廂房,外設(shè)挑廊,底層則架空或稍加圍隔作為儲(chǔ)存雜物或飼養(yǎng)牲口的空間。吊腳樓一般為兩開間,其進(jìn)深比正房的進(jìn)深小。這種形式具備一定的圍合意向,是土家族民居較常見的形式。
“凹”字型或三合水型:這種形式的住宅是在“一”字型基礎(chǔ)上,將兩端的“人間”吊腳,形成一正兩廂的形式。由于有兩端吊腳,因此也被稱為“雙吊式”。室外空間由三面建筑所圍合,封閉性更強(qiáng),更強(qiáng)調(diào)了場(chǎng)所感與領(lǐng)域感。形式上的對(duì)稱,顯示出其更莊重的性格。
“回”字型或四合水型:也是土家族俗稱的“印子房”,是以中軸線對(duì)稱,圍繞天井形成完全封閉宅院的中國傳統(tǒng)形式,具有一定自我防衛(wèi)能力,通常以大戶人家為主,根據(jù)院落天井的多少形成“三進(jìn)二亭” “四進(jìn)三亭” “五進(jìn)四亭”等形式。常見的是“三進(jìn)二亭”,建筑平面非常緊湊,以三開間為主,入口設(shè)門廳,天井內(nèi)院后面為正廳,正廳兩旁為廂房[3]。
3.建筑美學(xué)特征
鄂西土家族的傳統(tǒng)民居為純木結(jié)構(gòu),多為穿斗式,柱、梁、枋、檁等構(gòu)件以榫卯銜接,相互穿插搭接形成一個(gè)整體。當(dāng)?shù)亓?xí)慣把落地的支撐結(jié)構(gòu)稱為“柱”,把落在梁枋上的稱為“騎”,常見的有三柱四騎、三柱六騎、五柱六騎、五柱八騎等結(jié)構(gòu)[2]。建筑以木壁板作為圍護(hù)結(jié)構(gòu),壁板常縱向鋪設(shè)以分割空間,壁板多為長方形木板,長度視建筑高度而定,寬度約10厘米左右。雕花鏤空的木窗框嵌于壁板間,形成虛實(shí)變化。屋頂為歇山式坡屋頂,整體較為平整,而吊腳樓處的翼角會(huì)有明顯起翹,有向上飛升之勢(shì),使得建筑具有一種平緩舒展而又輕盈活潑的姿態(tài)。建筑尺度親切宜人,整體形態(tài)橫向舒展,匍匐于大地,與場(chǎng)地融為一體。而建筑的吊腳形式使其又像是微微地懸浮于大地之上,輕盈而自在。“座子屋”與“龕子”的自由組合,使得建筑千棟自別,相互競(jìng)秀。同時(shí)建筑布局自由,依山而筑,鱗次櫛比而有錯(cuò)落有致,使得建筑群落形成一個(gè)優(yōu)美而豐富的整體景觀。
土家族民居的建筑美學(xué)不僅體現(xiàn)在其優(yōu)雅輕盈的建筑形態(tài)上,更表現(xiàn)在其精美的細(xì)部裝飾上。土家族建筑的細(xì)部裝飾秉承了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藝術(shù)精髓,同時(shí)也具有其質(zhì)樸的民族特色。其細(xì)部裝飾的構(gòu)圖飽滿對(duì)稱,體裁多種多樣,造型精致有趣,是其文化、生活、宗教信仰的具體表現(xiàn)。
3.1門窗
土家族建筑的門窗裝飾雖不及徽派建筑的富貴繁復(fù),卻體現(xiàn)出其自然質(zhì)樸的特點(diǎn)。建筑正中堂屋或不設(shè)門,為半開敞空間,或設(shè)六合門,兩兩成對(duì)組成三對(duì)大門,在上下門中安裝門軸。門扇一般用木板拼成雕花門,其裝飾表現(xiàn)在其兩端的透雕或浮雕梭子話,中間則做成樣式豐富的門窗[4]。
窗戶在滿足其通風(fēng)采光的功能性的同時(shí)被賦予了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窗戶以正方形或長方形為主,根據(jù)功能需求有單個(gè)的也有兩三成組的。窗戶的裝飾樣式繁多,有“王字格”、“步步緊”、“萬字格”、“壽字格”等,形成上下左右對(duì)稱形式,中間為含有對(duì)幸福生活的美好祝愿,或表達(dá)敬重自然的文化寓意的各種精美圖案,豐富多彩,栩栩如生。
3.2屋脊
屋脊的裝飾也體現(xiàn)出土家族建筑的美學(xué)特點(diǎn)。建筑的屋脊由瓦片堆砌而成,屋脊中間的裝飾往往由兩片瓦片形成的葉狀格子為基本單位,組成“品”字型。“品”字型兩側(cè)則以瓦片依次排放,直至擺滿整條屋脊[5]。除此之外其屋脊頂飾還有各種不同形式,如四片瓦組成的古錢式,五片瓦組成的五角形,以及更為復(fù)雜的“福”、“壽”等字形。屋脊末端通常是一些簡單的翹腳,或用瓦片抬高,部分民居堆成簡單樸素的“回花脊”。整個(gè)屋脊不設(shè)脊獸,形式簡潔大方,質(zhì)樸親切。
3.3欄桿、檐柱
欄桿是吊腳樓重要的組成構(gòu)件,隨挑廊一起圍繞建筑的“龕子”形成一條裝飾性的線型空間。其鏤空的藝術(shù)處理手法與建筑木壁板形成虛實(shí)對(duì)比,突出了建筑懸浮于地上的輕盈之感。欄桿的樣式根據(jù)居民的財(cái)力與偏好各有不同,常見的有方柱式、圓柱式、“回”字格、“喜”字格、“亞”字格等有些欄桿,還在中央制作裝飾性的“美人靠”,來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欄桿實(shí)用性和形式美感[6]。
檐柱主要在其柱頭上進(jìn)行吊瓜的裝飾形式,即把柱頭雕刻成一個(gè)飽滿的“金瓜”形狀,形式多樣,或精美細(xì)膩或簡潔大方。其柱身根據(jù)不同需求,或形成回紋和龍鳳紋的裝飾形式。
4.傳統(tǒng)建筑保護(hù)與傳承的現(xiàn)狀與反思
鄂西土家族傳統(tǒng)民居的建筑形式與技藝是當(dāng)?shù)鼐用駥?duì)居住環(huán)境,建造材料等因素綜合考慮,長期的探索與創(chuàng)造,而形成的一種與其宗教文化、社會(huì)生活、自然環(huán)境相適應(yīng)的建筑形式,具有特色鮮明的本土性。但隨著社會(huì)發(fā)展,生活需求的變化,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沖擊使得傳統(tǒng)建筑的保護(hù)與傳承成為棘手問題。筆者以實(shí)地調(diào)研為基礎(chǔ)整理出三種當(dāng)前鄂西傳統(tǒng)建筑保護(hù)與傳承所呈現(xiàn)出的現(xiàn)狀與問題。
4.1原始村落保護(hù)區(qū)
以保存相對(duì)完好的原始村落為基礎(chǔ),以“整舊如舊”式修葺為手段,以整體式保護(hù)為策略形成原始村落保護(hù)區(qū)。以湖北恩施自治州宣恩縣的彭家寨為例。彭家寨作為第四批“中國歷史文化名村”,湖北省“重點(diǎn)文物保護(hù)單位”,也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命名的20個(gè)民族民間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之一[7]。村落的保護(hù)主要以政府主導(dǎo),制定法律法規(guī)與發(fā)展計(jì)劃,投入資金,進(jìn)行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同時(shí)兼顧作為文化載體的村民的參與與互動(dòng)的“合作式保護(hù)開發(fā)”模式,整個(gè)村落的傳統(tǒng)建筑與聚落結(jié)構(gòu)基本以原始形態(tài)完好地保存下來。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現(xiàn)代生活需求的變化,使得部分建筑內(nèi)部裝修風(fēng)格發(fā)生變化.大量現(xiàn)代風(fēng)格的家具被應(yīng)用,部分建筑內(nèi)部鋪成了瓷磚地板。同時(shí)由于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變,土家族村民已經(jīng)由畜牧業(yè)轉(zhuǎn)向農(nóng)業(yè)。吊腳樓下方的空間或圍合成房間以存放雜物。
雖然彭家寨建筑群落的保護(hù)非常成功,但這種以政府為主導(dǎo)的保護(hù)區(qū)式的保護(hù)政策同樣存在些隱患。政府的經(jīng)濟(jì)補(bǔ)助不能夠帶給居民長期的生活發(fā)展,生活條件、教育條件等不足,外來文化的沖擊,發(fā)展的滯后性都進(jìn)一步使得傳統(tǒng)村落人口流失,村民的保護(hù)意識(shí)不強(qiáng)。
4.2現(xiàn)代化的土家族“小洋樓”
當(dāng)前大多數(shù)受到現(xiàn)代化影響的鄂西土家族村民自發(fā)修建的新住宅,已經(jīng)放棄了木結(jié)構(gòu)的傳統(tǒng)吊腳樓形式,而更多的是采用鋼筋混凝土框架結(jié)構(gòu)的現(xiàn)代建筑形式。這種低成本、施工方便、建造速度快、堅(jiān)固實(shí)用的現(xiàn)代建筑更適應(yīng)了當(dāng)?shù)鼐用袢遮吀淖兊默F(xiàn)代生活需求。雖然當(dāng)?shù)鼐用裨谛伦≌奶幚砩蠒?huì)繼承一些傳統(tǒng)建筑的元素。在空間上,以堂屋為中心的對(duì)稱布局,在二三層會(huì)模仿“雙吊式”突出兩側(cè)建筑體量。在裝飾上,門窗往往采用以傳統(tǒng)樣式為主的木門窗,屋頂仍以傳統(tǒng)坡屋頂為主,加以裝飾性的挑檐。但其白色涂料粉刷或以瓷磚貼面的外墻裝飾,各種西式風(fēng)格的欄桿,各種傳統(tǒng)建筑元素的雜揉,以及毫無個(gè)性的建筑細(xì)部都凸顯出這種現(xiàn)代化“小洋樓”本土性與傳統(tǒng)性的缺失。
4.3景區(qū)仿古建筑
最近二十年,仿古建筑熱這一熱潮席卷了中國眾多名勝古跡。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它體現(xiàn)了國內(nèi)一種對(duì)于傳統(tǒng)文化,民族認(rèn)同感以及精神世界的訴求,然而仿古建筑的泛濫化、同一化、劣質(zhì)化也是問題所在。大多數(shù)仿古建筑只是打著傳統(tǒng)文化的旗號(hào),以謀求經(jīng)濟(jì)利益最大化。例如恩施土家女兒城,大多數(shù)建筑都是典型的現(xiàn)代建筑加以拙劣的傳統(tǒng)元素裝飾。建筑尺度形制單一,并沒有傳統(tǒng)土家族建筑小巧玲瓏之感。建筑屋頂、挑檐、椽子都是以混凝土澆筑,形成拙劣的模仿,其翹角轉(zhuǎn)折十分突兀。其梁枋、檐柱的圖案裝飾同樣不倫不類。整個(gè)建筑群雜糅了各種文化元素,消解了土家族傳統(tǒng)建筑文化特性,混淆了游客的知識(shí)結(jié)構(gòu)。
4.4保護(hù)與傳承
原始村落保護(hù)區(qū)的保護(hù)形式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完整的傳統(tǒng)建筑及其場(chǎng)所精神,以完全尊重傳統(tǒng)建筑真實(shí)性的方式來實(shí)現(xiàn)對(duì)物質(zhì)文化的傳承。這種模式能真切而清晰地展現(xiàn)鄂西傳統(tǒng)民居最原始的建構(gòu)關(guān)系,但卻難以順應(yīng)社會(huì)的發(fā)展。大量自發(fā)建造的現(xiàn)代建筑即是土家族人對(duì)生活觀念與社會(huì)文化風(fēng)俗的變化的訴求。這種異化的傳統(tǒng)民居以現(xiàn)代建造體系為支撐,建筑的經(jīng)濟(jì)性與自由度更強(qiáng),滿足了土家族的新的生活需求,但同時(shí)卻催生了建筑視覺與建筑本體的分裂。建筑的形態(tài)與結(jié)構(gòu)的分離,裝飾特色以符號(hào)化的形式簡單粗糙地被貼附于建筑表面,不再與材料,構(gòu)造方法相關(guān)聯(lián)。
在筆者看來,原始村落保護(hù)區(qū)形式是對(duì)傳統(tǒng)建筑以及傳統(tǒng)文化最尊重的一種保護(hù)形式,但是這是一種停滯的保護(hù)策略。保護(hù)區(qū)如同傳統(tǒng)文化的博物館,是其文化遺產(chǎn)得以保留與考證的場(chǎng)所。但這種模式只能是文化保護(hù)的一部分,真正的保護(hù)與傳承應(yīng)該是建筑對(duì)社會(huì)發(fā)展做出積極而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回應(yīng)。新建筑應(yīng)該在滿足土家族新的生活需求的同時(shí),增加建筑的可識(shí)別性,塑造可識(shí)別的土家族村落建筑風(fēng)貌。但這種可識(shí)別性,不應(yīng)該是傳統(tǒng)裝飾的符號(hào)化拼貼,而是對(duì)其文化內(nèi)涵進(jìn)行深入研究后的抽象提取,不只是對(duì)建筑形的模仿,更是對(duì)建筑神的刻畫。應(yīng)該從建筑的形態(tài),空間,材料與細(xì)部裝飾、建構(gòu)方式的關(guān)系角度出發(fā),同時(shí)結(jié)合所處的自然環(huán)境等綜合因素,去理解與探究傳統(tǒng)建筑所具有的建筑神韻與場(chǎng)所精神。建筑的傳統(tǒng)性與民族性的保護(hù)與傳承應(yīng)以演變的視角去看待,在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的基礎(chǔ)上,與社會(huì)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有機(jī)結(jié)合,才是傳統(tǒng)建筑得以持續(xù)發(fā)展的有效途徑。
[1]胡平.鄂西傳統(tǒng)民居聚落影響因素分析 [D].武漢:華中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園藝林學(xué)學(xué)院,2008.
[2]歐陽玉.從鄂西山村彭家寨現(xiàn)狀的調(diào)查兼議山村傳統(tǒng)聚落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D].武漢:武漢大學(xué),2005.
[3]羅仙佳.鄂西土家族傳統(tǒng)民居建筑美學(xué)特征研究 [D].武漢:武漢大學(xué),2005.
[4]王思喆.論彭家寨吊腳樓的特色與傳承 [D].武漢:武漢理工大學(xué),2014.
[5]辛克靖.族群·聚落·民族建筑——國際人類學(xué)與民族學(xué)聯(lián)合會(huì)第十六屆世界大會(huì)專題會(huì)議論文集[C].云南:云南大學(xué)出版社,2010.
[6]周傳發(fā).論鄂西土家族傳統(tǒng)民居藝術(shù)的審美特色 [J].重慶建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8,30(1):13-16.
[7]彭英明.土家族文化通志新編[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