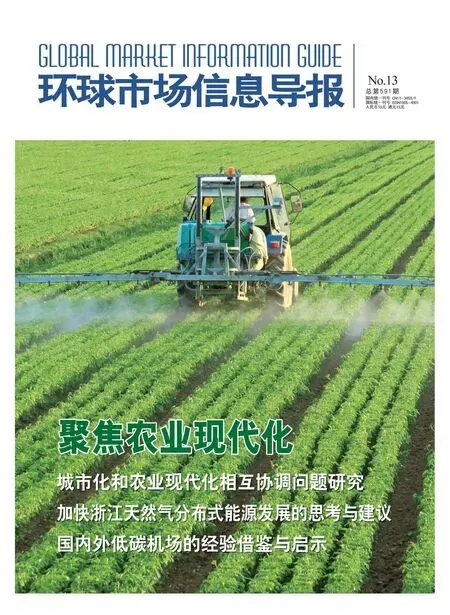“十億城民”背景下基礎設施建設標準的思考
■劉 云/文
“十億城民”背景下基礎設施建設標準的思考
■劉云/文
一、京滬高鐵運能提前飽和
近期,關于京滬高鐵2014年盈利的消息引起海內外關注。京滬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表示:“高鐵運營難盈利的一般規律,硬是被京滬高鐵打破了。當初預計的是運營5年后,逐漸達到盈虧平衡,之后用14年還本付息。”
“去年京滬高鐵發送旅客突破1億人次,日均超過250列高鐵列車運行,就這樣還是不能滿足高峰時期旅客出行需求,照這樣發展,說不定哪天就要修建京滬第二高鐵了。”
按照此說法,京滬高鐵運能己提前數年進入飽和狀態,應考慮修建京滬第二高鐵。
無獨有偶,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鐵路總公司負責人在全國“兩會”的政協經濟界分組討論時透露,中國東部沿海地區高鐵,包括京津城際、京滬、滬寧、滬杭、杭深、廣深等全面實現盈利,京津、長三角、珠三角這三個區域的高鐵線路能力已接近飽和。從目前來看,日常高鐵的運能還說得過去,但一到節假日,這些高鐵線路“一票難求”的現象又出現了。
一般來說,一條高鐵線路日均運行100對就基本飽和,但現在京津城際高鐵最高每天運行108對,京滬113對,京廣某些區段126對,滬杭某些區段108對,都已經超出運載量。因此,要提早規劃這三個地區未來高鐵的建設,某些重點區段可能再建第二條、甚至第三條高鐵,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出行需求。
二、首都國際機場與三峽船閘成為“瓶頸”
北京新機場工程已于2014年底開工,之所以要建北京新機場,是因為現有的首都國際機場的旅客吞吐量已經超過了設計時的8000萬人次,并且仍在不斷攀升。如果不及早開建新機場,首都機場將不堪重負。
另外,在2015年全國“兩會”上,也有全國人大代表表示,三峽船閘的通航規模是上世紀80年代論證確定的,當時,三峽船閘設計通過能力為雙向1億噸/ 年,預計2030年達到設計通過能力。但隨著長江水路貨運量大幅增加,早在2011年,通過三峽船閘的貨運量就達到了1億噸,提前19年達到了設計通過能力。目前年過閘量已接近1.2億噸,超過設計通過能力20%。這表明長江航運發展的速度之快,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期。現在三峽船閘已經處于過飽和運行狀態,由于通行船只數量超限,過閘船舶擁堵嚴重,下水船要等待約30小時,上水等待長達60小時。
盡管交通部門千方百計挖掘通航潛力,但挖潛空間有限。目前,國務院三峽辦正在牽頭組織開展船閘擴能前期研究工作。

三、長安街寬度規劃的前車之鑒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北京市決定拓寬東西長安街,那么新的長安街寬度應定為多少米?當時北京汽車很少,人口才200多萬,所有參與規劃設計的人員都認為,50米寬足夠了,還有人主張40米寬就夠了。但當時北京市市長彭真卻力排眾議,把長安街寬度定為80米,并解釋說,作為一個大國的首都,幾十年后北京人口將突破千萬大關,汽車可能多達幾十萬輛。但當時無人相信彭真的“預測”,私下視之為“天方夜潭”式笑話。盡管當時很多人反對,但彭真市長憑借科學判斷和預測,實施了自己的決定。如今北京的汽車多達500多萬輛,常駐人口突破2000萬大關。即使當初被視為“天方夜潭”式的彭真市長“預測”,現在看來也過于保守。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中后期,長安街擁堵就日趨嚴重,當時北京市政府就想把長安街拓寬到100米至120米寬,但由于沿線拆遷費過高,數次議而不決,錯過了寶貴的時間。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拆遷費隨房價而呈數十倍的暴漲,如今長安街兩側寸土寸金的地價與天價拆遷費己使拓寬長安街完全沒有可能。現在寬度恐怕己永久定型,整個北京交通都將為長安街超擁堵付出巨大的代價。
四、對“中國十億城民”巨大出行需求的預測宜高不宜低
北京人口的急速膨脹反映了中國快速城市化進程,2013年2月,長期生活在中國的英國記者湯姆米勒出版了一本書,名為《中國十億城民: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移居背后的故事》。書中稱,中國的城市化產生了令人瞠目的數據,過去30年中國有5億人遷入城市,從鞍山到鄭州,一些外人幾乎沒聽說過的城市高樓林立,到2030年中國城市人口將占全球人口的1/8,屆時,中國將擁有“十億城民”。麥肯錫2009年發布的《為中國10億城市人口做好準備》報告也預測,到2025年,中國將新增城鎮人口3.5億,約等于美國的總人口,將新增221個超過百萬人的城市。也就是說麥肯錫把中國進入“十億城民”時代又提前了5年,即2025年。
“十億城民”相當于歐盟與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四國人口總和,或者說相當于西方發達國家人口總和,其數量之龐大真是到了令西方人目瞪口呆的程度。所謂“城民”(即城市居民)與“鄉民”(農村居民)區別之一是出行次數的多少,“城民”為了求學、就業、工作、出差、旅游、出國等目的出行次數比“鄉民”要多得多。
2014年高鐵的發送旅客達到了9.08億人次,高鐵的客流增長了35.1%,占了全部旅客發送量的40%,創歷史新高。為何創歷史新高?中國快速城市化所導致的“城民”迅速增長是一個很重要因素。至于中國到2030年是否有“十億城民”,還有待觀察,但國內一些研究者也得出類似的結論,所以“十億城民”預測是靠譜的,不會與實際數字相差太大,或許還會更多。“十億城民”給中國帶來的挑戰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巨大的出行量給中國交通帶來嚴峻挑戰,唯有高速、大運量的高鐵網絡才能應對“十億城民”巨大的出行量。

五、高鐵建設標準宜高不宜低
目前,中國高鐵的在建里程高達上萬公里,那么中國高鐵建設會不會出現與京滬高鐵、三峽船閘、首都國際機場類似的問題,即建成通車或運營后不久,運能就處于飽和狀態,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這種可能是完全存在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應從中吸取教訓,未雨綢繆,早做應對。
在2011年“7·23”溫州動車追尾事故之前,原鐵道部在高鐵線路建設上一直推行高標準,要求按350公里乃至400公里時速的高標準來建設。但在動車追尾事故后,不少在建與待建高鐵線路建設標準大幅降低,由以前確定的350公里乃至400公里時速的建設標準,降低為250公里甚至200公里時速建設標準。而降低建高鐵時速建設標準所帶來的無窮后患,將超出很多人的估計與想像,很有可能重蹈首都國際機場、三峽船閘與長安街因規劃標準偏低而成“瓶頸”的覆轍。
不僅是京滬高鐵,全國所有高鐵線路客流量正迅速上升。經常坐高鐵的乘客都有這樣的體會,所有高鐵線路剛開通時尚可隨到隨買隨走,而現在不少車次不提前預訂根本買不到票,有些熱門線路和車次己到了人滿為患的程度,有時連站票都買不到。
2014年,高鐵的旅客量增長超過三成。按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也許到2020年前后,全國所有高鐵都將像京滬高鐵那樣處于滿負荷運行狀態,到2030年“十億城民”時代,全國高鐵即使除節假日之外的平時也將人滿為患,高鐵運能將無法滿足“十億城民”巨大的出行需求。那時增加高鐵運能最有效手段是提速,如把京滬高鐵由目前300公里運營時速提高到350公里(即京滬高鐵開通之初運營速度),則京滬高鐵運能能增加四分之一,且鐵路部門為此增加的運營成本不多。所以從長遠看,京滬高鐵380公里時速建造標準是必要的。
較之于高標準的京滬高鐵,廈門至深圳的廈深高鐵則是因為偏低的建設標準而形成運能制約運量的反面典型。廈深高鐵不僅聯結廈門與深圳兩個經濟特區,而且是聯結福建與廣東兩省唯一的鐵路線路,其運量的巨大需求是不言而喻的。自2013年底開通以來,基本上處于趟趟滿座狀況。廈深高鐵大概是全國首條開通后就處于運能滯后于運量的高鐵,由于廈深高鐵車次密度己接近飽和,想通過增加車次密度來提高運能己無多大潛力,想通過提速來提高運能也無多大潛力。因為廈深高鐵建設標準為最高時速250公里,比京滬高鐵低得多,出于安全考慮必須降速運行,正常運營時速為每小時200公里,而當前的發車密度為每天34對車,很難再有大幅提升。于是廈深高鐵陷入車次難增加、速度難提升的尷尬處境,成為全國高鐵網絡中第一個卡脖子的線路,其負面影響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趨嚴重。

其實高鐵線路建設標準與當年首都國際機場、三峽船閘、長安街寬度規劃有類似,如果現在把高鐵線路建設標準,由“7·23”動車追尾事故前的350公里至400公里時速,降為降低為250公里甚至200公里時速建設標準,再過五六年,即2020年前后,其后果就會顯現出來,那時再想提高線路速度標準,其難度如同現在去拓寬長安街,要么不可能,要么要付出難以承受的巨大代價,那真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重蹈長安街寬度規劃的覆轍。
“鄉民”對高鐵等基礎設施的依賴和需求比“城民”低得多,現在中國包括流動人口在內的“城民”約為7.5億,就出現了部份基礎設施提前飽和與瓶頸現象。不難想象,將來在城市集中生活的“十億城民”對道路、高鐵、水電氣等基礎設施的巨大需求很可能超出決策者、規劃者的預計與想象,城市的基礎設施將不堪重負。因為世界城市化歷史上從未有“十億城民”的先例,我們不能參照國外經驗來預測“十億城民”對基礎設施的巨大需求,在基礎設施規劃上適度超前和從長計議非常必要,高鐵是如此,其它基礎設施也是如此。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