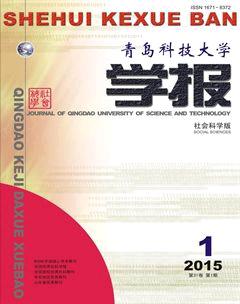文化區隔與政治分離
林超
[摘 要]民族主義多元文化論是建立在民族主義基礎上的多元單一文化論,它把原本主張文化自由與文化包容的多元文化主義簡單化和狹隘化了。民族主義多元文化論通過濃墨重彩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性、訴諸單一文化身份歸類和主張建立以社群為基礎的排他性自治政府的制度安排,而人為固化了民族文化間的差異。這種做法既無視文化之間的普遍聯系與交流融合的客觀實際,也嚴重干擾了個體的文化自由;不僅無助于實現多族群社會的多元和諧與差異共存,也極易產生事實上的文化“隔離”,進而誘發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對立和沖突。
[關鍵詞]民族主義多元文化論;文化區隔;政治分離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372(2015)01-0047-06
Abstract:Nationalistic multiculturalism is a type of plural monoculturalism based on nationalism. It makes multiculturalism, which originally advocates cultural freedom and cultural tolerance, be simplified and narrow. With much emphasis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ational cultures, and by resorting to a single cultural identity, the nationalistic multiculturalism advoc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xclusive community-based self-government to solidify cultural differences. This kind of practice not only ignores the reality of the common link and the interaction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but also seriously disturbs the cultural freedom of individuals; it is not conducive to a multi-ethnic social harmony and co-existence of differences,but easy to produce cultural “isolation”, and then induce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al groups.
Key words:nationalistic multiculturalism; the distinction of culture; 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s
多元文化社會如何實現差異共存是關系到社會穩定與文化發展的大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多元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很容易引起文化沖突與群體互斥。所以,對多元文化關系理論的研究和探索,無論在學術還是在現實意義等方面都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然而民族主義多元文化論的理論邏輯、政策主張和實踐效果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生動例證,說明糟糕的推理,如何能夠使人們在一種狹隘、割裂的多元單一文化觀①的支配下作繭自縛[1]。因此,如果我們認為多元文化主義對于促進文化間的交流與包容、發展群際和諧以及鞏固社會團結是好的,那么我們就有必要深入反思和檢討建立在社群主義基礎上的以區隔文化和分裂主義為特點的民族主義多元文化論,并將之與尊重個體文化自由、文化個性,并肯定文化交往交流價值的多元文化主義區別開來。
一、文化區隔與固化差異
民族主義者認為社群要比構成它的個體重要。他們主張為了保護少數族群本身的特色文化不被其他文化“侵染”和“同化”,國家應該按照族群身份的界線樹立起一道防止文化交往交流的政策隔離墻,并把(他們自認為)是族群成員最佳的傳統生活觀念強加給區隔到不同族群文化盒子里的公民,以維護族群文化的純潔。因此,民族主義者所主張的多元文化政策雖然一方面強調要給予不同社群文化以“自由展示”的機會,并由政府提供經濟支持以“扶持發展”;另一方面,其潛在的功能則是固化、強化不同文化的差異性,妨礙了文化的正常交流和更新[2]。我們常聽到某些文化保守主義者聲稱如果沒有對內部成員的言論、出版、宗教等方面自由的約束,他們的文化將會瓦解[3]160。在這種解釋中,“文化”是根據通常用來表示它的特性的規范被定義的。所以依據定義,對族群宗教、習俗的任何重要變更就都是對舊“文化”的“破壞”[3]160-161。這種社群主義文化主張存在的問題在于,它只是把一個群體內部不喜歡變化和文化交流的人的偏好當做認為社會的存在處在危險中的充足理由[3]161。但這顯然侵犯了許多想過其他理想文化生活的人們的文化自由。因此,只根據一部分人的保守文化偏好所制定的抵御文化特性變化的政策保護,不能被看做是對人們文化選擇能力的保護。相反,而應被看做是以一部分人的保守文化偏好對其他人文化選擇能力單方面施加的一種限制[3]159-160。對此,即使是積極主張保護少數群體文化權利的金里卡也不認可這種主張。他認為,“每個人都有追求他自認為合適的生活的公民和政治自由的廣闊天地。在認為最佳的社群是一個取締除他們自己喜歡的宗教的、性的、審美的實踐之外的一切實踐的社群的所有這類政治和宗教人士中,無疑有許多原教旨主義者。但是文化成員身份作為基本善的概念卻沒有給他們提供任何支持。因為只要每個人在他歸屬的社群內有自己應得的一份資源和追求自己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那么文化成員身份的基本善就得到了恰當的認可。在這些環境中推進原教旨主義的政綱,遠非是對文化成員身份的基本善的訴諸,而是與它的基本善沖突的。因為這樣做破壞了我們之所以贊成關注文化成員身份的那個理由,即對有意義的個人選擇的許可”[3]164-165。他舉例說,在普韋布洛(Pueblo)印第安人居留地的每個成員,他們生活在社群中的能力并不會受到允許本族新教徒成員表達他們宗教信仰的威脅[3]188。因而這里并不存在文化成員身份引起的不平等。所以,“當印第安居留地否認了少數派的宗教自由時,支持多數顯然就是在支持對他人施以羞辱和不正義的傷害”[3]188。
金里卡認為,我們能夠認同、保護和增進作為一個基本善的文化成員身份,而不必接受社群主義理論家要求保護一個既定文化社群特性的主張[3]162。即使當某些自由權的確破壞了一個社群的存在,我們所允許的某些反自由主義的措施,也只能當做是暫時性的措施以緩和由于文化特性過于急促的變化造成的社會震動。并且這種反自由的暫時性措施只有在幫助文化謹慎地朝一個充分自由主義的社會邁進時,才是正當的[3]163。
從歷史角度來看,民族主義保守封閉、固化差異的文化主張也嚴重無視了人類文化不斷融合發展的歷史事實。世界文化的多元化的確是人類自古已存在的文化形式,但人類文化總是在交流融合中不斷發展的。只不過在近現代以前世界各民族的交流因交通通訊技術的落后,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頻度和深度受到限制,各地方的文化差異才相對大一些。但文化還是在不斷融合發展著[4]。在過去的幾千年里,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鑒希臘,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藝復興的歐洲又仿效東羅馬帝國[5]146。在當今日趨全球化的現代社會,更難有某種文化是真正能夠與其他文化隔絕的。阿蘭·圖海納指出,現在來自各大洲各地區的人們,盡管他們生活的社會不同,所處的歷史發展背景和階段也有差異;但他們能在城市大街上相遇,在電視屏幕上互相看見彼此的形象,在音樂錄音帶上互相聽到彼此的歌聲。“在這樣一個世界上,還侈談什么保衛永恒的特性,那簡直是可笑的和危險的。……如果人們對文化的差異感到害怕和厭惡,因而想避免各種文化發生沖突,那就應當對各種文化的混合與會合給予一個積極的評價,因為這兩者幫助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擴大了自己的經驗,使我們自己的文化更富有創造性”[6]248。所以限制文化交流,就會對自身的文化發展有不利影響。比如內爾·比索達(Neil Bissoondath)在其《兜售幻覺:加拿大對多元主義的病態崇拜》一書中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實際上是對少數民族的一種禁閉,使他們封閉在狹小的文化空間而不能走出來”[7]。皮埃爾·埃利奧特·特魯多(Pierre Eliot Trudeau)更是呼吁法裔加拿大人必須拒絕被限制在魁北克,反對所謂的少數民族“特殊地位”的區別對待。他認為文化保護并不會讓少數族群有任何受益。從長遠來看,這樣的特殊地位只能強化法裔社群以這種方式受到保護、避免競爭的價值觀念。而文化必須保持思想交流,并通過接受挑戰才能不斷進步[8]196。
也許有觀點認為,民族主義多元文化論關于文化隔離保護政策的主張,或許可以適用于文化差異中最具封閉性的情況。然而“當前的文化交往已經導致了全球范圍內行為模式的大融合,要想再找到某種真正內生的、歷久不變的‘本土文化已經很困難了”[9]133。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我們關于沒有需要認可的天賦文化的判斷是正確的,那么,很多由官方認可的“族裔共同體”就意味著它只是一個法律的虛構而不是社會現實[10]89。在實踐效果上,可以預見的是,它對文化的制度化區隔,只會在政策、法律層面上對族群某一特定時間的特色文化風貌生成一個立即凍結和使之停滯的一種文化快照。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文化快照必然是逐漸失真和不可應用的。因為在政策和法律條文中凍結的關于多元文化格局的定義與實際社會文化變動進程之間的差異必然會不斷增長[10]89。同時,這種脫離了動態現實的多元文化政策還往往會因其封閉靜止的文化觀念,對文化的自然發展和更新造成干擾。因為它雖然可能導致對某些文化因素的保護,但這些因素也許是傾向于變化和轉型的[11]。
二、單一文化身份幻象與族群分離
文化認同處于流變之中,任何想以靜態的或行政劃分的方式呈現它的努力不僅是可疑的甚至是荒謬的[11],而且也是危險的。我們每個人出生時本沒有什么文化社群的身份意識、宗教意識或者內群排外思想。在互聯網全面飛速深入發展的現代社會,人們在心智成長的社會化過程中,落入的是一個相互連通的文化網絡,而不是被隔離在某個封閉的局域網中。在這個動態開放的文化網絡中,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文化節點,在法律容許的范圍內,任何人都可以在整個網絡中自由分享或廣播他所選擇或創造的文化信息、自由加入或退出由許多獨立文化節點組成的不同文化社群,并同時擁有多重文化社群身份。但在以固化單一民族文化身份差異為導向的民族主義多元文化政策的安排下,個人文化自由的空間受到了限制。每個人都首先被打上只屬于某一族文化成員的身份標簽。這種僵硬的文化區隔政策很容易將群體的刻板印象帶入個體的互動中,形成對個體的文化偏見。即使我們自己明了我們希望如何看待自己,我們也許仍然很難勸說他人也以同樣的方式看待我們。每個人無法堅持要求他人將其首先單純地視為一個人,而不管其民族成分如何。我們可能無法避免地被劃入國家和社會的統治者為我們準備好的某個人群類別中。不管我們如何看待自身,我們常常被貼著相同的標簽而籠統地按照群體文化形象給簡單地標簽化和符號化了。我們在維護個人文化身份方面的自由在制度化的單一文化身份歸類中是極有限的[9]5-6。
查爾斯·蒂利指出,“身份是一組有力的社會安排,在這種安排里,人們建構有關他們是誰、他們如何聯系和對他們發生了什么的共享故事。……不管這些故事根據歷史研究的標準是真是假,它們在達成協議與協同社會互動方面,發揮了不可缺少的作用”[12]221。民族主義政治大亨們之所以熱衷從歷史文化素材中萃取出可信的族性符號,就是要創造“我們”—“他們”的親疏意識,激活作為社會群體動員功能的故事與身份邊界,操縱壓制其他競爭的身份[12]223。那些以身份政治為業的民族主義者們總是不厭其煩地用各種文化符號切分人群,給人們貼上不同的民族標簽。如果用語言分不開一群人,他們就會用信仰、神話傳說、習俗,甚至飲食喜好或穿著方式的差異把人群分裂成多個小群體。同時,他們在切分出的各個小集團內始終努力培養成員內外親疏有別的族群意識。而當人們開始使用有關“我們是誰?”“你們是誰?”和“他們是誰?”這些問題的共享答案時,民族主義多元文化論者們就會很容易地把一種單一的文化身份歸類變成政治動員和排除異己的工具。同時,當其他被標簽化的人也開始用你身上的身份標簽先入為主地界定你是誰,以及你和他的關系的時候,你也很難從民族身份的小盒子中脫身。
蒂利認為,明顯的集體暴力依賴于群體身份邊界的激活和加強[13]4。民族主義多元文化論關于界別公民文化身份的政策主張,很容易使國家給每個人打上一個單一的民族文化身份,促使人們留居在本族的聚居區內。同時,原本可能被自然淡化、忘卻的文化“特性”,在區隔保護、施以恩惠的政策下又能得以重新突顯[2]。這又反過來加強了標示單一民族文化身份的原生質依據。在民族主義排外思想的滲透影響下,這種對人群的單一文化身份的制度分類,極易成為某些分離分子組織、動員和煽動群體對立的“合法”武器。有學者指出,盡管任何個人或群體都有多重身份,但對社會成員按照民族的單一文化身份的區隔安排很容易導致社會的日益“巴爾干化”,甚至引發鼓勵“種族分離”這樣的災難性后果[14]。比如在巴基斯坦,同樣一批人在不同的場合可能是作為工人、婦女、穆斯林、信德人的村民或某個行業的成員而行動。然而身份政治的邊界專家們卻總是在眾多的身份中專門挑選兩種相反的族群身份制造群體的對立和沖突[13]4。例如民族主義分子不僅在西巴基斯坦制造了內部旁遮普人、帕坦人、信德人以及其他族群之間的緊張與宿怨,又對東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大肆屠殺,結果以東巴基斯坦獨立為孟加拉國而收場。為了隔離穆斯林與印度教教徒,他們不惜血流成河與印度分治;為了割裂穆斯林兄弟,他們也照樣不惜血流成河[15]28。由于民族主義和多元單一文化主義在當代社會的泛濫,使得生活在多元化社會中的人們越來越容易被一些身份符號區隔為越來越多的族群。雖然整個世界的相互聯系正變得越來越頻繁緊密,但當今多元文化交匯的社會仍可能在民族主義多元文化論所制造的單一民族文化分類的幻想下,陷入到碎片化、部落化和永無止息的紛爭中去。
三、分族自治與虛假聯合
蓋爾納觀察到,在傳統環境里,追求單一的、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同一性的理想毫無意義。尼泊爾山區農民常常與多種多樣的宗教儀式發生關系,并根據情況從社會等級、宗族或者村落(但不從民族)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之所以說在傳統環境里鼓吹同一性并不重要,是因為那不會引起什么反響。然而在民族國家模式已然確立為國際主流的當代社會,明確刻畫自己的特征則是一個力圖對內保持同一性、對外實現自治的假定存在的民族的特點[16]18。安娜·特里安達菲利杜發現,那些善于經營族群邊界的現代民族主義者們,在文化領域建構各種民族性的工作中,利用某種語言、宗教、民俗或歷史傳說等具體的文化要素“不僅僅是在進一步確證民族身份的層面上才重要,因為正是它們將內部群體和外部群體區分開,才使對世界的這種區分性的觀點和政策主張得以合法化和真實化。文化特性、神話、傳統、歷史地域構成了‘我們和‘他們之間區別的內在組成部分。它們賦予民族和‘異己之間的對立以具體的形式,同時,它們又為這種對立所塑造,從而反過來進一步確證了它”[17]。對此,民族主義研究專家埃里·凱杜里認為,雖然民族主義“試圖通過求助歷史、人種學和語言學來證實民族是人類明顯的和自然的分支。但是這種企圖宣告失敗,因為無論何種人種學或語言學,均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來解釋,為什么如果存在操有相同語言或屬于相同種族的人們的事實的話,就應該單獨地賦予他們享有一個他們自己的排他性的政府的權利”[18]74。但令人遺憾的是,一些主張各群體文化友好相處的人們,卻每每陷入了多元單一文化主義的思維幻象,使得原本豐富的關于人類文化多元溝通與差異共存的探討和實踐,常常簡化成在數個排他性民族文化板塊所構成的“拼圖游戲”中某種“和稀泥”式的“求同存異”。在民族主義關于“劃族而治”的多元文化政策的宣傳中,“民族”變成了唯一的多元文化單位,差異只能是族際之間的文化差異,而不能是別的。同時,族內個體豐富多樣的文化個性往往被忽略、抹平,族際文化之間某些方面的少數“差異”常常被嚴重放大。多元文化的共存模式似乎只是數個不同顏色的玻璃片剛好被擺在一起,而一旦條件出現,它們可以隨時分開。因此,純粹以族群單位界分文化群體類型的民族主義多元文化論,既追求地方群體文化同質性,又欺世盜名地打著多元文化主義的幌子,很容易成為多族群國家內部一些民族分離主義者們追求高度自治甚至搞分裂的漸進手段:首先通過盜用多元文化主義影響國家群體文化政策的制定,形成一種國家內部各族文化相互區隔的馬賽克拼盤式的虛假聯合。其次等到國家一旦遭遇重大政治危機,一旦中央對邊疆的控制出現較大程度的松動時,某些平日里大談“政治一體、文化多元”,主張“差異共存”的民族主義多元文化論者們很可能搖身一變,成為激活族群文化認同邊界,鼓動民族政治自決的政治大亨,將早已切割開來的各個民族文化自治集團坐實為可分離的地方政治集團從而分裂國家。
邁克爾·赫克特指出,“民族主義運動常常以一種受到威脅的文化群體的保衛者身份來證明它們自己的合法性”[8]151。但實際上,族群領導人和精英們“是利用他們的文化群體作為動員群眾的場所,并且作為他們競爭權力和資源的贊助者,因為他們發現利用族群群體比利用社會階級更有效”[19]59。而且族群分隔的制度化建設越多,對于其工作和社會地位都要靠這一文化之維系的人們來說,主權的個人凈收益就越多[8]152。他觀察到,“文化上具有獨特性的領地在覺醒時常常會形成民族主義。由于處于間接統治體系的地方政權已經控制了領土內的行政管理機構,它們擁有可以動用的資源以及可動員的屬民。有時,它們會胸有成竹地宣布脫離中央統治者”[8]33。
一些陷入多元單一文化主義虛假聯合思維誤區的人們也許會簡單地認為,地方民族主義者們最多不過尋求保持一種獨特的民族語言和文化。因此,一個多族群國家的政府將文化事務方面的自治權力讓予其統治之下的不同族群,便可以滿足族群民族主義的要求并使他們放下武器[18]111。但這種想法未免太過天真。因為民族主義認為政治的和民族的單位應該是一致的[16]1。它的終極追求,就是要使文化和政體一致,努力讓文化擁有自己獨立的政治屋頂[16]57-58。安東尼·史密斯發現,在現代民族分離運動的實踐中,“民族主義的文化和政治形式常常相互繼承,并且民族主義者們可能會在兩者之間搖擺。當政治民族主義在其目標上躊躇時,文化民族主義就可能充當臨時代理人,發展共同體的集體文化資源;當文化的元氣消減時,新的民族主義政治運動又會顯現”[19]81-82。埃里·凱杜里認為,試圖用更大的文化自治來“阻止民族主義者不滿勢頭的企圖是很難成功的。因為民族主義者認為,政治和文化事務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不賦予其一個排他的主權的話,任何文化是沒有生命力的。這種企圖只能使藝術、文學和語言問題變成嚴重的政治對立問題,并被用來作為民族斗爭的武器”[18]111。他指出,“只有當一個多民族帝國的不同民族的文化、語言和宗教自治不取決于民族主義學說,或者被這種學說加以證實的時候,這種自治才是可行的;數世紀中,在奧斯曼帝國,這種自治使得以‘米萊特(millet)制度著稱的安排有可能維持下來,恰恰因為民族主義不被人們所知,而它的崩潰則是當民族主義在該帝國不同民族中間得到傳播的時候。這種‘米萊特制度的瓦解是因為這種有限的自治不能滿足民族主義者的野心”[18]111。因此,盡管一些民族主義多元文化論者常常搬出許多古代多族群帝國“因俗而治”的古老案例來為當下的自治主張作注腳,但在民族主義思潮泛起的今天,狹隘封閉的自治實際上已成為多族群國家解決地方民族主義者要求的不確定和不可靠的方式[1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