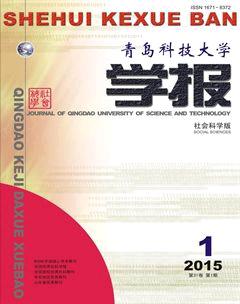席勒的崇高論
張玉能
[摘 要]席勒把崇高與藝術聯系起來,認為激情的諷刺詩是崇高性格的表現,嬉戲的諷刺詩是優美性格的表現。席勒把崇高與悲劇藝術聯系起來,指明了悲劇是崇高的集中表現。這是席勒在藝術史上最大的歷史貢獻,不僅指明了悲劇藝術的崇高本質,而且突破了西方古典形態的悲劇觀,啟發了黑格爾等的悲劇矛盾沖突論。
[關鍵詞]崇高;藝術;悲劇藝術
[中圖分類號]I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372(2015)01-0061-08
Abstract:Schiller linked the sublime with the art and believed that the passionate satire was the performance of noble temperament and the playful satire was the performance of beautiful temperament. Schiller put the sublimity and the tragedy art together to specify the tragedy was the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noble, of which is Schillers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the art history. In this way, he not only pointed out the sublime nature of the tragedy art, but also broke through the tragic theory of Western classical form and inspired the tragic conflicts theory of Hagel and other people.
Key words:sublime;art;tragic art
席勒不僅關注到自然界中的各種崇高現象和崇高對象,而且把人類的文學藝術與崇高聯系起來。一方面,他把詩(文學作品)視為人性的具體表現,而激情的諷刺詩是崇高性格的表現,戲謔的諷刺詩則是優美性格的表現;另一方面,他把悲劇與崇高緊密聯系起來,把悲劇看做是崇高的集中表現。
一、崇高與藝術、諷刺詩
在《關于各種審美對象的斷想》中,席勒不僅列舉了許許多多自然界的崇高對象,也列舉了許多藝術中的崇高對象。他說:“在希臘羅馬神話中沒有比從地獄里出來追捕罪犯時的復仇女神福利亞或愛倫尼更可怕和更丑的形象了。令人厭惡地扭歪的臉,瘦骨嶙峋的軀體,一群蛇代替頭發披在頭上,既激怒我們的感覺,又傷害我們的審美趣味。但是當我們在舞臺上看到這些怪物如何追捕弒母者俄瑞斯特,怎樣揮動著火炬不知疲倦地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追趕他的時候,看到她們最后使滿腔義憤平靜下來,消逝在地獄的深淵的時候,我們就會以一種愉快的恐怖注視著這個表象。除了由福利亞體現出來的罪人良心的苦惱,甚至違反義務的行為,他真正的犯罪行為也能在表現中使我們歡喜。古希臘悲劇的美狄亞,殺死丈夫的克麗特姆涅斯特娜,殺死母親的俄瑞斯特,使我們體驗到一種令人戰栗的快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會發現,對我們冷漠無情的,甚至使我們苦惱和可怕的事物,只要它一接近成為某種龐然大物或令人恐怖的東西,就開始使我們感興趣。一個極其普通的小人物,只要強烈的激情在最微小的程度上也不提高他的價值,就會使他成為可怕和恐怖的對象;那么,一個平庸的無足輕重的對象,只要我們使它增大到接近超越我們的把握能力,它就成為快感的源泉。一個丑人由于憤怒會變得更丑,但是就在這種激情的爆發中,只要這種激情不是可笑的,而是可怕的,他就可能對我們具有最強烈的吸引力。這種觀點甚至也適用于動物。拉犁的牛,套車的馬、狗,都是常見的對象;如果我們激起公牛參加戰斗,使一匹安靜的馬激怒,或者我們看見一條瘋狗—所有這些動物就會成為審美的對象,我們也開始帶著愉快和尊敬的感情觀看它們。一切人所共有的對充滿激情的事物的愛好,在自然中迫使我們觀照痛苦,可怕和恐怖的同情感,在藝術中對我們有那么大的魅力,在劇院中那么吸引我們,使我們那么喜愛對巨大不幸的描寫,這一些都證明,除開愉快、善和美之外還存在著快感的第四個源泉。”[1]98-99席勒尤其強調了藝術可以把世界上一切充滿激情的事物都轉化為崇高的審美對象,特別是悲劇藝術能夠把人世間的一切不幸的事件都在劇院里轉變為崇高的審美對象,而且,從古希臘神話傳說和悲劇藝術開始都那么充滿吸引人的永恒魅力。
在《論激情》中,席勒在分析崇高的類型時論述了不同的藝術家所適宜表現的崇高對象。他說:“靜穆的崇高可以直觀,因為它以共存性為基礎;相反,行動的崇高只可以沉思,因為它以連續性為基礎,而且為了從自由的決定中推導出痛苦,理智是必需的。因此,只有第一種崇高才適用于造型藝術家,因為這種藝術家只能成功地表現同時存在的東西,而詩人能夠詳述兩者。甚至當造型藝術家表現行動的崇高時,他也必須把它化為靜穆的崇高。”[1]160席勒認為,靜穆的崇高,由于是在空間中展現出來的,主要是一種直觀的對象,所以適合于繪畫和雕塑等造型藝術表現,而行動的崇高,由于是既在空間中展現出來,又在時間中持續出現的,主要是一種激情的對象,所以詩人既可以詳盡地表現行動的崇高,也可以細致地描述直觀的崇高。同時,造型藝術家比起詩人,好像更加受制于自己的空間展現局限,無法描繪時間中持續出現的行動的崇高,所以不得不先把行動的崇高轉化為直觀的崇高,才能夠比較合適地描繪出行動的崇高。這里的論述,似乎是對萊辛的《拉奧孔—論詩與畫的界限》的一種發揮和補充。在《拉奧孔》中,萊辛曾經分析了詩人與造型藝術家的優勢和不足,認為詩人擅長于表現時間中持續出現的對象,而造型藝術家則更適合于描繪在空間中展現出來的對象,并且指出,詩人要描繪在空間中展現出來的對象可以“化美為媚”或者“化靜為動”[2]93。不過,萊辛似乎把詩人與畫家的限制有點絕對化了,而且并沒有說到詩人可以比畫家具有更多的優越性,可以“詳述二者”,也沒有說到畫家等造型藝術家如何揚長避短,描繪在時間中持續出現的行動的崇高,而這些在席勒的《論激情》中都說到了。這大概不能說是席勒的無意所為吧,因為萊辛的《拉奧孔—論詩與畫的界限》于1765年寫出來以后,隨著“狂飆突進”文學運動的發展已經廣為流傳,所以席勒在論述到相關問題時就必然會發揮和補充萊辛的某些看法,以更加完善德國啟蒙主義的美學理論。
此外,在《論激情》中,席勒分析了道德判斷與審美判斷的相對立和相阻礙,希望詩人能夠從審美判斷的態度上來表現崇高的對象。他說:“一個對象恰好比起它適合于道德的使用更少適合于審美的使用;如果詩人仍然必須選中它,那么他應該那樣著手處理它,以致不是我們的理性指出意志的法則,而是我們的想象力指出意志的能力。為了他的自我,詩人必須選擇這條道路,因為同我們的自由一起,他的王國也完結了。只有當我們在我們之外直觀時,我們才是他的,一旦我們轉向我們自身的內心,他對我們就失去了;只要一個對象不再作為我們觀照的現象,而作為評判我們的法則,這種情況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也就是說,詩人必須以同情的態度,想象地采用崇高對象,并且想象地表現出克服感性痛苦激情的人性意志能力和意志自由。與此同時,詩人還必須從崇高對象在主人公身上所引起的感性本性與理性本性的矛盾沖突中顯現出人的精神能力的提高和未來必達的精神自由。他說:“甚至從最崇高的道德表現中,詩人為了他的目的,除了屬于力量的表現的東西以外,無論什么也不能采用。而且他一點也不關心力量的方向。詩人,在他把最完善的道德典范提供在我們眼前時,除了使我們通過直觀它們而愉悅以外,沒有其他目的,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目的。然而這時除了使我們的主體改善的東西以外,沒有什么能夠使我們愉悅;除了提高我們精神能力的東西以外,也沒有什么能夠使我們在精神上愉悅。但是,別人的義務節制怎樣改善我們主體和提高我們的精神力量呢?他實際上履行他的義務,是以他對他的自由的偶然運用為基礎的,而這種運用恰恰對此一點也不能向我們證明什么。我們與他共有的僅僅是達到類似義務節制的能力,而且當我們在他的能力中也感覺到我們的能力時,我們就感到我們的精神力量提高了。因此,只有絕對自由的意愿的表現的可能性及其真正的實現才使我們的美感愉快。”[1]163-164因此,在詩和藝術中表現崇高對象必須顯現出人性意志自由的未來必達性,即人類精神自由的可能性,而不是意志自由和精神自由的現實性,一旦這種意志自由或者精神自由在現實中實現了,它的審美價值也就消失了。所以,崇高對象一般說來就更加適宜于感傷詩人和感傷的詩。正因為如此,席勒后來在《論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中把感傷的詩歸結為崇高心靈或者崇高性格的表現。
在《論崇高(II)》中席勒明確地把崇高與藝術聯系起來,論述了藝術表現崇高對象具有自然界不可比擬的優勢。他說:“像美一樣,崇高也源源不斷地泛溢于整個自然,一切人都有感受兩者的能力。但是這種感受能力的胚芽生長發育并不平衡,而藝術應該促進它的發育生長。自然的意義本來就導致我們首先趨向于美,同時我們就躲避開崇高。因為美是我們童年時代的保護者,必定引導我們從粗野的自然狀態達到良好的教養。但是,盡管美是我們初戀的情人,我們對美的感受能力也是首先發展起來的,然而,自然仍然關注這種感受能力的逐漸成熟,而且在這種感受能力完全發育成熟之前先培養理智和心靈。假如審美趣味達到完全成熟,比真理和道德更早培植在我們心田中,而且是通過比審美趣味可能實現的更好的方法培植的,那么感性世界就永遠始終是我們意向的界限。我們無論在我們的概念中,還是在我們的信念中,都會超越不了感性世界的界限,而且想象力不能表現的東西,就會對于我們沒有任何現實性。不過,非常幸運,自然早就安排好了,審美趣味雖然最先興盛起來,但是它畢竟產生于所有精神能力之中。同時在這期間贏得足夠的時間,把豐富的概念培植于頭腦中并把珍貴的原則培植于胸懷中,然后就從理性中單獨發展起對偉大和崇高的感受能力。”[1]189也就是說,藝術應該而且可以把大自然賦予人類的崇高和崇高感培育壯大,成為人類保持人性自由本質的重要方面或者更有效的手段。席勒說:“現在自然本身雖然本來就提供了大量獨一無二的客體,在這些客體上我們對美和崇高的感受能力可以得到訓練;但是,人,像在其他情況下一樣,比起運用第一手材料更善于運用第二手材料,而且比起從自然的不純潔源泉中艱難而可憐地汲取材料,他更樂意接受藝術精選和調配的材料。模仿的造型沖動不能忍受不立即使印象栩栩如生地表現出來,而且在自然每個美的形式或偉大的形式中都發現與自然爭高低的號召,在自然面前就具有巨大的優越性,能夠把自然在追求一種比較切近它的目的時順便帶來的東西—只要自然不把它完全無意地扔掉—作為主要目的和一個獨特的整體來對待。如果自然在它美的有機構成物之中,不是由于質料的個性不足,就是由于異類力量的影響而忍受暴力,或者如果它在自己偉大和激情的場景中施行暴力并作為一種威力對人發生作用,這時它又仍然可以僅僅作為自由觀照的客體而成為審美客體,那么,它的模仿者,造型藝術就完全是自由的,因為這種藝術使偶然性的限制與它的對象隔絕開來。而且這種藝術也允許觀照者的精神是自由的,因為藝術只模仿外觀而不模仿實在(die Wirklichkeit)。再者,因為崇高和美的全部魅力僅僅在于外觀,而不在于內容,所以藝術共享自然的一切優點,卻不分擔自然的束縛。”[1]193-194這就是說,藝術不僅可以像大自然一樣培育起人類的崇高和崇高感的幼苗,而且可以更好地發揮作用。藝術是人類想象力的創造,所以它能夠充分利用審美對象的外觀形象性、情感感染性、超越功利性的優勢,讓人更加有利地對崇高對象采取“同情”的態度,從而比起大自然的崇高對象會更加有效地成為審美教育和藝術教育的手段和途徑。
恰恰是注意到崇高的藝術表現必須是在人類的感性本性與理性本性的矛盾沖突中充分顯現出來,而且必須是以想象性、可能性的形象表現出來,所以,席勒在《論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中把崇高與詩的藝術聯系起來,認為激情的諷刺詩是崇高性格的表現,嬉戲的諷刺詩是優美性格的表現。他說:“如果激情的諷刺只是適合于崇高的心靈,那么嬉戲的諷刺只能由一顆優美的心來完成。因為前者早已借助他的嚴肅的題材而避免了輕浮;但是后者只能處理道德上無關緊要的題材,如果在這里不使內容的處理高尚化,如果詩人的主體不能代替他的客體,那就必然會陷入輕浮,就會喪失任何詩的尊嚴。然而只有優美的心才能不依賴于它的活動的對象,在它的任何表現中顯示出它自己的完美形象。崇高的性格只有在對感官抵抗的個別勝利中,只有在情感激昂的片刻和瞬間的緊張之中,才能表現出自己。相反,在優美的心靈中,理想作為天性發生作用,即始終如一地發生作用,因而可以在一種寧靜的狀態中把自己表現出來。深深的海洋在波濤洶涌的時候顯得是最崇高的,清澈的小溪在平靜流淌的時候顯得是最優美的。”[1]318在這里,席勒不僅把崇高與詩的藝術緊密聯系在一起了,而且把詩的藝術與人類的人性特征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形成了崇高、藝術、人性三位一體的統一,充分地顯示出席勒人性美學思想體系的獨特特征。這種崇高、藝術、人性“三位一體”最為集中地表現在席勒把悲劇與崇高聯系起來進行探討的深入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