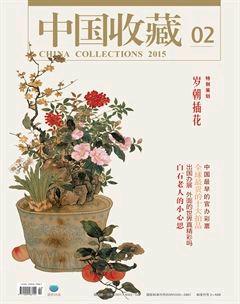誰言一點紅 解寄無邊春
王菁菁
在中國傳統習俗“歲朝清供”中,花是必不可少的元素。因為新春伊始,需要有一點兒色彩來作為襯托,而且花有芬芳,有不懈的生命力,加之國人尊崇“生之喜悅”,借助這些美好也能表達出人們對未來一年的憧憬與期盼。
抱著想要對“歲朝清供”以及中國傳統插花藝術進行更多了解的心態,2014年12月末的一個午后,我們走進了位于北京市西城區的一家藝術工作室。素懷清韻軒主人吳永剛雖然年輕,卻對中國傳統插花藝術非常摯愛與癡迷。茶香氤氳中,作為同齡人,大家隨意地聊著這般閑情逸致的話題,一時間竟也忘卻了室外的車水馬龍與世俗繁華。
緣起
提到插花,國人對此稍顯陌生,給人第一反應或許是日本花道,那身著和服的女人畢恭畢敬跪坐于榻榻米上的畫面。然而在歷史長河中,插花藝術并非源于日本,也不是女性的“專利”。
“大體上說,插花分為西方插花與東方插花兩大類,前者起源于古埃及,后者則起源于中國。”吳永剛說。每周四的晚上,吳永剛都會去北京五道營胡同的惠量小院為志同道合的花友們講授交流,共同研習中國傳統插花藝術。面對新入門的花友,回顧歷史是他一貫的“開場白”。

早在先秦時期人們就已有賞花品卉的風俗,而關于插花在中國最早出現的時期,現在業內通常有兩種說法:一說是可以推至西周或者春秋,早在3000多年前,中國就對花卉應用有了初始形態,其中《詩經》、《楚辭》中多有記載;而另一種認同性更廣的說法,則是最初出現在漢魏南北朝,隋唐五代國力比較昌盛,插花成為了一種藝術門類,屬于古典藝術之一。宋元是插花的興盛時期,特別是宋朝,這個將傳統之美發揮到極致的年代。這一時期除了“文人四藝”外,又有插花、掛畫、烹茶、焚香,演變為當時流行于文人士大夫間的四大閑事。行至明清,傳統插花達到了鼎盛時期,此時已經出現了幾部與此相關的著作,比如張謙德的《瓶花譜》和袁宏道的《瓶史》,堪稱中國古典插花藝術典籍的雙璧。只不過清代中葉后,國力衰退,戰亂頻繁,由此,中國插花出現了將近200年的斷代。
值得一提的是,在1000多年前的隋唐時期,佛教由印度傳到中國。當時日本有一位名叫小野妹子的遣唐使,本身非常熱愛文化,到了中國后特別喜歡佛教及中國的古典藝術,又在皇宮里看到了插花的形式,更是欣喜不已,待完成使命回到日本國內以后,此君的第一件事便是辭了工作,剃度出家,日夜以花供佛,由此在日本東京池坊產生了日式插花鼻祖第一大門派—池坊花道。
不難看出,日本的花道實際上是從中國傳入的。只不過因為民族習慣、性格、審美認知的不同,插花藝術的講究和側重點也有所區別。另一方面,受歷史原因、推廣力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以致當今的國人會對插花文化產生這樣或那樣的認識誤區。
辭舊
由于采訪當日正值年末,沒多久,我們的話題很自然便落到了“歲朝插花”上。正巧,工作室里有一件吳永剛完成不久的插花作品,用撿來的龍爪樹枝條,搭配黃芯小菊、玫瑰等,高低錯落,疏密有致,既雅致又不乏嬌媚。“所有的花材分為線狀、塊狀、點狀、面狀,空間構圖分為直立、傾斜、平展、下垂。選擇好花器后,我們先定一個主枝,再看整個作品是直立、傾斜、平展還是下垂,通過這樣的變化,其他的花材圍繞主枝來進行空間構圖,像龍爪樹,盡量不去破壞它的空間,而玫瑰的桿是比較直的,可選擇曲線稍曲折一點,形成一個不等式的三角形構圖,先插焦點花材,再插點狀花材,接著是面狀花材,其中的變化在于插花者內心的認知,花個20多分鐘插完后,最后給它命個名,就只待欣賞了。”他介紹道。
由此可見,中國插花藝術的特點,意趣(內容美)總是置之首位的,其次才是形式(構圖美),最后是色彩(質材)。在掌握基本構圖、布局手法要求的基礎上,選擇什么樣的花材,以何種方式呈現似乎更多的是一件至情至性之事。當然,植物有自己的生長期,況且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之一,不似我們今天能有大棚培植的便利,古代傳統插花對于花材的選擇基本按照季節變化來分。自明代開始,傳統插花中就有了花盟主、花卿客、花使命之稱謂。古代文人用花來比德,例如明人張謙德就仿蜀漢張翊《九品九命》的方法,將花卉從一品九命到九品一命分為九等,評定標準除傳統的花德外,還加之以對花卉在插花中的實用性的考量,古人以花言志的情懷可見一斑。于是,一些寓意比較好的花被推選為當月的“盟主”,譬如一月梅花、二月杏花、三月桃花、四月牡丹、五月石榴、六月荷花、七月蘭花、八月桂花、九月菊花、十月月季、十一月臘梅、十二月水仙(關于每月的花盟主說法比較多,此為其中一種)。選定盟主后,其余的花材可以作為襯花按時令季節及花品心性搭配。
而在歲朝插花的傳統習俗里,京津兩地偏愛水仙,南方好梅。以水仙為例,有單瓣和復瓣之分,單瓣中間有小圈的水仙叫“金盞銀臺”,重瓣的叫“玉玲瓏”,水仙還有個別稱叫“凌波仙子”,這樣的意境聽起來就足夠令人心馳神往。此外,其他一些木本花卉,像常見的山茶、迎春、瑞香等,都可以作為歲朝插花的花材。
“插花最難之處在于對植物屬性的了解。要把不同的花卉搭配起來去表現內心的情感,除了要熟悉植物屬性外,更重要的是人跟植物之間要有情感的交流。”令吳永剛感觸最深的是,每次插好花后,與這些花卉朝夕相處一二十天,每天都能看到它們細微的變化,這是一種難得的緣分。在他看來,插花的本質不僅僅是掌握某種技巧,而是能觸發人對美、對生活的思考,所謂“花開不忘其美,花落不忘其心”。正因如此,插花被視為最能融入生活的一種藝術。


花悟
事實上,無論是插花也好,點茶、焚香也罷,當我們通過某一個藝術門類試圖想走進中國傳統文化的大門時,會看到其中的很多東西實則都是來源于生活、服務于生活的。當一種習慣漸漸成為風俗,從中延伸出諸多講究,并且慢慢累積為一門學問時,這或許就是人們常說的“閑玩出藝術”。更加不容回避的是,因為有了中國傳統文人士大夫這一群體的推動,讓原本的民風民俗變成了雅趣,讓美來源于生活,卻又更高于生活,回味無窮。
正如吳永剛告訴我們,整個中國傳統插花有四大種類形式,即文人插花、佛前供花、民間插花、宮廷插花,其中佳作都是以文人為主,當中能夠有建樹、著書立說的都是文人。
據說,古代插花需要“三境”:心境、情境和物境,也就是說,你除了要能靜下心來做以外,還得有一個合適的環境與一定財力(或者能力)。早有唐代羅虬在《花九錫》中就提道,插花“一、重頂帷(障風);二、金剪刀(剪折);三、甘泉(浸);四、玉缸(貯);五、雕文臺座(安置);六、畫圖;七、翻曲;八、美醑(賞);九、新詩(詠)”。用今天的話解釋就是,插花時要搭一個類似于帳子的環境,而且要看天氣,當月朗星稀,微風徐徐,風吹到幕布上撩起投影的時候,感覺就到位了。這時要用金剪刀當工具,而且由于花本身需要一定的礦物質培養,須將銅器土埋帶銹后再拿出來用以盛放,或者是用玉器來作為花器。另外,養花須是泉水,如果怕水質變化,還可以放一塊燒紅的炭在里面;花器的底座一定是黃花梨、沉香木之類,而且還要有雕文……
是不是非常講究?其實上述這些只是眾多講究中的“一斑”。比如采集花卉,必須要清晨帶露的,才能保持它的花香和色;而不同的花,有不同的滋養方式,梅花需要把根莖稍微搗碎一點兒,抹點兒鹽;最難養的是荷花,采擇后從頸部注水,以發纏絲系住;還有芍藥、牡丹等,直接插在蜂蜜里……
文人插花必定追求雅致,因此一般不會超過4種顏色。不同的節氣也有不同的插花方式,端午、清明、月夕……如八月十五插花,花器往往會選擇圓形的,水要清澈見底,在南方,人們還在水中放一點浮萍,當月光投下來,花影綽約,引人遐思翩翩。
花美需人賞,自然也有講究。隋唐時期的插花,講究欣賞時邊飲美酒,邊聽音樂,還不時即興詠詩,融插花、生活與娛樂于一體,這種鑒賞方式稱為“酒賞”。到五代時期,則由“酒賞”發展成“香賞”。南唐進士韓熙載在《五宜說》中寫道:“對花焚香,有風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樨宜龍腦,酴醾宜沉水,蘭宜四絕,含笑宜麝,檐葡宜檀。”要求插作不同花材時選用不同香料焚燃,形成花香相和的“香賞”風格,注重追求嗅覺之美。到明朝時,袁宏道對插花的審美要求更高一層,將插花與品茗相結合,謂之“茗賞”,這與前代大異其趣。其注重品位,即賞花花品兼得時清香幽美之情趣和韻味,并認為“酒賞”、“香賞”均不如“茗賞”高雅。
說到此,古人的敬畏之心不得不提。在他們看來,插花需要用多少就采多少,花材用不完丟棄都是對花神的褻瀆。插花、賞花既是悅己,也是悅知己,這種花與人的和靜之美,即便放到今天來看,也是現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吳永剛說,在古代中國,插花被視為“醒者”的藝術,它需要仔細品味,用心體悟,用崇敬之情來創作。相比日本花道的“道”更講究規矩,中國插花的“道”則是順其自然。與其他藝術門類一樣,中國插花深究起來最終都歸于易經與五行,比如稱花器為“大地”,比如古代對于花器中“劍山”(即中心點)位置擺放的講究(遵循洛書比)等等。就如同《心經》短短286個字,有人讀了一輩子也不明其所以然一般,中國插花藝術的博大精深不在于技法有多難,而是在于對花的理解和頓悟。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們中國的愛情之花是芍藥,‘兩情相悅,贈之以芍藥’,芍藥還有個別名叫 將離;母親之花是忘憂草,種在家門口,希望游子能忘記憂傷,還有牽牛花,別名朝顏……你看我們的祖先把花卉取名得多么美!插花與繪畫、詩歌、文學等古典藝術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通過這樣的方式能讓我們涉獵很多東西,向外可以看到一個廣闊無垠的世界,向內可以看到深邃無比的內心世界。”這是吳永剛愛上插花以來最為受益的“花之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