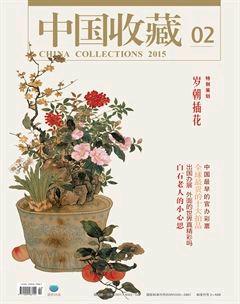隨器裁花 境時相宜
劉禮福
2014年年底,“瓶盆風華—明清故宮花器特展”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拉開帷幕,105件明清御用瓷花器讓人大開眼界。“臺北故宮博物院經常與我們合作舉辦插花展,一件器物一旦與插花藝術相結合就好像被賦予了生命,更加鮮活。”在臺灣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北京代表林愛卿女士看來,自古插花,雖花為主,器為賓,不能喧賓奪主,但也要相得益彰。而欲行插花,必先度其是供是賞,次擇花器,再選花材,方能各得其所。然器韻有高下之分、質有優劣之別,非隨心所用,必因時而異、因地有別、與花相宜,并表現中國傳統插花的意境與內涵,才算盡善盡美,這正是中國插花的精妙所在。
以器為地
說起對中國傳統插花藝術的研習,臺灣顯然比大陸先行了一步。1984年,臺灣中華婦女蘭藝社結合黃永川教授及一群同好潛心研究,在臺灣歷史博物館舉辦了第一屆“中國古典插花藝術展”,這是唐宋以來首次舉辦有系統的純中國古典插花藝術展。1987年,臺灣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正式成立,黃永川教授擔任董事長。黃永川教授曾任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其所著《中國插花史研究》一書考證詳實,史料豐富,是目前中國插花研究領域最權威的書籍。
“臺灣曾被日本殖民統治了50年,這期間日本花道在臺灣十分盛行,黃永川教授及一群同好因有感于我國古典插花的光榮歷史有發揚光大的必要,便立足傳統,潛心研究,積極復興中國傳統插花藝術。”林愛卿告訴記者,在臺灣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的努力下,中國傳統插花藝術在臺灣已形成一套完善的傳授、研習體系,并已超越日本花道成為主流。
當記者帶著歲朝插花這一主題拜訪林愛卿時,她強調,對于歲朝插花來講,除了花材需結合時節外,對花器也有特別的講究。“在臺灣的插花藝術中,因循傳統非常重要,每一次插花,從主題的構思、到花材,再到花器都有講究、有說法。”林愛卿拿出由黃永川先生注釋的《瓶花譜》和《瓶史》,“這兩本中國古代插花藝術的專著是研習中國傳統插花藝術的根基。”
我國傳統花器材質眾多,銅、瓷、玉、石、玻璃、水晶、漆、木竹等不一而足;形制多樣,壺、尊、甕、瓶、盆、盤、缸、碗、筒、籃等不甚枚舉,因為花器不僅是盛放花材與水的工具,更是欣賞插花必不可少的藝術元素和體悟天地造化奧秘的載體。據唐代《春盤賦》所述:“多事佳人,假盤盂而做地,疏綺繡以為珍。叢林俱秀,百卉爭新。一本一枝,協陶甄之妙致,片花片蕊,得造化之窮神。”此段文字充分說明,早在唐代盤、瓶的之類花器就已非簡單的花材之精舍,而是大地之縮影;插花一藝除了力求花材與花器的造型、質地相協調之外,更欲與造化爭勝。
既然外師造化、集天地之靈,花器的選擇自然要因時而異、因地有別。正如明代張謙德在《瓶花譜》中所言:“凡插貯花,先須擇瓶,春冬用銅,秋夏用瓷,因乎時也。堂廈宜大,書室宜小,因乎地也。貴瓷銅,賤金銀,尚清雅也。忌有環,忌成對,像神祠也。口欲小而足欲厚,取其安穩而不泄氣也。”


新歲始,奉神敬祖以祈吉福的歲朝插花,不僅是中國插花之供花一系的經典,更能體現花器也須因時而異的獨特理念。歲朝供花之器往往以瓶為主,又以銅器為宗、瓷器為輔,崇尚典麗、高貴、莊重、雅潔之風。然近觀現代歲朝插花,有用編織精美的籃器以及新穎奇特的現代陶藝者,實為犯忌,皆因此類花器難有典雅之感,有失敬意。
若論花器因地有別的精論,當推高濂成書于明代萬歷年間的《瓶花之宜》,書言:“堂中插花,乃以漢之銅壺,大古尊罍,或官哥大瓶,如弓耳壺、直口敞瓶;或龍泉蓍草大方瓶,高架兩旁,或置幾上……若書齋插花,瓶宜短小,以官哥膽瓶、紙槌瓶、鵝頸瓶、青東磁、古龍泉,俱可插花。”(見高濂的《遵生八箋》中《燕閑清賞箋》之《瓶花三說》)如此細膩深邃的擇器理論,在中國插花藝術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臺灣,不少制瓷名家都對花器的制作頗為重視,像曉芳窯的花器在滿含古韻的同時也不乏現代氣息,”林愛卿說,相比而言,在大陸當代瓷中,花器還未得到重視。雖然當代花器材質種類較傳統更加豐富、形制更為五花八門,但有些器物太過隨意、極盡新奇,更因不識先賢對常見插花擇器陋習及易犯之忌所作的審理,時有“瓶忌有環,忌放成對,忌用小口、甕肚、瘦足、藥壇,忌用葫蘆瓶。凡瓶忌吊花、妝彩。”(高濂《瓶花之忌》)等亂象叢生,致使最終呈現的插花雖時尚奇特,卻多紛亂繁雜、無章無序,更失掉了中國插花應有的意境幽遠、耐人尋味的品位與情趣。
因時而異
細審中國插花千百年之芳容,各朝各代對花器之所衷不僅極富情趣且各有千秋。花器又在不斷變化、完善中日積月累,終成洋洋大觀。
魏晉南北朝時,中國插花已形成盤花和瓶花兩大形式。雖然此時的插花僅是放花或養花于器,尚乏藝術地“插立”、“安排”的境界,但多用精美的盤、鼎、瓶等器皿與花材相配,并崇尚金銅器,已現藝術之端倪。
隨后,中國插花經歷“隋唐盛世”。愛花者不僅精研花木的自然習性,而且普遍賦以花木個性與格調、意義與象征。由《花九錫》可遙知,唐代花器追捧銅器、白瓷之類質料高潔上好者,而從薛能《牡丹詩》之“異色稟陶甄,常疑主者偏”一句借牡丹插于陶器而發心中不平之鳴,推知陶器則多被唐人插花所貶棄。為配合牡丹等大型花卉,唐代花器除用瓶盤之類外,還流行用缸、甕之類,是為“缸花”。此類插花之花器往往襯以擁有精雕華美紋飾的嵌螺鈿或錯金漆幾座、或青玉案底座、墊板、花臺,極盡雍容豪華之能事。
五代除了繼承唐代正統插花的絢麗隆盛遺風外,新生之自由花更受推崇。正因如此,五代花器突破盤瓶之限,而喜用銅制瓶壺乃至竹筒、吊盤之類的質樸花器,以期能更加充分地表現花材的天然情趣,這是對中國插花藝術的一次解放。而這種解放又為花器的改良留有用武之地,對中國插花貢獻至深至遠的占景盤、隔筒與掛花、吊花便誕生于五代,諸多新鮮元素讓五代插花藝術呈現出自由奔放的成熟境界。
愛花之深、插花之興到趙宋一代,別朝無出其右。除眷賞名花珍卉外,宋人時興鑒玩花器之風。如碾玉瓶、水晶瓶、銅壺、大食玻璃瓶等珍玩,以及精貴的汝、官、哥、定等名窯瓷器,一般在宮廷只作觀賞,一到花朝,則全數拿出,貯插名貴花材,安排在各殿堂,以壯勝觀。又因宋代鑒古好藏之風極盛,本就喜對每類花器嚴加考究的文人插花便也提倡以古董器物為上,如銅器自以先秦三代遺物為極品。正如南宋皇族宗室趙希鵠在《洞天清祿集》所解釋的:“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瓶結實……若水銹傳世古則否,陶器入土千年亦然。”至于瓷器,宋代花器則推崇名窯所產,又以青瓷為宗,講求雅潔含蓄、質地晶瑩。
為避免高大的瓶花顛覆,宋人則在瓶底備開小孔,以皮帶穿孔將瓶綁于花架或花桌之上;若是瓶底細長者則行用護瓶架。有些花器為了固定花枝,而于瓶口留有曲凹。為防花枝根部易腐,還借五代占景盤之巧思而多置插花孔于各類花器中,如三孔瓶、十九孔花插、三十一孔花碗、五岳朝天瓶等不僅美觀別致,更富有科學精神。另對珍貴花器,宋代插花還講求配帶附座或承盤,其設計之精巧,如花囊之屬至今令人欽佩,其他如花幾及襯景更力求精美。
可惜元代插花并未承接宋時興旺,其所用花器遠不及宋代講究,除盤、鑑、彝器之外,裝飾華美的隆重瓶器最受青睞。如元人《豐登報喜圖》中以精美的轉心瓶為花器,表現花葉扶疏、形色招展的隆盛花之特色。

幸及明代,中國插花得以復興。但明代宮廷插花只于喜慶節日如元旦、端午偶爾行之,且所做也僅限瓶花類,盤、籃、缸、碗之類幾不采用,民間插花亦受其影響,所以明代瓶花一枝獨秀,而對花器的講究也愈發細致入微、有理有序,這在諸家花書中隨處可見。如張謙德的《瓶花譜》曰:“大都瓶寧瘦,毋過壯,寧小,毋過大。極高者,不可過二尺,得六七寸、四五寸瓶插貯佳。若太小,則養花又不能久……尚古莫如銅器,窯則柴汝最貴,而世絕無之。官、哥、宣、定,為當今第一珍品,而龍泉、均州、章生、烏泥、成化等瓶,亦以次見重矣……余如暗花、茄袋、葫蘆樣、細口、匾肚、瘦足、藥壇等瓶,俱不入清供。”
然自清以降至今,中國插花日漸衰微,故無多情趣。如清代插花雖在民間最盛,但就花器講求而言,舉國謹守“春冬用銅、秋夏用瓷”的原則,色喜花俏、紋飾繁縟,極具華麗,喜用花籃,不免流于艷俗。
花器兩相宜
“臺灣不少藏家都很愿意把自己收藏的花器拿出來,請造詣高深的插花師插上合適的花卉。因為在他們看來,插花藝術賦予了花器靈魂,為花器增光添色。”林愛卿告訴記者,不管是因時而異、因地有別,還是歷朝各有所好,插花最終還是要落在如何神奇巧妙地處理花與器的關系上。故此,“花器兩相宜”就成為指導插花藝術的一大宗旨和不懈追求的境界。
唐代將牡丹用玉缸貯、雕文臺座安置,視為對國花最合其品格的禮遇。而以銅插梅、以瓷插牡丹,則是宋代插花崇尚的特殊品位。到了明代,因瓶花獨大而不斷豐富的“花與瓶稱”的審美追求則更加謹慎、細膩和完善,冬時插梅花必須龍泉大瓶、象窯敞瓶、厚銅漢壺,若瓶高三四尺以上,斫大枝插供,是文人最為快意之事;鳳尾水竹可插瓶取其枝葉如筆法者,折入小口瓶內,更別有意趣;屠隆更在《考槃馀事》中說:“若養蘭、蕙須用觚,牡丹則用蒲槌瓶方稱。”
同在明代萬歷年間成就中國插花圣典的高濂、張謙德對瓶花更有妙論。高濂認為:“大率插花須要花與瓶稱,花高于瓶四五寸則可。假如瓶高二尺,肚大下實者,花出瓶口二尺六七寸,須折斜冗花枝,鋪撒左右,覆瓶兩旁之半,則雅。若瓶高瘦,卻宜一高一低,雙枝或屈曲斜裊,較瓶身少短數寸,似佳。最忌花瘦于瓶,又忌復雜,如縛成把,殊無雅趣。若小瓶插花,令花出瓶,須較瓶身短少二寸,如八寸長瓶,花只六七寸方妙。若瓶矮者,花高于瓶二三寸,亦可插花有態,可供清賞。”張謙德則說:“大率插花須要與瓶稱,令花稍高于瓶。假如瓶高一尺,花出瓶口一尺三四寸;瓶高六七寸,花出瓶口八九寸乃佳。忌太高,太高瓶易仆;忌太低,太低雅趣失……小瓶插花,宜瘦巧,不宜繁雜。若止插一枝,須擇枝柯奇古、屈曲斜裊者;欲插二種,須分高下合插,儼若一枝天生者……瓶花雖忌繁冗,尤忌花瘦于瓶,須折斜斜欹花枝鋪撒小瓶左右,乃為得體也。”


其實,自古以來,中國有類似高濂、張謙德等太多的先賢深明“花器兩相宜”之義,且對此有相當深入的研討。花與器相得益彰,乍看似易,實則極難。更重要的是,在花與器相稱的同時,還要表現出中國傳統插花的意境與內涵來。插花與繪畫一樣,有定法而無定式,插花者愛花識卉有多少、藝術造詣的高低、審美情趣之雅俗,最見功力。因此,細審先賢如何賞花插花,回顧歷代插花如何在花的世界探求“天人合一”的至高哲學,無論是現在抑或將來,對再次復興的中國傳統插花藝術仍有著深遠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