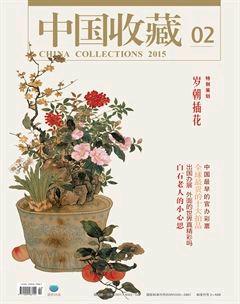遷想妙得 筆墨哲思
筱軒
中國近現(xiàn)代書畫藝壇名家輩出,知名者數(shù)以千計,因為與世界藝術文明的正式接軌,也造就了豐碩的藝術面貌與表現(xiàn)形式。這不到一個世紀的近現(xiàn)代書畫藝壇,在數(shù)千年書畫藝術長河的撐持與推擁下,在堅持筆墨元素的大前提下,水到渠成地踏進了世界藝術舞臺。

『遷想妙得』,這句傳統(tǒng)畫理名言最能體現(xiàn)近現(xiàn)代書畫藝壇承先啟后的內涵,也最能啟迪當前憂慮中國書畫或將隨快餐文明式微的迷惘。
張大千《佛頭青牡丹》
尺幅:145厘米×69厘米
在《張大千畫》中有關于“工筆牡丹”一文,張大千對描繪佛頭青技法之掌握運用已有極為詳細的說明。若追源溯始,可推及甲申嘉平月本《佛頭青牡丹》上之題跋,曰:“昔居海上,于王雪岑丈齋中見刁光胤《五色牡丹》、強邨翁齋中見道君皇帝《佛頭青》,并效唐法,元明以來寫意,雖輕膩可愛,而秾姿貴彩不可得見矣。”可知,見諸朱祖謀所藏的宋徽宗趙佶本,正是大千筆下佛頭青所宗者。
復考大千的工筆重彩牡丹,構圖取折枝,于綠葉遮護下逞其獨艷豐姿。惟本幅則屬近五尺大幛,在碧綠枝葉簇擁下,佛頭青牡丹結伴成雙,益見主次伴襯之序。而如此根莖枝葉連系生長之處理手法,在其牡丹畫中極為稀見。
20世紀初至中后期的民國藝壇,由于西方藝術表現(xiàn)形式與觀念技法的全面輸入,使中國近現(xiàn)代書畫呈現(xiàn)出百花齊放的大開大合氣。在這短短幾十年間,全中國的書畫家不論在人數(shù)、風格、派別、社團組織和美術院校的質與量上,都呈現(xiàn)出中國書畫歷史長河中前所未見的蓬勃景象。同時,在人文內涵與筆墨鍛煉的深厚基礎條件上融合中西、汲古開今,開拓出無比廣闊的發(fā)展道途。
而與中國書畫史上各個興盛時期相較,近現(xiàn)代書畫藝壇當時所處的大環(huán)境無疑是前所未見的復雜紛亂,政治、軍事、經(jīng)濟、社會……都陷入內憂外患不斷的詭譎局面。雖然“五四運動”揚起了知識分子淑世救國的大纛,創(chuàng)造了文學、藝術的犖犖大觀,但是也因為時代的動蕩不安,使得民國時期豐碩的文學、藝術圖文史料匯整幾乎付之闕如,中國書畫史至清代為止即已斷層。而接續(xù)清代的20世紀近現(xiàn)代民國書畫史的撰寫,就成為當今海峽兩岸學術領域的極大責任。
所幸,近20年來,祖國大陸改革開放后國力快速崛起,中國文物藝術品市場也隨之興盛。作為文物藝術品市場最大板塊的中國書畫,也將潛藏散佚于民間近百年的書畫作品放量而出,形成巨大的市場規(guī)模。其中,近現(xiàn)代書畫的數(shù)量更如筆湖墨海,成為中國書畫市場的主角。
事實上,近現(xiàn)代書畫在以典藏古代書畫文物為主的各地美術館、博物館庋藏中,質量畢竟有限,因此給予了文物藝術品市場最好的流通條件。海內外藏家或私人美術館在這20年來于藝術市場上所搜羅競價而得的近現(xiàn)代書畫杰作宛如泉涌,不但印證了近現(xiàn)代書畫藝壇的豐沛面貌,也進一步提供了學者專家書寫中國近現(xiàn)代書畫史最深最廣的實物與最全面的資料素材。
中國近現(xiàn)代書畫藝壇名家輩出,知名者數(shù)以千計,因為與世界藝術文明的正式接軌,也造就了豐碩的藝術面貌與表現(xiàn)形式。這不到一個世紀的近現(xiàn)代書畫藝壇,在數(shù)千年書畫藝術長河的撐持與推擁下,在堅持筆墨元素的大前提下,水到渠成地踏進了世界藝術舞臺。
然而,人文積淀深厚、需要咀嚼品味的中國書畫藝術卻在功利主義與快餐文明侵蝕社會價值觀的今天,潛藏著被大眾漠視忽略的危機。甚至連高等美術教育中,“書畫”一詞都已被打入“冷宮”,即使作為“水墨”創(chuàng)作者或教師,亦不乏認為中國書畫是“傳統(tǒng)包袱”已不合時宜的論調,動輒以強調“觀念”作為打擊筆墨基礎鍛煉的擋箭牌。中國書畫的薪傳在20世紀初期至中后期達于巔峰,卻在進入21世紀后面臨著成為“失根的蘭花”的隱憂。
希冀能夠在一片漠視中國書畫本質的逆流中撥亂反正,莫過于藉由杰出的傳世真跡作為最佳的實物教材與印證,而近20年龐大的書畫市場所提供的資源,正可建構出這樣的局面。剛剛在臺北國父紀念館中山國家畫廊落下帷幕的“遷想妙得—中國近現(xiàn)代書畫擷萃”展覽,其規(guī)劃即由此出發(fā)。
之所以選擇近現(xiàn)代書畫作為展覽主軸,即因為這個時期不但在時序上距離今日最近,同時,在民國藝壇的多元發(fā)展中又可見到眾多接收世界藝術文明養(yǎng)分的實例,明確地說明了中國傳統(tǒng)書畫在歷史傳續(xù)中的海納百川與包容大度,對視“傳統(tǒng)”為洪水猛獸者正可振聾發(fā)聵。
以“遷想妙得”作為這次展覽的主題,在于此句傳統(tǒng)畫理名言最能體現(xiàn)近現(xiàn)代書畫藝壇承先啟后的內涵,也最能啟迪當前憂慮中國書畫或將隨快餐文明式微的迷惘。
這句出自東晉顧愷之《魏晉勝流畫贊》的畫語,不僅僅只是人物畫的闡述,而可放諸于中國書畫的全面性適用。“遷想妙得”強調了中國書畫家在藝術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主觀意念與構思,將主觀情思藉由豐富的想像移情于客觀物象之中,而達到作品的傳神之妙。以今日最為流行的語匯來說,“遷想妙得”的實質意涵恰恰就是諸多高談創(chuàng)新者所朗朗上口的“觀念”,而中國書畫所揭橥的主觀觀念卻早在2000年前即已由“遷想妙得”加以實踐,而非空談。更進一步來說,“遷想妙得”這種中國古代的主觀觀念思考,絕非書空咄咄的紙上談兵,反而需要筆墨與學養(yǎng)的累積作為根基,筆墨與學養(yǎng)基礎扎得愈深,于“遷想”中的悟性就愈高,在作品中的“妙得”之處就愈精彩。
由臺灣資深藝術機構羲之堂策展的“遷想妙得—近現(xiàn)代中國書畫擷萃”大展,在體現(xiàn)中國書畫既需筆墨根基又具觀念思維且能新意勃發(fā)、兼容并蓄的大前提下,精選出40余位近現(xiàn)代書畫名家的百余組件各類型杰作,在作品整體內涵上側重于中國書畫的人文層面,將中國書畫藝術的生活美學與形而上人文哲思的態(tài)度完整呈現(xiàn),期盼能喚起社會大眾對中國書畫藝術的重新審視。

康有為 ?行書三十二言聯(lián)
尺幅:368.8厘米×43.8厘米
1917年,友人資助康氏于杭州西湖丁家山購得30余畝地,并營別墅。庚申(1920年)秋冬之際落成后,康有為自撰文并書此長聯(lián)。
此聯(lián)64字雜糅諸多佛莊之語,康有為歷經(jīng)變法失敗、流亡海外、復辟再失意等人生大起大落后,內心歸于沉寂,從聯(lián)語中流露無遺。內容字字獨立,結體開張,焦墨重筆,點提勾畫,遒勁潑辣。不求秀雅輕盈,筆畫間多飛白,書寫時追求碑石斑駁蒼勁感。結體嚴密,不尚姸美,自有一番古茂渾樸筆趣。

吳昌碩 ?沈曾植 ?行書詩扇
此扇為吳昌碩、沈曾植書贈丁輔之。丁輔之為西泠印社創(chuàng)始人之一。1922年春,西泠印社為吳昌碩慶八十大壽,日本雕塑家朝倉文夫所塑吳氏半身像也同時置入西泠印社“缶龕”之中,像贊即為沈曾植所書。同年夏,丁輔之于西泠印社發(fā)行珂羅版《缶廬近作》,為此書題端者亦為沈曾植。此書發(fā)行后,丁輔之請吳昌碩以小行書錄寫于西湖所作八首詩數(shù)百字于此扇,吳昌碩與丁輔之交情極深,自是精心書贈。之后,丁輔之又請沈曾植于扇背同樣以小字書寫舊作,再配以湘妃扇骨,遂完成此一佳構。
此扇吳昌碩所書數(shù)百字,字體雖小而氣魄宏偉;沈曾植所書則龍游鳳舞、峻峭瑰麗、奇趣橫生,盡顯沈氏書風。此件書法成扇記錄了吳昌碩、沈曾植兩位清末民初書壇大家與忘年之交丁輔之的特殊情誼,于書法藝術的價值之外亦增添了近現(xiàn)代書壇上切磋書藝、惺惺相惜的文人風采。

徐悲鴻《睡獅猛醒》
尺幅:112厘米×81厘米
徐悲鴻不僅擅畫動物題材,而且皆有深遠寓意,此幅《睡獅猛醒》即為激勵民心之杰作。畫中雄獅踞于畫面前方山巔之上,側身作勢,蓄勁待發(fā),瞠目直視,眼神凌厲。而雄獅身后則以花青淡染遠山,拉出遼闊的空間以襯托雄獅之氣概。有趣者為雄獅盯視之畫面左下角,隱現(xiàn)一屈曲蛇尾,正符合題識所言,百獸之尊,高行無畏,窺伺丑蛇,只能竄逃。
此畫作于1935年春徐悲鴻出任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主任時期,此時日軍已于中國各地四處挑釁,制造事端,狼子野心暴露無遺。徐悲鴻此作藉由雄獅“浩然氣可恃”以激勵民心,共御外侮。

李可染《千巖競秀 萬壑藏云》
尺幅:104厘米×78厘米
此幅完成于1988年的大作,是李可染去世前一年集山水藝術大成的經(jīng)典,構圖新奇,氣象壯闊。此幅大作融合了中國傳統(tǒng)的“三遠”構圖,參差錯落的千巖萬壑隨著視覺深度依次遠去,山形或巨大雄渾如北宋“巨碑”派,或瘦削如筍似張家界奇景,或獨自矗立,或橫亙相接,有北派山水的壯麗雄奇,又有南方山水的氤氳幽邈,實為李可染一生游歷寫生對于瑰麗山河的綜合與總結。

林風眠《火燒赤壁》
尺幅:68.5厘米×67.1厘米
《火燒赤壁》是林風眠晚年一再創(chuàng)作的題材之一。1989年,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林風眠回顧展”,林風眠親自挑選本幅參展,可見其對此作的滿意度。與同一題材之其他作品比較,此作構圖、處理手法基本相同,最顯著的差別也是另幅所無的,正是畫中只見如戲曲臉譜的諸色歷史人物面貌在火光濃煙中若隱若現(xiàn),卻未見描繪身軀,連勾畫頸部或肩膊的簡練線條也未見。畫家更簡化了畫面的具象視覺效果,將半抽象表現(xiàn)手法往前推進了一步,焦點全置于面容神情的刻畫,烘托畫面之氣氛更充滿張力,隨著燃燒熾烈的感情膨脹擴充至每一寸空間。掙脫了形體所帶來任何束縛的可能性,或許正反映了林風眠晚年創(chuàng)作已臻無拘無束之境地。
20世紀初至中后期的民國藝壇,由于西方藝術表現(xiàn)形式與觀念技法的全面輸入,使中國近現(xiàn)代書畫呈現(xiàn)出百花齊放的大開大合氣。在這短短幾十年間,全中國的書畫家不論在人數(shù)、風格、派別、社團組織和美術院校的質與量上,都呈現(xiàn)出中國書畫歷史長河中前所未見的蓬勃景象。同時,在人文內涵與筆墨鍛煉的深厚基礎條件上融合中西、汲古開今,開拓出無比廣闊的發(fā)展道途。
而與中國書畫史上各個興盛時期相較,近現(xiàn)代書畫藝壇當時所處的大環(huán)境無疑是前所未見的復雜紛亂,政治、軍事、經(jīng)濟、社會……都陷入內憂外患不斷的詭譎局面。雖然“五四運動”揚起了知識分子淑世救國的大纛,創(chuàng)造了文學、藝術的犖犖大觀,但是也因為時代的動蕩不安,使得民國時期豐碩的文學、藝術圖文史料匯整幾乎付之闕如,中國書畫史至清代為止即已斷層。而接續(xù)清代的20世紀近現(xiàn)代民國書畫史的撰寫,就成為當今海峽兩岸學術領域的極大責任。
所幸,近20年來,祖國大陸改革開放后國力快速崛起,中國文物藝術品市場也隨之興盛。作為文物藝術品市場最大板塊的中國書畫,也將潛藏散佚于民間近百年的書畫作品放量而出,形成巨大的市場規(guī)模。其中,近現(xiàn)代書畫的數(shù)量更如筆湖墨海,成為中國書畫市場的主角。
事實上,近現(xiàn)代書畫在以典藏古代書畫文物為主的各地美術館、博物館庋藏中,質量畢竟有限,因此給予了文物藝術品市場最好的流通條件。海內外藏家或私人美術館在這20年來于藝術市場上所搜羅競價而得的近現(xiàn)代書畫杰作宛如泉涌,不但印證了近現(xiàn)代書畫藝壇的豐沛面貌,也進一步提供了學者專家書寫中國近現(xiàn)代書畫史最深最廣的實物與最全面的資料素材。
中國近現(xiàn)代書畫藝壇名家輩出,知名者數(shù)以千計,因為與世界藝術文明的正式接軌,也造就了豐碩的藝術面貌與表現(xiàn)形式。這不到一個世紀的近現(xiàn)代書畫藝壇,在數(shù)千年書畫藝術長河的撐持與推擁下,在堅持筆墨元素的大前提下,水到渠成地踏進了世界藝術舞臺。
然而,人文積淀深厚、需要咀嚼品味的中國書畫藝術卻在功利主義與快餐文明侵蝕社會價值觀的今天,潛藏著被大眾漠視忽略的危機。甚至連高等美術教育中,“書畫”一詞都已被打入“冷宮”,即使作為“水墨”創(chuàng)作者或教師,亦不乏認為中國書畫是“傳統(tǒng)包袱”已不合時宜的論調,動輒以強調“觀念”作為打擊筆墨基礎鍛煉的擋箭牌。中國書畫的薪傳在20世紀初期至中后期達于巔峰,卻在進入21世紀后面臨著成為“失根的蘭花”的隱憂。
希冀能夠在一片漠視中國書畫本質的逆流中撥亂反正,莫過于藉由杰出的傳世真跡作為最佳的實物教材與印證,而近20年龐大的書畫市場所提供的資源,正可建構出這樣的局面。剛剛在臺北國父紀念館中山國家畫廊落下帷幕的“遷想妙得—中國近現(xiàn)代書畫擷萃”展覽,其規(guī)劃即由此出發(fā)。
之所以選擇近現(xiàn)代書畫作為展覽主軸,即因為這個時期不但在時序上距離今日最近,同時,在民國藝壇的多元發(fā)展中又可見到眾多接收世界藝術文明養(yǎng)分的實例,明確地說明了中國傳統(tǒng)書畫在歷史傳續(xù)中的海納百川與包容大度,對視“傳統(tǒng)”為洪水猛獸者正可振聾發(fā)聵。
以“遷想妙得”作為這次展覽的主題,在于此句傳統(tǒng)畫理名言最能體現(xiàn)近現(xiàn)代書畫藝壇承先啟后的內涵,也最能啟迪當前憂慮中國書畫或將隨快餐文明式微的迷惘。
這句出自東晉顧愷之《魏晉勝流畫贊》的畫語,不僅僅只是人物畫的闡述,而可放諸于中國書畫的全面性適用。“遷想妙得”強調了中國書畫家在藝術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主觀意念與構思,將主觀情思藉由豐富的想像移情于客觀物象之中,而達到作品的傳神之妙。以今日最為流行的語匯來說,“遷想妙得”的實質意涵恰恰就是諸多高談創(chuàng)新者所朗朗上口的“觀念”,而中國書畫所揭橥的主觀觀念卻早在2000年前即已由“遷想妙得”加以實踐,而非空談。更進一步來說,“遷想妙得”這種中國古代的主觀觀念思考,絕非書空咄咄的紙上談兵,反而需要筆墨與學養(yǎng)的累積作為根基,筆墨與學養(yǎng)基礎扎得愈深,于“遷想”中的悟性就愈高,在作品中的“妙得”之處就愈精彩。
由臺灣資深藝術機構羲之堂策展的“遷想妙得—近現(xiàn)代中國書畫擷萃”大展,在體現(xiàn)中國書畫既需筆墨根基又具觀念思維且能新意勃發(fā)、兼容并蓄的大前提下,精選出40余位近現(xiàn)代書畫名家的百余組件各類型杰作,在作品整體內涵上側重于中國書畫的人文層面,將中國書畫藝術的生活美學與形而上人文哲思的態(tài)度完整呈現(xiàn),期盼能喚起社會大眾對中國書畫藝術的重新審視。

張大千《春山積雪》
尺幅:75.9厘米×54.6厘米
此作擬仿宋人畫《春山積雪》、《雪江岸景》等天寒地凍的早春景象,承衍李成、郭熙一脈山水風格,卻以青綠潑墨潑彩風格揮寫,另出蹊徑,別具手眼,可謂“上追古人,后啟來者”。山頂積雪沉郁渾厚,遠景山色濃郁,相互輝映而有光源躍動的樣子;近景江岸滔滔卷起千堆雪,氣勢雄渾奔放,雪意蒼茫,寒氣逼人。畫面有著真山實水的生動氣韻,是張大千大青綠寫意寒冬雪景的杰作。據(jù)署款可知,本幅為大千先生壬午年(1942年)七月畫,時44歲,而此際大千先生正于敦煌臨摹壁畫,莫高、榆林石窟中鮮麗的色彩給他以許多靈感。以畫論,是為盛壯時期的精心杰制。

吳湖帆《浮巒暖翠圖》
尺幅:731.5厘米×32.8厘米
筆者所見傳世吳湖帆作品中,最覺動人心魄者有兩件,其一是上海私人收藏的《如此多嬌》冊十開,另一件則是此臺北私人收藏、長逾七米的《浮巒暖翠圖》。
此幅作于1955年,正值吳氏筆墨日益升華的時期,堪稱諸妙俱備,神采煥然。此卷尤為特殊,至少是筆者所見吳氏一生所畫手卷中最長、最精絕的一件。從卷尾題跋中可知,此圖為吳氏“費時二月完成”,足見此畫在吳氏傳世作品中具有何種分量。
此卷擬仿的是南宗宗主黃大癡的名跡。就在此前的1954年,吳氏擬仿了黃氏的另一件長逾7米的名作——《富春山居圖》。
全畫除結構位置外,筆墨設色已全然是吳湖帆極盛期的面貌,落墨沉厚蒼潤,用筆縱肆簡逸——往往以闊筆豪縱抒寫,如庖丁解牛,視如無物,而山石結構已然俱足。復以小筆勾寫樹色,禿筆點葉復點苔,兔起鶻落,毛辣蒼雄,尤見筆力。設色則于重色青綠中點綴丹黃朱紫,明麗中特見沉厚,絢麗中尤多素雅。比諸煙客、廉州,雖少沉穆氣,卻多鮮活感。寓目所見,已全然是一派卓然獨立的梅景風韻(下圖為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