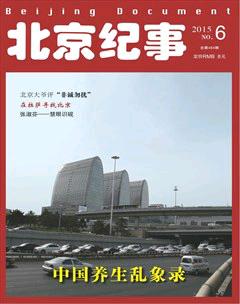張淑芬——慧眼識(shí)硯
余瑋



“武士愛(ài)劍,文人愛(ài)硯。”在中國(guó)傳統(tǒng)的筆、墨、紙、硯這“文房四寶”中,硯固然排在最末,但其文化含量和收藏價(jià)值卻居領(lǐng)銜地位。
“窗竹影搖書(shū)案上,野泉聲入硯池中。”在性情浪漫的古代文人眼中,山水是詩(shī)畫(huà),自然即文章,而這都離不開(kāi)案頭一方靜默的石硯,它是古人借以揮灑才情寄托憂樂(lè)的工具。如今,硯雖然從案頭挪移到博古架上,但收藏者依舊不改對(duì)它的一片癡情。
對(duì)面的長(zhǎng)者,是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張淑芬。在永安賓館的咖啡廳里,記者與這位著名文博專(zhuān)家、雜項(xiàng)鑒定專(zhuān)家邊品茶邊賞硯。張淑芬娓娓而談自己獨(dú)特的文博經(jīng)歷和與鑒賞的不解之緣……
自大宅門(mén)到故宮博物院
張淑芬出生在廣東番禺,3歲那年隨祖輩遷到北京,最初長(zhǎng)時(shí)間住在北京的番禺會(huì)館,直到成年后才和家人過(guò)著獨(dú)門(mén)獨(dú)院的生活。
出身于大戶(hù)之家的張淑芬對(duì)古董、古玩的接觸是從童年就開(kāi)始了。她的祖父張維屏少時(shí)就有詩(shī)才,聞名鄉(xiāng)里。嘉慶九年,張維屏中舉人,道光二年成進(jìn)士。此后,張維屏在湖北、江西任州縣地方官,一度署理南康知府。為官清廉,終因厭倦官場(chǎng)的腐敗,于道光十六年辭官歸里。張維屏和黃培芳、譚敬昭等并稱(chēng)“粵東三子”,且與林伯桐、黃喬松、譚敬昭、梁佩蘭、黃培芳、孔繼勛被譽(yù)為“詩(shī)壇七子”。小時(shí)候,張淑芬是典型的大家閨秀,對(duì)古玩、女紅很有興趣,還特別喜歡去博物館。接受采訪時(shí),她說(shuō):“家中先人是與林則徐同科的舉人,是當(dāng)年有名的詩(shī)人。鴉片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先輩和林則徐并肩戰(zhàn)斗過(guò)。家庭傳統(tǒng)深受‘唯有讀書(shū)高的思想影響。從我的祖母到很多姑母,她們都是不裹小腳、不扎耳眼、上洋學(xué)堂的新一代女性。”
文房雅玩自古以來(lái)都是文人墨客孜孜以求的,張府到處是精致典雅的筆墨紙硯。每每用畢書(shū)寫(xiě)工具,長(zhǎng)輩就會(huì)讓小淑芬擦拭硯臺(tái)。張淑芬常常為硯臺(tái)外觀的晶瑩透亮、紋理的細(xì)膩清秀所吸引。
20世紀(jì)60年代,張淑芬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當(dāng)時(shí)的冷門(mén)專(zhuān)業(yè),進(jìn)入文化部文化學(xué)院文物博物館系學(xué)習(xí),次年轉(zhuǎn)入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美術(shù)史系。大學(xué)共用6年的時(shí)間學(xué)習(xí)繪畫(huà)、書(shū)法及文化史論課。畢業(yè)實(shí)習(xí)的時(shí)候,她還參加了廣東一處東漢墓葬的發(fā)掘工作,成為中國(guó)為數(shù)不多的最早從事考古工作的女性之一。
“1966年8月家被抄了以后,大家族不復(fù)存在。我拿著一床薄被和一口破鍋,開(kāi)始獨(dú)立生活。不久,我們畢業(yè)被分到張家口的部隊(duì)去鍛煉,一去就是5年3個(gè)月。那時(shí)對(duì)于自己的未來(lái),完全不敢想,只能用‘心情非常壓抑來(lái)形容。”但是這并沒(méi)有改變張淑芬的志向,1973年回到北京的她最終還是進(jìn)入了故宮博物院。
然而很快,職業(yè)生涯再次遭遇不幸。“文革”期間,故宮大門(mén)一閉就有5年之久,在許多地方名勝古跡慘遭破壞的時(shí)候,故宮得以幸免。“文革”使得故宮博物院的正常展出和研究工作幾乎全部中斷。張淑芬每天只能做一些文物檔案的記錄、抄寫(xiě)工作。
來(lái)到故宮之后,張淑芬最先進(jìn)入到文物保管部。后來(lái),她進(jìn)入了陳列部,這是國(guó)寶級(jí)文物展出的地方。每換一次文物,她都記下資料,私下里自己揣摩學(xué)習(xí)。由于她對(duì)工作認(rèn)真負(fù)責(zé),不久又去從事“文房四寶”(文房清供)及竹、木、牙、角工藝類(lèi)藏品的陳列和研究工作,這一干就是一輩子。“當(dāng)年,市場(chǎng)并不看好‘文房四寶,加上我是學(xué)美術(shù)出身的,一時(shí)心里還難過(guò)好一陣子。但是,我不停地告訴自己要爭(zhēng)氣,要作出成績(jī)來(lái)。”
功能被“擱置”之外的文化
“古玩行按照收藏對(duì)象的不同,大致分為書(shū)畫(huà)、陶瓷、玉器、銅器、家具、雜項(xiàng)幾大類(lèi)。當(dāng)然,這只是一種分法。但不論怎么分,雜項(xiàng)都被放在最后,將其他類(lèi)別不要的一股腦兒全收了進(jìn)來(lái)。”張淑芬說(shuō),不過(guò),這并不是雜項(xiàng)收藏的地位低,反過(guò)來(lái),它說(shuō)明了雜項(xiàng)的廣博、豐富。
硯是文房大項(xiàng),“四寶”之重。張淑芬說(shuō),硯臺(tái)在古代差不多是最早被當(dāng)作雅玩的文房用具,也是傳統(tǒng)文人最珍視的文玩。
硯石雕刻制作不同于其他的工藝,每塊石料材質(zhì)各異,依此設(shè)計(jì)和雕刻出的作品,即便是圖案大體相同,實(shí)際顏色、細(xì)節(jié)等也幾乎“獨(dú)一無(wú)二”,這就給了硯臺(tái)極大的創(chuàng)作空間。張淑芬認(rèn)為,當(dāng)今硯文化的出路應(yīng)該在傳承上不失硯功能的形制,在繼承傳統(tǒng)工藝技法上少用機(jī)工、多用手工藝雕刻技法創(chuàng)新思路,題材內(nèi)容為歷史、文學(xué)、神話、故事等人文內(nèi)涵豐富的主題,反對(duì)異造,要因材施藝,突出硯石的材質(zhì)美感,為制硯藝術(shù)的重要追求。“雕刻要善于利用硯臺(tái)材料和天然特性,材質(zhì)、形狀、色澤、紋理、石眼等都是創(chuàng)作的元素,甚至可以變廢為寶,顯瑜掩瑕,充分利用硯材本身特點(diǎn)給人的美感。”正因?yàn)槌幍淖饔谜D(zhuǎn)向品賞和收藏,所以就必然地要更加注意它的石質(zhì)、雕工、銘刻、品相裝飾、藝術(shù)構(gòu)思等,把硯當(dāng)成藝術(shù)擺玩和人文風(fēng)景。張淑芳高興地看到許多硯的創(chuàng)意推陳出新,將現(xiàn)代雕塑書(shū)畫(huà)藝術(shù)融入傳統(tǒng)的設(shè)計(jì)雕刻,提升了硯臺(tái)的品質(zhì)。當(dāng)然,隨著硯臺(tái)實(shí)用性的市場(chǎng)價(jià)值不斷衰退,人們對(duì)其藝術(shù)性、觀賞性和收藏性也有了更高需求。
針對(duì)目前國(guó)內(nèi)民間收藏?zé)岬某掷m(xù)升溫,有時(shí)單件藏品的漲幅令人咋舌。張淑芬則不忘給火爆的收藏市場(chǎng)“潑冷水”,認(rèn)為不能盲目進(jìn)入收藏市場(chǎng)。“硯臺(tái)作偽,主要在石材上動(dòng)手腳。我國(guó)硯材豐富,品種繁多。鑒別硯臺(tái)的真?zhèn)危瑧?yīng)該先看它是什么硯石、產(chǎn)在什么地方、石性如何、紋理有什么特點(diǎn);進(jìn)而再看石品、紋理、雕刻手法、鐫硯裝飾是否與時(shí)代特點(diǎn)相同。”張淑芬說(shuō),端硯石料名貴,偽造者多用別處類(lèi)似、近似的石料雕琢,但細(xì)觀察可以發(fā)現(xiàn)石質(zhì)生硬,不溫潤(rùn)也無(wú)光,完全沒(méi)有幼嫩密實(shí)的特點(diǎn)。識(shí)硯有四招,即看色、手模、聽(tīng)聲、掂重。看硯色是否自然、是否經(jīng)過(guò)修補(bǔ),手摸石質(zhì)潤(rùn)滑的為佳,手感冰涼的好,不同材質(zhì)的硯臺(tái)敲打后音色也不同。”
收藏能夠改變?nèi)松J詹貝?ài)好者追求的應(yīng)是收藏過(guò)程中的喜怒哀樂(lè),或者從中悟出的人生哲理,而不是個(gè)人藏品的多寡貴賤。收藏者有打眼吃藥的痛楚,也有過(guò)撿漏的驚喜,甚至有踏破鐵鞋無(wú)覓處的惆悵和錯(cuò)過(guò)撿漏機(jī)會(huì)的遺憾,以及損壞一件心愛(ài)藏品的懊悔。張淑芬說(shuō),你不妨將這些悲喜看作一種常態(tài),任自己體味。
如今,硯的功能雖然已被“擱置”,但其歷史文化內(nèi)涵和藝術(shù)審美價(jià)值卻受到格外垂青而突現(xiàn)出來(lái)。“硯的本質(zhì)特征并沒(méi)有消失,古今的間隔和視角的改變,不可能泯滅硯與非硯之界限。一方古硯雖不再拿來(lái)磨墨實(shí)用,但人們?nèi)匀灰曋疄槌帯R驗(yàn)樗?jīng)作為文人書(shū)案上的文具使用過(guò),它的實(shí)用性已沉淀為歷史性的永恒存在,已轉(zhuǎn)化為今天人們觀照、鑒賞的對(duì)象了,使人們產(chǎn)生一種深沉的歷史向往和審美愉悅。”
“小”硯臺(tái)里的大乾坤
在中國(guó)古代,硯的地位遠(yuǎn)遠(yuǎn)高于其他許多門(mén)類(lèi)的藝術(shù)品。除了文人喜愛(ài)之外,與皇家的寵愛(ài)不無(wú)關(guān)系。硯臺(tái)不是尋常家用擺件或生活實(shí)用器皿,畢竟它是直接參與書(shū)畫(huà)創(chuàng)作的主要工具。近年來(lái),出自清宮的文房用品紛紛現(xiàn)身拍場(chǎng),并在各路藏家的追捧下成交價(jià)格逐年走高,成為市場(chǎng)的新熱點(diǎn)。被譽(yù)為“大清國(guó)寶”的松花石硯尤其引人關(guān)注,據(jù)統(tǒng)計(jì)在已獲成交的60多方松花石硯中有8方拍出了上百萬(wàn)元的高價(jià)。
細(xì)查松花石硯的成交狀況,可見(jiàn)凡是拍出高價(jià)者無(wú)不出自康熙、雍正、乾隆這三代。同時(shí),據(jù)史料記載,松花石硯自被康熙帝看重,并在宮中造辦處設(shè)置硯作以來(lái),這三朝制作的數(shù)量最多、品質(zhì)最佳。投資收藏者如想收藏好松花石硯,就要了解這三朝制作松花石硯的狀況,把握三朝制品的特征,進(jìn)而判斷價(jià)值,準(zhǔn)確出手。張淑芬透露,目前北京故宮館藏的松花石硯僅80多方,臺(tái)北故宮有100多方,而且兩地故宮收藏的松花石硯多數(shù)是在康雍乾三朝制作的——北京故宮的藏品中有康雍乾三朝款銘的松花石硯39方,臺(tái)北故宮則有86方出自這三朝。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的狀況,是因?yàn)椋郧∈拍晗铝罘饨瘓?chǎng)后,便不再采石,宮中制硯都取用存料。而且隨著大清帝國(guó)的衰落,清宮中也無(wú)力大量制作松花石硯。可見(jiàn)本已十分名貴的松花石硯,更因?yàn)榇媸赖南∩儆l(fā)地彌足珍貴。據(jù)估算,目前流落在民間的宮廷松花石硯不足百方,其中絕大多數(shù)是溥儀逃出故宮時(shí)候帶走的。
張淑芬很迷戀于收藏,但是國(guó)家有規(guī)定,文物工作者在職期間禁止自己收藏或參加這方面的市場(chǎng)活動(dòng)。因此,她早期的藏品全是祖?zhèn)鞯摹M诵莺螅挥袝r(shí)間張淑芬都會(huì)到古玩市場(chǎng)看看,遇到有特點(diǎn)、有代表性的硯臺(tái)等精品會(huì)買(mǎi)下來(lái),作為收藏或以后講課時(shí)的素材。“逛古玩市場(chǎng)是收藏愛(ài)好者的必修課,更是基礎(chǔ)課。去市場(chǎng)要懂行話,識(shí)貨是基礎(chǔ),砍價(jià)見(jiàn)真?zhèn)巍J袌?chǎng)的騙子很多,不要輕易下手。”張淑芬提醒收藏愛(ài)好者,地?cái)偵先菀捉粚W(xué)費(fèi),熟人殺熟也做局。“高手也有打眼的時(shí)候,高手吃進(jìn)贗品后礙于面子,只能先當(dāng)精品藏著,然后再找機(jī)會(huì)以真品的價(jià)格轉(zhuǎn)讓給‘二五眼。”
歲月荏苒,韶華易逝。“世紀(jì)詩(shī)翁”臧克家曾詩(shī)曰:“老牛亦解韶光貴,不待揚(yáng)鞭自?shī)^蹄。”時(shí)光總從我們身邊無(wú)情地悄然溜過(guò),不留任何痕跡。然而,年過(guò)古稀的張淑芬樂(lè)作時(shí)間的主人,甘為文博付韶華。“我一直在搶時(shí)間,搶在自己還不糊涂、腿還能跑的時(shí)候多做一些事,為復(fù)興硯文化、弘揚(yáng)硯文化做些努力!”這正應(yīng)了自己的祖父張維屏早年寫(xiě)的訓(xùn)子孫之道“惜分陰”。
張淑芬的生活是那么多姿多彩,因?yàn)榕c硯結(jié)緣的她從中找到了硯文化的真諦,體味到了其中真趣。
(編輯·麻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