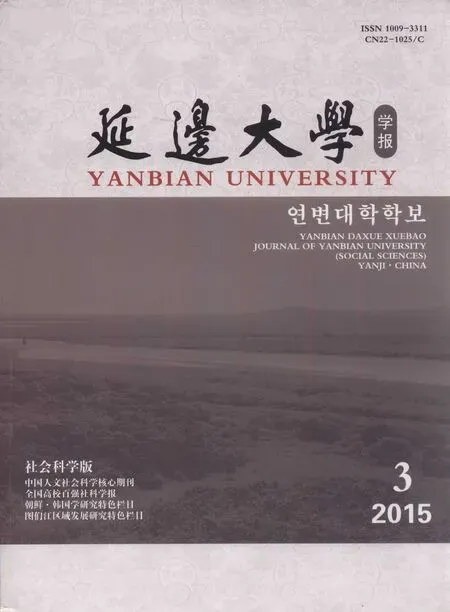姜敬愛與蕭紅小說的敘事結構藝術
劉艷萍
(延邊大學 漢語言文化學院,吉林 延吉 133002)
姜敬愛(1906-1944)與蕭紅(1911-1942)分別是20世紀30年代朝鮮和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頗有影響的女作家。她們雖然身處不同國度,卻同樣生活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都有著階級壓迫的體驗和國破家亡的民族恥辱,因此,她們的小說創作表現出20世紀30年代中朝現代文學共具的主流敘事方式,即展現貧富懸殊的階級差別和尖銳復雜的民族矛盾,而這又是通過壓迫─反抗的二元對立結構和場景表現出來的。然而,如果從當代敘事學的角度來分析,就可以看出,在這表面相同的背后,兩位作家小說的敘述視角和敘事結構都呈現出不同的模式。基于此,本文主要運用敘事學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理論,著重從敘事結構、敘述視角和話語模式等方面對其小說創作進行比較分析,并探討其成因,以期更好地把握同一時代不同國度的兩位女作家小說創作模式的同異。
一、敘事結構:縱式結構與橫式結構
作為小說的基本手段,傳統意義的敘事是指借助于獨白、倒敘、插敘等藝術手法表現一個完整而生動的故事情節,從中傳達出作者對生活的認識與感悟、創作目的與動機等。而作為一種文藝理論,敘事學(Narratologie)又稱為敘述學,它是直接采用結構主義方法來研究敘事作品內部結構規律和各種要素之間關聯的學科,隸屬于文本研究的形式批評范疇。它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的法國,很快傳播到其他國家,成為一股國際性的文學研究潮流。
從敘事的角度進行分析,姜敬愛小說傾向于故事的完整敘述,屬于縱式結構;而蕭紅小說則傾向于情節的片斷描寫,屬于橫式結構。縱式結構完全按照時間的先后順序和事件發生、發展的自然進程來安排情節;而橫式結構則是把若干表面上沒有必然聯系的生活場景或故事情節平列起來安排,以從各個不同的側面或角度共同表現作品的主題。縱式結構是一種全景展示,一般用于中心人物只有一個(也可以是兩個,平行展開,分頭敘述)、情節線索比較單純的敘事性文學作品,有利于表現主人公一生的經歷、遭遇或斗爭事跡。而橫式結構則是一種素描勾勒,一般用于散文或某些短篇小說,用于長篇則易造成結構松散等弊病。
姜敬愛的小說一般采用傳統的敘事體式,按照時間的順序和事件因果關系的脈絡,并在特定的敘事空間內展開情節,敘述故事的發展,情節充滿著矛盾和糾葛,完整劃一,人物也有著完整而發展的性格。她所創作的21部(不包括她與別人合著的兩部小說《年輕的母親》和《破鏡》)長、中、短篇小說基本上都是按照時間的順序,以一至兩個人物的故事為情節主線,有頭有尾、全景般地展現人物的現實命運。中心突出,情節有發展,有高潮,也有結局,非常集中而完整。譬如,《破琴》著重表現亨哲的精神苦悶和排解過程;《菜田》則描寫秀芳受繼母虐待并致死的過程。
然而,蕭紅小說在結構上雖然不乏對某事某物的詳細敘述,卻沒有貫穿全局的統一的故事情節,她“常常是通過一些素描式的生活場景的描繪和藝術境界的創設,通過對生命的深刻而獨特的體悟來感染、打動讀者,換言之,她的小說融入了更多的散文化的元素,增強了小說的抒情色彩”。[1]也就是說,蕭紅的小說與散文是互滲的,時間性不強,主要依靠空間關系來鋪敘故事,將敘述、描寫、抒情、議論等散文表達方式有機地結合起來,呈現出一種開放式的結構體式。下面以兩位作家的2部長篇小說為例,用略圖來標示并分析姜敬愛和蕭紅小說不同的敘事結構。先看姜敬愛的小說《母與女》:

圖1 《母與女》的敘事結構
《母與女》雖然設置了多條線索,如美麗與李春植的線索、珊瑚珠與崗壽的線索、玉與母親美麗的線索、玉與婆母珊瑚珠的線索以及玉與奉俊的線索等,但是整部小說都是以玉的個性覺醒為中心軸,統領其他線索和人物故事。小說開頭描寫獨守家庭的玉接到丈夫要離婚的信后而產生的不安和困惑,結尾表現個性覺醒后的玉毅然決定與丈夫奉俊離婚,而玉的母親美麗的故事、玉的婆母珊瑚珠的故事、玉童年的故事、玉與奉俊由婆母促成婚姻的故事等,都是通過玉的回憶倒敘出來的。小說依照時間順序展開故事,展現了玉擺脫舊思想的束縛和個性覺醒的過程,情節顯得緊湊而完整。兩位母親美麗和珊瑚珠作為對照性的形象出現,又共同襯托并突出了玉的形象。美麗被丈夫拋棄后自暴自棄,淪為男人的玩物;珊瑚珠被愛人拋棄后卻棄妓從良,自立自強,獨自撫養幼子和玉。兩位母親分別為玉樹立了兩種典型:母親美麗成為墮落可恥的典型,使玉時刻警醒不再重蹈母親的墮落之路;婆母珊瑚珠作為自強自立的典型,使玉體驗到人與人之間的關愛,從而自重自強。奉俊從東京留學歸來,移情別戀愛上了女學生淑姬,向玉提出離婚的請求。溫柔賢惠卻軟弱無力的玉由此陷入將重蹈母親與婆母被遺棄的命運中。對此,玉苦苦規勸并挽留奉俊,甚至蒙羞請淑姬來探望奉俊,可是奉俊執意離婚。一個偶然的機會,英實哥哥為勞苦大眾而義無反顧走上刑場的壯舉使玉幡然醒悟,認識到了自己的軟弱和蒙昧,決定擺脫對奉俊的依賴,與之離婚,做一個獨立自強的女性。可見,整部小說以玉的個性覺醒為主線,其他人物形象均是陪襯并為了塑造其性格而設置的,每個部分都是自足而缺一不可的,當然也不可添加其他的人與事,否則就會破壞整篇故事的完整性和玉形象的完美性。
《人間問題》也是按照時間順序和人物性格發展的邏輯來敘事,不過與前兩部小說稍有不同的是,它以阿大和善妃兩個人物為中心展開情節,時間是從苦難的童年一直寫到青年工人,空間是從農村(龍淵村)到城市(仁川)。

圖2 《人間問題》的敘事結構
從圖2可見,小說設置了兩條平行而又交叉的線索,一條是阿大─德浩─信哲的線索,另一條則是善妃─德浩─難兒的線索。前者表現阿大作為喝酒、打架、偷竊的農民,在知識分子信哲的幫助下成長為一名有階級覺悟、思想進步的碼頭工人;后者描寫溫順軟弱的善妃因忍受不了地主鄭德浩一家的侮辱與虐待,而到仁川大同紡織廠做女工,以及她在難兒的啟發教育下,逐漸產生階級意識和女性意識的過程。這兩條線索除了在小說開頭(童年時代,阿大搶善妃酸模、送給善妃媽苦楝根治病)和結尾(阿大見到死去的善妃)有所交匯外,在整個故事情節運行過程中都是齊頭并進,分別展開的。人物突出,線索清晰,情節也非常嚴整(見圖3)。
蕭紅小說的敘事結構則呈橫式結構,亦稱環式結構,以《生死場》為例(見圖3):

圖3 《生死場》的敘事結構
從圖3中可見,《生死場》描寫的是20世紀30年代生活在東北地區某鄉村里的人們生與死的過程,勾勒的是二里半、二里半的老婆麻面婆、王婆、趙三、月英、金枝等人物群體的生活與命運問題。與姜敬愛小說以人物為中心設置故事的傳統而封閉的敘事結構不同,《生死場》不是以某個人物為主線安排故事,而是圍繞生活在東北某鄉村這個生死場里的民眾的苦難圖景來設置情節的,每個故事都是獨立的,自成一體,但合在一起又從不同側面詮釋了生死場里的苦難與罪惡。從敘事結構上看,小說呈開放式特點,讀者還可以在此基礎上添加新的情節,繼續書寫生死場里的其他人與事。
《呼蘭河傳》也是如此,作者的創作意圖是為故鄉呼蘭河作傳,故而她分章描寫故鄉小城的民俗、人事特點等。譬如,第一章概括描寫呼蘭城的嚴寒氣候、街道布局和攤主經營的生意事項(火磨、學堂、農業學校、染坊、扎彩鋪、麻花、涼粉、豆腐等);第二章就描寫呼蘭小城的民俗,諸如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燈、野臺子戲、四月十八娘娘廟大會等;第三章寫“我”、祖父和后花園的樂趣;第四章則描寫租住在“我”家破房子里的漏粉人家和趕車人家的貧窮生活;第五章寫老胡家的小團圓媳婦進門后被折磨致死的經過;第六章介紹有二伯;第七章突出描寫馮歪嘴子與王大姐偷偷同居、生子的故事。如圖4所示:

圖4 《呼蘭河傳》的敘事結構
《呼蘭河傳》不以人物為中心,而以鋪敘事件和情境為主,一幅幅畫面宛若一個個特寫鏡頭,共同詮釋著呼蘭河的現實圖景。這種散文化的抒情小說體式,不僅表現在作者那孤寂憂傷的獨白上,而且還滲透在小說情境的生動描寫中。它不在意小說情節的完整統一和人物性格的典型刻畫,而是密切關注作者和主人公的情感抒發和情景交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姜敬愛是為人而設置故事,而蕭紅是為情節而寫人敘事。姜敬愛小說的人物與故事一經完成,就定型不變,深深地印入讀者心中;而蕭紅小說的人物與故事似乎還有發展和完善的空間,總能引起人的無限遐思。
二、視角選擇與話語模式:焦點透視與散點透視
視角(point of view)的字面意義是指觀察問題的角度,它也是敘述學頗為重視的一個領域,通常包含兩個常見的所指:一是結構上的,即敘事時所采用的視覺角度,它直接作用于被敘述的事件,結構上的視角是調節敘述信息和距離的重要手段;一是文體上的,指的是敘述話語的方式,即敘述者在敘事時通過文字表達或流露出來的立場觀點、語氣口吻等,它間接地作用于事件。下面針對姜敬愛與蕭紅小說中的視角進行分析與評價。
身子沒入海水里的亨哲臉和胳膊腿曬得好像黑人一樣黑,胸膛鼓起,堅硬的身體真的很可靠。他偶爾笑的時候,從黑嘴唇中略微看得到晶瑩的白牙,他全身散發著一股斗志,沒錯,他是地地道道的勇士,十足的男子漢。惠京看著恩淑咧嘴一笑,慢慢地跟在他的后面——踩著亨哲先頭留在沙子上的腳印兒——抓住輕輕走著的恩淑的手腕兒走去。[2]
這是姜敬愛小說《破琴》中的一段描寫。在此,作家采用第三人稱全知敘述視角描寫亨哲與帶著他的妹妹來海邊玩的惠京相遇,他們一起去海里游泳的場面。亨哲被描寫得英俊挺拔、胸肌闊健、男性魅力十足;而惠京則被表現為溫柔、話語不多,依戀著亨哲。惠京踩著亨哲留下的腳印兒走,其隱含著的性別話語是對亨哲的無條件順從。整篇小說從亨哲的視角觀察現實,思考前途、未來和與女友惠京的關系。惠京與亨哲雖然有著同等的學歷(大學生)和階級地位(貧農),但是他們在小說中的登場和地位是不平等的。亨哲首先登場,并處于主動和行動地位,力圖打破這黑暗的常規(“破琴”的寓意),想要行動,只是因前途渺茫而苦悶失落。而惠京則處于被動和等待地位,一旦亨哲找到出路,她便義無反顧地追隨亨哲,聽從亨哲對自己命運的安排。惠京的沉默使她拒絕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情節安排完全由亨哲這位發言者所主導,連敘述者的聲音有時也被亨哲的話語所超越,亨哲成為具有獨立自主意識的唯一的發話者。可見,該小說采用的是男性占優勢的視角,因此惠京根本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只能聽從男主人公亨哲的勸告與命令。并且,惠京的話語輕柔、簡短,口語色彩比較濃重,如“不是啊”、“我也跟你走”。而亨哲的話語堅定、威嚴,帶有命令性,是正式的書面語體。在亨哲眼里,惠京始終是一位需要照顧和保護的柔弱女性,他希望她活下去,將來成為優秀的女性和成功的人士。他卻從沒有問過始終處于沉默中的惠京的意愿和感受,因此惠京在小說里是被邊緣化了的人物。
《煩惱》的敘述視角幾次發生轉換,先是以第一人稱全知視角來敘述,然后轉換為第三人稱主人公敘述,這一敘述幾乎占據整篇小說,最后又轉回到第一人稱全知視角。作家采用直接引語(“請給我一碗水吧!”)、間接引語(我一旦明白這是不能超越的,便摸索著剛才放到書桌上的教科書,拿著站了起來。為什么屁股也是這么沉呢?)和自由間接引語(那位母親邊哭邊抓頭,不管有沒有吃的,讓我直到他兒子出來為止都一起住)的話語表述方式轉述化名為“R”的男主人公的話語。而從“R”所表述的話語里,讀者感知到了一位男人眼里的好女人——溫柔、善良而又正直的理想女性繼淳的形象。第一人稱全知敘述者“我”完全被第三人稱主人公敘述者的話語所吸引,除了說過幾句鼓勵和過渡的話,如“啊,真的!”表示感嘆;“是這樣嗎?”表示疑問;“不,快點都講了吧。”表示急切和催促;“是那樣啊!”表示明白和鼓勵外,幾近于一名沉默的聆聽者。并且直到男性發話者“R”結束自己冗長的故事為止,“我”都是同情并認同“R”對繼淳的評價的。可見,這里的“R”是一個曖昧而又抽象的符號,實際上代表著男性視野和男性觀點。
《母與女》采用第三人稱全知視角,借助特定人物(如作為第三人稱敘述者的女主人公玉)與其他人物(如美麗、珊瑚珠、奉俊等)之間的距離表達作者自己的思想意識。這里的“距離”是敘述者與女主人公間的協商,具有明確選擇的意義,能充分表達女主人公的“自我發現”和作家的女性意識。而作家是從富者與窮者、男性與女性相對立的二元世界來認識問題的,并且男性與女性的對立結構是由富者與窮者的二元對立演化而來的,這就強化了階級對立視點的作用。
蕭紅小說也多采用第一人稱主人公全知視角和第三人稱全知視角來敘述,但是話語模式非常豐富,有直接敘述/引語、間接引語和自由間接引語等多種表達方式。換句話來說,全知敘述者、主人公和旁觀者(聽眾)的話語交錯盤結,各自發表不同的意見,彼此都想壓過對方的聲音,而獨立地表達。正如俄羅斯著名文藝理論家巴赫金(1895—1975)在論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特點時所說的,“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真正的復調——這確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篇小說的基本特點”。[3]敘述的多聲部也是蕭紅小說區別于姜敬愛小說的主要特點,這一點在《呼蘭河傳》第4章第4節中表現得最為突出。該節描寫小團圓媳婦——一個天真純潔、不諳世事的女孩,被其婆婆折磨致死的慘劇。
小團圓媳婦剛剛14歲,剛進門時圓圓的臉,黑而長的大辮子,很是靈氣,也桀驁不馴。只因她“一點也不害羞,坐到那兒坐得筆直,走起路來,走得風快”,她的婆婆便看不順眼,為了給她一個下馬威,以便制服她,就成天打她,并且說她“是個胡仙旁邊的,胡仙要她去出馬……”,請來大神、二神天天夜里為她打鼓聯唱,又是扎草人,又是扎“替身”,又是焙藥吃。在此,鄉鄰的議論、老婆子們的餿主意、小團圓媳婦家人間的問答、胡家與出偏方的藥鋪廚子的對話、全知敘述者的插話、鄰居們的建議、胡家與訛錢的云游真人的對話、小團圓媳婦婆婆內心的獨白等構成了眾語喧嘩。[4]作家圍繞婆婆為“管教”小團圓媳婦而將她打出病來這件事,對聚攏來看熱鬧出主意、出藥方的眾旁觀者進行散點透視,模擬他們的態度和話語模式,一一記錄他們各自發出的不同聲音,并且用了162個括號將這些聲音括起來。
“說那……”表面上看是全知敘述者在轉述別人的話,其實誰在說話?是不確定的,讀者可以理解為周圍的旁觀者之一在說話,也可以看作是全知敘述者用反諷的語言說出自己心中的看法。在此和接下來的敘述中,全知敘述者故意隱瞞作品中人物的具體身份,只是用“他”或“有的”來指代說話者,這就避免了因具體指出其身份而造成的敘述語流的中斷。同時,全知敘述者在引文中還大量使用直接引語(“去,買上半斤來。給她治一治。”/“反正治不好也治不壞。”)、間接引語(除直接引語和最末一句話外都是)和自由間接引語(“人哪能夠見死不救呢?”/“但那是治病,也不是吃,又有甚么關系”)。自由間接引語在人稱和時態上與敘述描寫一致,難于區分,然而它不帶引導句,轉述語本身為獨立的句子。由于擺脫了引導句,受敘述語語境的壓力比較小,這一形式常常保留體現人物主體意識的語言成分,比如疑問句式、感嘆句式、不完整的句子、口語化或帶感情色彩的語言成分等。采用自由間接引語能夠有效地達到譏諷或詼諧的效果。自由間接引語是蕭紅小說慣用的手法,這也是其小說不同于姜敬愛小說的獨特話語模式。譬如,“但那是治病,也不是吃,又有甚么關系”這句在敘述者客觀可靠的敘述描寫的反襯下,用瘟豬肉治病的荒唐可笑就暴露無遺,從而增強了反諷的效果。
從讀者的角度來說,也能夠以旁觀者的眼光充分品味人物話語中的荒唐成分以及敘述者的譏諷語氣。在婆婆的虐待下,小團圓媳婦奄奄一息,這時,周圍的“好心人”紛紛提出自己的經驗性權威意見:扎草人燒掉、做“替身”、畫花臉、吃全毛雞、黃連豬肉焙面兒吃等。沒有誰發出批評和譴責婆婆虐待小團圓媳婦的話語,這樣,婆婆和眾看客的“善心”就被打上了問號。蕭紅描寫小團圓媳婦遭受婆婆和周三奶奶、楊老太太等村婦的虐待,意在反諷麻木而不覺醒的國民的劣根性,即這場鬧劇的主人公都是女性,是處于強勢的女性虐待、折磨處于弱勢的女性。而“我”則是公開(露面)的敘述者,在“我”之上,還有一個潛在(隱而不露)的全知敘述者,即不斷用反諷語言表達強烈抗議的作為潛在敘述者的作家。
可見,無論是公開的敘述者(“我”),還是潛在的敘述者(作者),都是從女性視角出發,憤怒地批判和諷刺落后村婦的愚昧、偏見、麻木和野蠻。這就逼迫讀者思考這樣的現實:女性受封建傳統思想(“三從四德”)的影響和毒害達到何種變態和令人發指的地步啊!正因為有了這群頑固不化的傳統女性的承繼和傳播,世俗社會對女性的偏見和束縛才能根深蒂固,并且口耳相襲,代代相傳,一直沿續至今。由此,作家蕭紅就站在女性視角,對傳統社會的陋習和性別偏見進行了憤怒的指斥和強烈的批判,充分表達了自己的女性意識。
短篇小說《出嫁》采用第一人稱主人公全知敘述的視角,通過“吃飯”和“看娶媳婦”兩個場景探討了女性命運。在前一場景里,主要通過間接引語和自由間接引語表現敘述主人公“我”的觀感;在第二個場景里,通過敘述主人公與小說人物小蓮的對話,采用直接引語的方式描寫女性的悲劇命運。“娶媳婦”可謂是鄉下最熱鬧的場景,菱姑、“我”、小妹妹蓮兒都跑上炮臺去觀看這“電影”。可是,“我”卻看不到新娘子,通過小妹才了解“新媳婦怕老婆子,她不愿意出門子”,所以“把眼睛都哭紅啦”,就用被子包起來。小說題目“出嫁”寓示著女性悲劇命運的開始,不是像小團圓媳婦那樣受到丈夫和婆婆的虐待和毒打,就是像嬸娘們那樣埋沒在生殖和繁瑣家務中,因此,女性在離開爹娘出嫁時都要痛哭,仿佛即將步入地獄一般。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姜敬愛與蕭紅小說均習慣采用第三人稱全知視角和第一人稱主人公全知視角來敘述,在敘述過程中都運用直接引語、間接引語和自由間接引語等話語模式,但是蕭紅小說更多地采用自由間接引語的形式,拉大第三人稱敘述者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姜敬愛小說主要以男性視角來表述,其主要敘述策略是借助發話者所設定并展開的談話氛圍進行焦點透視(一個固定視點);而蕭紅小說則側重從女性視角去觀察與描寫,運用反諷敘事的話語模式,通過散點透視(眾語喧嘩)的方式,批判傳統社會的輿論和偏見,揭露麻木愚昧的女性群體的集體無意識和對個體女性身心的戕害。
三、不同敘事結構模式的成因分析
通過對兩位作家小說敘事結構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姜敬愛采用典型而傳統的敘事模式來結構小說,即按照時間線索和人物性格發展的必然邏輯來敘事;而蕭紅則突破傳統的敘事結構,采用“散點透視”來結構小說。之所以如此,可從兩個方面分析其成因:一是創作觀,二是性別觀。
從創作觀上看,姜敬愛和蕭紅都基于強烈的人道主義立場,把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貧苦女性的不幸命運作為創作的重點,揭示世態的炎涼和人情的冷漠,鞭撻病態而丑惡的靈魂。然而,姜敬愛小說著重從階級意識著眼,以階級對立的觀點觀察生活,認識生活和反映生活,特別強調社會動蕩、階級關系變化和世俗偏見等現實客觀因素所導致的人情冷漠和精神病態,是外因引起內因的過程。其情感指向帶有鮮明的階級論色彩,即把日帝、地主、資本家作為社會丑惡的制造者,是著力批判的對象,而將廣大貧苦而善良的民眾當作同情、歌頌的對象。這種創作觀也是當時的主流創作意識,顯然受到“卡普”思想意識的影響。
蕭紅雖然也具有這種創作意識,但更關注從社會歷史和文化的角度來批判人性的弱點,揭示承繼著傳統因襲的人物內在心靈的扭曲和病態,是由內向外的發散過程。這種創作觀決定其小說不注重情節的完整敘述和人物性格的整一刻畫,而呈現出散文化的創作趨向。同時代文學批評家胡風就指出過《生死場》結構比較散,中心不突出。茅盾盡管肯定了《呼蘭河傳》的價值,也承認它的確不太像一部小說,“沒有貫穿全書的線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的,都是片斷的,不是整個的有機體”。[5]蕭紅的這種創作傾向據作家自己說是師法于魯迅先生。她曾說過,“有一種小說學,小說有一定的寫法,一定要具備幾種東西,一定寫得像巴爾扎克或契訶夫的作品那樣。我不相信這一套,有各式各樣的作者,有各式各樣的小說。若說一定要怎樣才算小說,魯迅的小說有些就不是小說,如《頭發的故事》、《一件小事》、《鴨的喜劇》等等”。[1]蕭紅的這種獨特個性和對現代小說創作的獨特理解與自覺追求,使她的小說別具一格,并超越時空,在倡導小說創作多樣化的今天獲得了長久的生命力和鑒賞價值。
從性別觀上看,姜敬愛與蕭紅都是女性主體意識比較強烈的作家,她們的小說都揭示了男女不平等的現實,并通過女性經歷與女性體驗展示女性自我覺醒的過程,表現出女性對自身悲劇命運的頑強抗爭精神。然而,姜敬愛小說主要表現保存傳統家庭范式基礎上女性之固有角色的性別意識,而且其性別意識往往因受到民族意識和階級意識的啟蒙和感召而產生,特別是受到階級意識的催動才發生,是從屬于階級意識的。以《人間問題》為例,敘述者把先驗的觀點與民眾視點(即集團視點)相結合,無論是“怨沼傳說”,還是作家先驗的觀點,都具有確定性和完結性的意義,讀者個人的主體價值判斷與修正都是不可能的,只能接受它。這種敘述策略是將女性的悲慘境遇納入到民眾集團的軌道上來,但卻以女性整體性的喪失為前提。換句話說,姜敬愛是采用男性的認知模式來看筆下受壓迫的女性的,這就必然把女性所受的壓迫與無知無識的民眾同一起來,而忽略了女性自身,當然也不會設置女性個人的空間。因此,其小說中的女性在階級意識和性別意識兩條道路上都走得不徹底。因此,作家為讀者勾勒的是“女性發現─民眾主義─現實主義”的視點運行軌跡,并借用積極進步的男性敘述視角來評判女性,所以其小說在表層結構上發現了女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女性不同的聲音,而在深層結構上卻立足于男性敘述視角,步入了男性中心的權力場中,這顯然是受到時代主流傾向(社會主義思想,即丈夫張河一的進步思想)影響的結果。[6]同時也與他認識并探求女性存在的角度有關,反映出作家并未以主體身份參與到朝鮮近代化過程和女性主義中來,這既是時代女性的局限,也是作家認識的局限。
蕭紅小說則從女性在戀愛、結婚、生育上與男性不平等的現實,敘述女性所遭受的不幸命運和悲劇,常以性別視角為創作切入點,從社會歷史文化和性別壓迫的角度進行反思和評說,表達出鮮明而強烈的性別意識。月英的慘死、金枝的偷情和失身、小團圓媳婦的夭折與其說是階級迫害的結果,毋寧說是性別歧視和性別偏見所造成的。蕭紅筆下的女性們不僅忙著生、忙著死,還要忍受日寇和地主的暴虐,更要提防成為男性的性奴隸。這樣,蕭紅小說就從生與死、心靈與肉體等多重層面寫出了女性的生存本相,并從個體生存體驗出發表達出一種集體生存的經驗,即男人的處世方式、秉性、德行并不比女人強,這是對男性清醒認識之后來自女性生命生存與生命發展的一種欲望和沖動。
總之,作為不同國度卻處于同一時代、身處相似社會文化語境中的兩位作家,姜敬愛與蕭紅在書寫底層民眾特別是女性的苦難和不幸命運、以女性視角觀察自然、人與女性等方面表現出諸多共同之處。然而,在小說敘事結構和視角的選擇上卻呈現出迥然不同的特點:姜敬愛小說屬于焦點透視,偏重縱式結構的建構,展現出傳統的敘事模式;蕭紅小說屬于散點透視,呈現橫式結構(環式結構)之特點,表現出散文化的傾向。盡管從敘事和性別批評的角度看,她們的小說利弊分明,但是從其小說的社會與美學意義上看,她們的小說具有同等價值,兩位作家同樣是不朽的!
[1]楊慶娟:《論蕭紅小說的抒情化特征》,《揚州教育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第51、52頁。
[2][韓]李相慶:《姜敬愛全集》,漢城:昭明出版社,1999年,第42頁。
[3][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白春仁、顧亞玲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第29頁。
[4]艾曉明:《戲劇性諷刺——論蕭紅小說文體的獨特素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年第3期,第53頁。
[5]肖鳳:《蕭紅研究》,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編:《現代文學講演集》,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225頁。
[6][韓]鄭美淑:《從敘述學看女性小說的特征》,《現代小說研究》2000年第13期,第317-3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