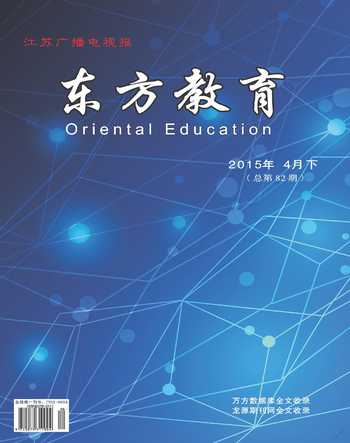不懂生活,不要妄談藝術創作
李澈
【摘要】生活與藝術之間存在著三層境界:來源于生活,深入生活,愛上生活。只有達到這三種境界,所做出來的作品才不會是空洞乏味的,脫離生活的藝術,就失去了藝術本質的東西。一個會生活、懂生活、愛生活的人才會創造出看得懂、記得住、可回味的好作品。
【關鍵詞】藝術;舞蹈創作;生活
田露老師的風格并沒有之乎者也那些浮浮躁躁的詞語,反而語言是輕松幽默、直如人心的。讓我總是在哈哈大笑過后啞口無言。針對于以中國民族民間舞為例談生活與舞蹈,老師有著獨特的經歷和獨到的見解,這讓我有著眾多的感悟。這些感悟我想用三個境界來總結:
一、“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藝術源于生活。哲學上講:“生活是第二自然。”生活是人與人、人與自然、物質與環境的一種關系,生活無處不在,而藝術則將無處不在的生活點綴的熠熠生輝。如果說藝術是藝術家們對生活的白日夢,雖然概念不同、形式不同,,藝術創作的途徑不同,,但異口同聲的,一定就是:生活無處不藝術!舞蹈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但凡是反映生活的藝術,歷來深受人們喜愛。我國各民族的先民們早就以舞蹈這種形式傳授生產知識和生活知識,寄托各民族的理想和愿望,進行廣泛的社交活動。由此可見,舞蹈起源生活實踐。
以中國民族民間舞為例,民族民間舞藝術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原生態、次生態、再生態、衍生態的衍化過程。將生活中司空見慣的行為加以提煉、加工最終衍生出我們所看到的舞蹈藝術。東北秧歌的演化過程與之相似,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中,它受到社會經濟、政治、地域文化、宗教、教育等多方面影響,動作大多來源于生產生活的日常行為 讓東北秧歌本身帶有詼諧、純樸豪放的靈性與風情。當時的社會對男女愛情的要求相對苛刻,根據習俗,每年只有特定的日子才可以男女共舞,造就了女孩在舞蹈中穩中浪,浪中翹,豪爽中不時羞澀的特點,男孩則是節奏鮮明,剛柔并濟。現如今北方地區在節日期間依然會用秧歌活躍氣氛,增進人們情誼。之所以秧歌經久不衰因為取材都是源于大眾生活,適宜大眾參與,能跳到大家心窩里去。并不是簡單的搬用而是經過提煉、升華,讓最能表現每個民族特征的舞蹈情緒化、形象化,讓觀眾知道所要表達的東西,也讓觀眾看后對這場舞蹈有所震撼、感動。讓作品更有生命力。總之,生活是舞蹈創作的源泉,舞蹈作品是生活的形象反映。能做生活與舞蹈之間不可或缺的紐帶的是優秀的編導,讓二者相互融合、兼容并蓄的是好作品。
二、“眾里尋它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要學會觀察生活。老舍先生說:“要天天記.養成一種習慣,刮一陣風,你記下來,下一陣雨,你也記下來,因為不知道哪一天,你的作品里需要描寫一陣風或一場雨。”要真實、細膩地反映生活,就一定要認真仔細地觀察生活。要想做出貼合生活的好作品,一定要在當地采風,融入風土民俗中,愛上這塊土地,只有這樣這片土地才會給你想要的回饋。關注國內比賽的人一定記得《翠狐》這部作品,作為民間舞的舞臺作品,其語匯語言的基礎是來自生活、貼近生活的。它為下層人民所培育、發展,表現著一般大眾的生活寫照。海陽秧歌的這些元素都是從人民生活中來,發源、孕育在民族生活與地方文化意識形態中。它源于蒲松齡《聊齋志異》里面的人物,通過海陽秧歌的風格特征完美生動的表現出了一個狐仙的形象。作品的成果與風土人情密不可分,海陽南鄰渤海、中部平原、北部丘陵山脈,得天獨厚的地理形式,鑄造了海陽格局的相對封閉,文化的相對穩定與系統,使得海洋文化保存相對更為完整。因為瀕臨海洋所以漁、鹽業發達,又因平原農耕文化交織發展,再加之山脈、丘陵的自然災害,使得海陽人的性格既樂觀、豪爽又堅忍不拔,在小富即安的悠閑心態下,形成了人與自然既和諧又矛盾的辯證生活觀。在相對隔絕的生活環境里,好聚忌散性格特征,使得載歌載舞的海陽秧歌增添了許多的人文背景下的集體結晶,這是這部作品的先決條件。對于狐仙有這樣一種說法,王大娘本就是傳說中的千年狐仙轉世,因為不甘山林的寂寞,來到凡間變成美貌、妖氣的姑娘。動作中即有人們的樸實又有狐仙的輕挑。《翠狐》作為民間舞的舞臺作品,其語匯語言的基礎是來自生活、貼近生活的。能將二者緊密結合起來,說明編舞者一定是深入生活中采風,仔細的觀察周圍的事物,才會有如此細膩、創新的產物。
三、“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作為一個編導,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對生活百分百的熱愛與投入,只有當完全融入生活,與周圍環境相融把周圍環境變成自己的一部分,像喜愛自己一樣喜歡周圍環境,這樣所看到的生活才是鮮活的。熱愛生活,除了對周圍環境、他人的關注。.還包括積極體驗生活,勇敢品嘗生活的各種滋味等。舞蹈與生活的鏈接莫過于“情”字舞蹈看似只是真實地重現了生活中的情景,既沒有情節和戲劇性的矛盾起伏 .也沒有更多的布景,但觀眾卻能從中獲得比來自生活情景更要深刻的審美感受,覺得 比真實 的生活現象更富有詩情畫 意。表演者不僅重現了生活情景,更突出表現了人的精界,利用舞蹈表演的方式將生活內容美化。這一切都離不jing開“情”。以《孔雀飛來》為例,再刀美蘭《水》之后又一經典的作品,塑造了一只優美、典雅、柔美,翩翩起舞的孔雀,在繼承傣族傳統的形態上又有著獨特的創新。編導用了細膩的肢體動作塑造了孔雀這個優美神圣的舞蹈形象。作品給人們留下的印象,不僅僅是那只美麗至極翩翩飛來的孔雀,體現了作者對孔雀的喜愛、對傣族文化的敬仰及生命的熱情歌頌和美好未來的憧憬。
“這謙虛的情!這謙虛的情!就是宗教的起源呀!淮爾特 wilde呀,佛爾蘭V甜aine呀!你們從獄里叫出來的‘要謙虛 BehuIIIble!的意思我能了解了。”這是《茫茫夜》中的一段描寫,雖然是簡單的幾句話,卻將主人公面對一些平常生活景物的感想呈現出來,將生活中最自然,最簡單的東西與藝術作品相聯系。引用這個典故的原因在于總結生活與藝術之間存在著三層境界:來源于生活,深入生活,愛上生活。只有達到這三種境界,所做出來的作品才不會是空洞乏味的,脫離生活的藝術,就失去了藝術本質的東西。所以要建立藝術與生活的新秩序與新境界,讓藝術本身回歸與生活之中,善于把生活中零碎事物重新組織成精妙的畫面,用創新的思維方式重現出來。在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下,讓藝術與生活共生、共存,藝術家要用藝術的眼光生活,用生活的方式創造藝術,這樣所創造出來的作品才能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