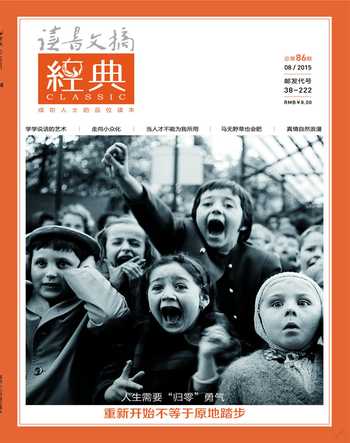政治世襲愈演愈烈
趙靈敏
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是美國的兩大政治豪門克林頓家族和布什家族之間的對決。自1989年以來的26年里,美國的四位總統有三位都來自這兩大家族,統治時間更長達20年。
其他幾個已經參選或有意參選的,比如蘭德保羅、安德魯科莫等,其父也都是國會議員或州長。因此,《華盛頓郵報》在1月17日發文認為,2016年的美國大選是一場了無新意的游戲,“這些候選人中,有人是州長兼總統候選人之子,有人是國會議員兼總統候選人之子,有人是總統之妻,有人則來自兄長是總統、父親是總統、祖父是參議員的家庭。推翻君主制近250年后,我們的總統大選依然帶著濃濃的貴族老爺味兒。”連杰布布什的母親芭芭拉布什也看不下去了:“如果我們除了兩三個家族以外找不到人參加競選,這就太不像話了。我不相信這個偉大的國家沒有培養出其他優秀的人才。”
《紐約時報》則通過大數據的分析得出結論:“父輩優勢”雖然在其他行業也普遍存在,但在政治領域尤為明顯。目前,美國總統的兒子成為總統的幾率比同齡人大約高140萬倍,州長的兒子成為州長的概率比普通美國人高出6000倍,參議員子承父業的機會比普通美國男性高出8500倍。美國的裙帶關系已經非常嚴重。
事實上,這種政治世襲現象并非美國獨有,也并非只存在于某一種社會形態,而是漸漸成了一個全球性的現象: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韓國總統樸槿惠、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馬來西亞首相納吉布、孟加拉國總理謝赫哈希娜、肯尼亞總統肯雅塔、剛果民主共和國總統約瑟夫卡比拉都是“官二代”或“官三代”,其父輩都擔任過國家領導人。古巴的勞爾卡斯特羅則承襲了哥哥菲德爾卡斯特羅的位子,阿根廷現任總統克里斯蒂娜是已故前總統基什內爾的妻子。歐洲也是如此,57%的英國議會議員是前任或現任議員的親戚;近些年風頭正勁的法國“國民陣線”,其領導人一直由勒龐父女擔任;比利時39歲的首相夏爾米歇爾,其父曾經擔任外交大臣和歐盟發展與人道主義援助委員。
政治世襲現象近年來大行其道,其原因是復雜的。
首先,在一些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政治文化中的前現代因素根深蒂固,人們的政治效忠對象首先是家族、部落、種族、宗教,然后才是政府、國家,這種情況即便到了今天也沒有多少改變。在南亞,由于不曾進行過社會改革,農民和領主之間還存在著人身依附關系,領主可以強制農民按照他們的意愿投票,于是,出現了幾大家族長期壟斷政治權力的現象。正如巴基斯坦作家阿赫邁德拉希德所言:“在某些選區,如果封建地主讓自己的狗當候選人,這條狗肯定會以99%的選票高票當選。”在這種情況下,不管這些國家實行何種民主制度,時間有多長,選舉程序如何規范和熱鬧,但歸根到底,它和普通民眾關系不大,只不過是給現存不合理的統治秩序披上合法的外衣而已。
其次,媒體特別是社交媒體的發達,使得選民選擇領導人和到超市購物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大品牌總是更有優勢,更讓人信賴。而那些政治世家出身的人,因為有上一輩積累下來的品牌效應,總是更容易得到民眾的關注和媒體的報道,因此擁有先天的優勢。某些名門望族的后代,可能從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經上了媒體頭條,幾十年下來已經成了國民的集體記憶。再加上這些人從小耳濡目染,對政治職業有精深的理解,又熟悉政界的內部運作程序,其政治感覺和政治經驗肯定是普通人無法企及的。
當然,平庸、不成器的“官二代”也很多,法國前總統密特朗、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和以色列前總理沙龍的兒子,就分別因不同的罪名被判入獄,聲名掃地;印度甘地家族的第四代拉胡爾甘地,也在選舉中敗給了平民子弟莫迪。而在美國,參議院里畢竟還有超過九成議員的父母不是政治人物。這或許是政治王朝現象的另一面:選民會給王朝家族子孫一張免費入場券,但之后,他們必須在競爭中證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