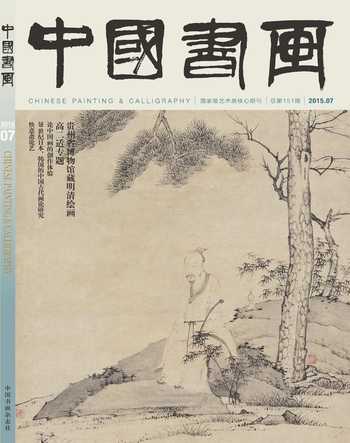詩畫相濟 寫照黔山
朱良津



在清代乾隆、嘉慶時期的貴州,來黔的及本籍的畫家主要有:鄒一桂、董逵、錢維城、洪亮士、楊、浦、陳琮、舒位、蔡兆瑞、簡貴衡、王道行、王敦仁、成世瑄、張金鑒、邱蓀等人。以這些畫家的存世作品及本人在繪畫史上的影響來看'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鄒一桂、錢維城、洪亮吉、王道行。前三位是清廷派往貴州的官員,他們均為名顯于書畫史的大家。鄒一桂、洪亮吉來到貴州均是出任貴州提學使一職,執掌全省文化教育方面的事務,以這樣的職務再兼有書畫造詣,對黔貴書壇畫苑的影響及推動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鄒一桂、洪亮吉、錢維城三位都是江南名士,入黔為官后,目睹貴州地域內,山川蒼茫重疊、雄渾壯麗的氣勢,異于他們所熟悉的一水兩岸,秀麗清雅、逸氣盎然的江南景象,新奇贊嘆之余,情為之所動,筆為之揮灑,三人均曾圖寫貴州山川,并且鄒一桂和錢維城兩人都如同清代初期入黔的蘇州畫家黃向堅一樣,有表現貴州山川風物的圖卷承傳到今。在本文中,筆者試對藏于貴州省博物館的鄒一桂表現貴州風光的山水畫集——《山水觀我》冊,作一番賞析,
鄒一桂,字原褒,號小山,江蘇無錫人。在仕途上最后官至禮部侍郎加尚書銜。清代張庚說他畫花卉“分枝布葉,條暢自如,設色明凈,清古冶艷,惲南田后僅見也”,評價是極高的。張庚還談到了一件事:“一桂嘗作《百花卷》,每種賦詩一經進呈,皇上亦題絕句百篇,—桂復寫一卷,恭錄御制于每種之前,而書已作于后,藏于家。”(見《國朝畫征錄》)一卷畫能讓天下獨尊的皇帝留詩百首,這樣的殊榮,在美術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鄒一桂以擅畫花卉名世,留傳下來的作品主要是這方面題材的,不僅如此,其著《小山畫譜》是關于花卉寫生和創作等方面的專著,對花卉觀察描繪之精微,對技法陳述之詳明、見地之獨到,啟迪后世學畫者良多。
關于鄒一桂在山水畫方面的學習及創作經歷,很少有人提起,據筆者的了解,沈子丞在其著《歷代論畫名著匯編》中有談及:“間作倪黃山水,風格雋冷,亦不亞鷗香館。”語焉不詳,難以讓人更多地T解。貴州省搏物館所藏的這本鄒一桂山水冊頁,因冊頁開頭有鄒氏所書篆字“山水觀我”四字,故以之命名。這本山水畫冊,大多以貴州山川為創作題材,技法豐富多變,不拘一格,細細地品讀觀摩,可窺知這位以花卉畫享譽的畫家,其山水創作之豹斑。
鄒一桂于乾隆元年至六年(1736-1741)出任貴州提學使,在貴州連任此職,宦黔六載。其間,巡游貴州各地,與貴州的山山永水結下了不解之緣,也留下了佳作——《山水觀我》冊。畫冊中的各幅,均是“指名道姓”地圖寫湘黔景色,從畫幅數量看,以貴州山水為創作主體。像這樣出自古代名家之手表現貴州風物的專集,在傳世繪畫中是至為罕見的,堪稱貴州文化遺產中的珍品,是貴州人應視為至寶的。當年,鄒一桂是取道湖南而入貴州的,一踏入湘黔境地,就被這邊的風景深深地吸引了,他那時的心情報在《山水觀我》冊的自序里是這樣表述的:“丙辰春抵湖南,泛舟沅江,花柳爭媚,沿流峭壁頗覺動人,乃稿而笥之,俟暇,欲為圖以嗣粵游之冊。既入黔則萬山穿云,巖壑崖洞稱奇勝者,不一而足顧,以巡試匆匆未暇及,戊午冬期滿,作楚黔十二景一冊……叉蒙恩留任三年,重經所過如遇舊知,然欲圖之,卒無其隙。壬戍還京……憶在黔六載,披荊涉險如在夢中,而林壑在胸不能去,乃追而圖之,得二十二幀。”從這段文中可知,這本冊子實際是他描繪貴州風光的第二本,在序言的后段有“然人不觀山水,山水日起而觀人”之句,在冊子前面便有了“山水觀我”四字篆額,故名曰《山水觀我》冊,全本依次為篆額、自序、二十二幅圖,以及鄭珍、張鵬種、竇奉家三人題跋。在二十二幅圖中,前五幅表現湘西景色,其余均描繪貴州風光,它們依序是《穿石》《清浪灘》《辰溪》《馬嘴巖》《黃繞山》《天柱縣》《相見坡》《玉屏山》《石阡》《關索嶺》《飛云巖》《雞公嶺》《幫洞》《鐵鎖橋》《白水河》《九里箐》《葛鏡橋》《東山》《黔靈山》《雪崖洞》《照壁山》《涵碧潭》。這本畫冊后來又輾轉流入貴州,為遵義名士蹇子振所收藏,冊后的三位題跋者中,唯鄭珍名見經傳,是貴州文化史上的一位重量級人物。他題詩兩首,詩云:“絕(綠)蘿西上接南盤,卅載吟鞭遍謝蠻。滿地干戈人就老,奇山只向畫中看。”其二:“小山秀筆百年存,衣白風流可共論。此跡他時恐難得,喜歸巴縣相公孫。”款:“子振世兄新得此鄒學使所圖,自穿石以上至關索嶺,使節經游奇山水,凡廿二夾。適余過郡,觀之系兩絕句,咸豐己未仲冬,鄭珍。”白文印“鄭珍私印”,朱文印“子尹”。
觀賞冊中的各幅畫,均筆法清秀寫真生動,并且詩書結合這些都是共有的特點。湖南、貴州山勢奇峭險峻,雄渾壯麗,江河秀美,飛流急湍,別具天姿,非親臨其境.難于領略贊嘆其妙處。貴州自古文化滯后,開發較晚,歷史上見于經傳的騷人墨客,丹青妙手踏入此方土地者屈指可數,殊乏對外傳揚。第一個描繪貴州山川的名家是前述的黃向堅,他于順治元年(1644)遠赴云南尋找父母,往返貴州境內,其后,將途中目睹景色,繪成《萬里尋親圖》冊。在他的畫冊中,苗嶺上下,烏江南北,盤江天險盡在圖寫中。第二位便是鄒一桂,—本《山水觀我》冊,將湖南、貴州兩地的風光特色,尤其是后者的山川風物躍然于紙上。細讀此冊,猶如品茗,慢慢地細讀各幅,筆者認為就描繪山水奇峭險峻論,以《馬嘴巖》《幫洞》《石阡》《鐵鎖橋》諸幅可作代表,如突出雄渾壯美者,以《關索嶺》《天柱縣》《雞公嶺》《九里箐》數幅則引人注目。關于每幅畫的構圖、位置經營、技法運用、色彩淡艷等諸多方面,筆者在文中不能一一敘述,選擇其中三幅提出,加以賞析。
首先談談《相見坡》這幅畫,相見坡位于貴州鎮遠縣城附近的文德關,是苗民的世居之地,黃向堅也描繪過此地,鄒一桂以與他迥然不同的手法表現,以墨筆畫出山巒起伏延綿,畫中挺拔聳立的高山與低矮的丘巒相比,畫的重心,不言而喻了'其中的樹木、村居、小橋,加之前面靜靜的河水與蜿蜒而上的山中小徑組合起來,形成了一幅和諧抒情的構圖。位于畫幅左上方的款題,有“相見坡”三個隸字,后楷書七言詩:“偏橋橋東相見坡,行人聽我苗子歌。吹蘆大踏月皎皎,搖鈴暗拍聲嗚嗚。前坡草長苦雅務(難行),后坡石滑愁商訛(放牛)。阿孛(父)阿交(飲酒)在前店,阿蒙(母)歹雞(坐)方陟獻。回頭相見不足奇,去去忽然還對面。山坳固麥(吃飯)趁泉流,山前果翁(行路)人不休,人不休,鵑啼鷓叫延風秋。”款云:“以苗語為長句,聊志方言—二,以資解頤。”觀賞這畫,再讀題詩,兩者意蘊一致,讓讀者獲得了一種整體的審美享受,儼然是一幅鄉間風情畫。論技法,鄒一桂在畫中,對山石的描繪是先定輪廓,后再加簡單的皴筆,繼而用淡墨輕輕地渲染,沒有用濃重的墨去點苔點,墨法顯得明潔,畫面感覺清新爽朗。這種對畫面的處理方法,與作者生活時代的其他山水畫家,繼承元畫,那種淡墨匡廓,重墨皴擦,濃墨點苔,得郁然蒼渾之氣相比,是各有千秋的。與同樣表現過相見坡的黃向堅的那種以渴筆皴擦,取高遠透視,山巒重疊的造勢,一片蒼茫迷蒙的氛圍營造相比,也是大相徑庭的。
接下來要談的第二幅畫是冊中的《鐵鎖橋》,畫中“鐵鎖橋”三個字,以隸書題于畫的左上方,后也以楷書寫絕句兩首。畫中有兩岸奇峰聳峙,一橋凌空飛架,宛若矯龍,這座橋便是位于貴州關嶺、晴隆二縣交界處的盤江鐵鎖橋,崇山峻嶺,煙云繚繞,一彎江水回旋于兩山間,水中礁石錯列,江水沖跌湍急,數折而下,江濤聲聲猶在耳畔,烘托了鐵鎖橋的“驚”“絕”“險”。該幅突出的是江上的梳黃向堅也有表現此處的作品,不過他是著力于對盤江一帶大環境的表現,以中國畫中深遠之法來構圖,畫中蒼山如海,雄關漫道,刻畫得淋漓盡致,大處如此,對畫中近處的“細節”,也沒有忽略。畫得也不失生動。鄒、黃二人雖然表現手法各有不同,這是各自的理解與創作的側重點不一樣,但是殊途同歸,都使讀者感受到了盤江奇峭險峻的自然景觀。鄒在畫上題詩更是增添了這樣的意蘊,詩曰:“豈徒騎馬似乘船,鐵鎖橫橋直上天。正是秋風吹不定,怒濤驚吼起龍眠。”另一首:“十二峰頭鎖玉關,八牛粗杠滿連環。盤江萬里滇黔界,一道長虹控百蠻。”
再看冊中《九里菁》這幀,九里菁在貴州黔西、大方二縣之間,畫里一道清泉置于正中,在山間盤回,涓涓而下,這張畫在構圖上有一個特點,兩邊山石大小及排列樹木著筆分量幾乎相等,作者畫右邊山不見頭,云騰霧繞蒼茫一片'如此處理會使觀者產生無盡的遐想。筆者以為這樣的表現方法,正體現畫家的高明之處,試想若畫山頭,勢必造成溪流將兩邊山石一分為二的對等形式,中國畫構圖中最忌“齊”字,鄒一桂不畫山頭而以云煙代之,畫的意境頓增。另外,就色彩而論,此幀山石施以淡赭,樹木則以紅黃二色為主調,加上遠處云煙迷漫,確是一派渾樸雄健的黔北秋色。山石技法上,披麻皴、折帶皴、斧劈皴和諧融為一體,樹法上,點葉法、勾葉法交錯使用,畫云法,勾勒、烘染兼而有之。畫幅右上題“九里菁”三字,左上題詩:“水西西去是西溪,竹樹蒙口取徑迷。賴有一勾泉引路,系教人信鷓鵠啼。”后有四句因紙本殘泐不易辯識。這幅予觀者的感受,既非《鐵鎖橋》的“驚”“險”“奇”“絕”,也非《相見坡》的恬靜抒情,而呈現一種郁然蒼深之氣。
讀罷《山水觀我》冊后,筆者產生了一些想法,以審美角度來看,此冊每幅均有感而發,賦以詩句,詩畫相配是冊中的一大特點。詩意與畫境相兼,更助于作者對繪畫意境的表達,同時也強化了客觀物象在主觀心理上的表現。鄒一桂本人也曾說過:“善詩者詩中有畫,善畫者畫中有詩,然則繪事之寄興與詩人相表里焉”。冊中每幅的詩句,都是在直抒心緒,觸景生情,都是面對自然風光的有感而發,作者利用詩句來拓展畫的表現意境,讀者賞畫讀詩之后,便獲得了有回旋余地的“神游”世界,在心中產生了意境美、詩意美的享受。
“搜盡奇峰打草稿”是古往今來很多畫家在關注生活,進行創作時的一種表現。鄒一桂在畫冊中,以實景為依托進行創作,“指名道姓”地為黔貴山川寫照。從畫家的角度,對現實物象產生很多的關注,本身已說明了其藝術主張。關于這—點,鄒—桂在其著作亦有談及的,例如,說到對花卉的觀察,他說:“天生雖一,而地各不同,北地風塞,百花俱晚,滇南氣暖,冬月春花,芍藥以京師為最,菊花則吳下為佳,湖南多木本之芙蓉,塞北無倒垂之楊柳。”(見《小山畫譜》)一般而論,勤于觀察生活的畫家,大都必然善于寫生,鄒一桂也不例外,《國朝畫征錄》中記載著:“少司寇錢香樹,曾與鄒一桂游盤山,適杏花盛放,錢香樹出所藏佳紙,索寫盤山杏花圖,鄒不辭,于花下點染,屋宇、垣墉、山嵐、花氣,一一如妙。”所以當他一進入湘黔境地,便搜盡奇山異水,創作了一幅幅別樣多姿的佳作。這些以抒發個性、感受現實景象作為創作原則的作品,與上述他的那些留意自然物象變化的言論相聯系,展示了他在繪畫創作上理論與實踐的一致性。與比他稍早的一些畫家,如石濤、弘仁等人的那種“搜盡奇峰打草稿”的創作態度趨于一致,這本山水冊,題材取之造化,對大自然的氤氳變幻,奇妙之景,不拘—格地隨境界意趣的不同而使用各種技法。在讀這本畫冊時,我們又有一種感覺,對于眼前的具體景物,作者又有自己的主觀理解,并不為所見的自然景觀所囿,依附自然景觀,而主觀的理解,需要夸張和側重的東西,非常明顯地存在于每幅之中,充分地得以彰顯。可謂“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還有_點值得提及的是,鄒一桂生活在清代前期,這一時期“四王”畫風煊赫于畫壇,摹古習尚引發對前人作品的頂禮膜拜,不重視對生活的體驗,具體表現在山水畫中,峰巒滿縑,堆砌成圖,千篇一律,使生氣索然之作比比皆是。鄒官居顯位,而又供奉內廷,學古亦師造化,直面當時倡導的那種藝術精神,能以豐富的技巧,描繪目睹的現實風光,確屬難得。
在這本畫冊中,還有一種審美意趣,即“生”的意趣。筆者所說的作者在畫中所表現出來的“生”,自然不是指那種由于學畫日短,各方面都顯得生疏的意思,而是指在繪畫創作的各個方面已相當成熟的基礎上,能有意地避熟就生,所達到的由巧還樸的境界,兩者是不同層面上的問題。仔細地觀賞《山水觀我》冊,不論從畫的章法、物象的造型或筆墨的處理上看,都不斤斤計較于一種形式上的嚴密性,或者造型上的精準性,漫筆寫來而不刻意追求,有些畫面讓人感到比較率意。我們有時讀畫,常因為作者在創作中過于想到法度問題,在畫面中想做到面面俱到,太多地去計較細枝末節的得失,缺乏生動,而遺憾作品失之“玩味”。這種“生”的意趣,是畫家在創作中一種天性的自然流露,無處不在,也是畫家的內在學識及藝術造詣產生作用的一種藝術創作的外在表現。
這本畫冊以現實的自然風物為題材依據,洋溢著文人畫家的氣息,詩與畫相配來讓觀者產生詩意想象,同時又是以豐富多變而帶生拙的手法來進行創作的。